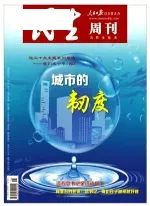肖亞洲:為“900后”正名
□ 本刊記者 張子琦
肖亞洲:為“900后”正名
□ 本刊記者 張子琦
“在我看來,亞洲最讓我感慨的,不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在認識國情、吃透國情方面的不懈努力,是不依不饒的批判精神,是他對公權力習慣性地保持著批判性質疑的姿態(tài)。”——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周瑞金(皇甫平)
17歲的肖亞洲個子高高的、一頭濃密的自來卷、五官還未褪去少年的稚氣,笑起來憨憨的,用時下流行的詞來說就是“萌”。
1995年出生的肖亞洲已經小有名氣,他的時評文章常見諸報端和主流新聞網站,還擔任過《北京晨報》、《楚天都市報》、《青島晚報》等多家知名媒體的專欄作者和特約評論員。前不久,這些文章被九州出版社分三冊結集出版,定名《一個90后的社會人文沉思錄》。
沒有搶眼的封面,也沒有花俏的宣傳,只在下方羅列了幾位重量級的推薦人——皇甫平、于建嶸、梁文道、鄢烈山、秋風、熊培云。3冊書并排擺在書架上,低調地華麗著。
今年暑假,肖亞洲在王府井書店看見這3本書,覺得“特別有成就感”。
公民寫作者
2000年起,新世紀作文比賽推出了一系列少年作家。在隨后的十年里,“少年作家”們層出不窮,“低齡”成為出版社吸引讀者眼球的一個重要噱頭。
表達少年內心世界的彷徨以及華麗的文風幾乎成為少年作家們的標志。相比之下,肖亞洲干凈簡潔的文字,犀利卻不失清新的文風,立論清晰針砭時弊的理性思考,顯得獨樹一幟。
“我寫不好那些表達迷惘和頹廢情緒的文字,只能寫直面社會現(xiàn)實的時事評論。”他說,對社會上某些荒誕、鬧心的事,他無法保持緘默,“我的內心始終蘊藏著質樸的‘道德沖動’。性格即文體,有的人活成了散文,有的人活成了小說,我愿意活成雜評。”對于自己選擇的寫作方式,肖亞洲語氣中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
肖亞洲最初的寫作沖動是對某些不公平的社會現(xiàn)實的“憤怒”。但隨著“閱讀經歷”的豐富和知識面的擴大,肖亞洲逐漸意識到時評作者需要的不僅僅是“憤怒”,而是“理智地用犀利的文字捍衛(wèi)弱者的權利、呼吁對生命和尊嚴的維護。”他說,“我不是反對一切,更不是‘憤青’,寫作只是源于愛、正義和真理難以觸摸時深刻的傷痛,即使是批判,最終也指向人性深處的溫暖。”
他把自己的寫作歸為“公民寫作”,即以公民身份,促進公共利益,維護公共規(guī)范,就公共事務理性發(fā)言。用自己的筆,為弱勢群體鼓與呼,推動社會進步,“哪怕是一小步”,也是肖亞洲樂見的。
2011年7月,陜西省城固縣冒出一個用來收容關押上訪人員的“法制培訓班”,用饑餓、打罵等手段折磨上訪者直至其“息訴罷訪”,造成一名上訪者被活活餓死。肖亞洲就此寫了一篇《“法培班”事件中的刁官與刁民》,首發(fā)在湖南紅網“紅辣椒評論”。在民間和官方都引起了特別大的反響。
這篇時評獲得“2011年度紅辣椒評論佳作獎”。還有網友將肖亞洲評為“2011年度十大影響力(新銳)時評作家”。盡管這頂桂冠來自民間,但其中分量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湖南紅網“紅辣椒評論”的幾位編輯,兩三年時間里先后編發(fā)肖亞洲的時評文章五六十篇,一直以為他是教師。直到他因這篇評論受邀去衡陽領獎時,才知道他的身份是一名在校高中生。
獨立精神
肖亞洲第一篇發(fā)表的文章是9歲的時候寫的《有些地方是哪些地方》,發(fā)表在河北省的《雜文報》上。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肖亞洲覺得自己如此癡迷文字的原因是家庭的熏陶。他說,父母都酷愛讀書,家里光是裝書報的箱子至少有10個,油墨香伴隨了肖亞洲的整個童年。
茶余飯后和父母討論交談,是他最為歡快的家庭記憶。在這樣的“家庭論壇”里,也培養(yǎng)了肖亞洲的獨立思考精神。和父母在同一個問題上的平等對話,讓他學會了在任何時候都真誠地、盡量有高度地看待一個問題,而不是僅僅順從于他人的思想或某種習俗。
“這實際上就是在培養(yǎng)我的批判意識。所以我們家庭也有爭論,常常會因為某個問題,父子之間爭得面紅耳赤,但事后都感覺過程很愉快。”
但對肖亞洲來說,父親賦予他的絕不僅僅是觀察分析生活的能力,而是對社會的“責任感”。他說,“爸爸沒寫過一篇時評,但他有一種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底層關懷意識,有一種為弱者代言的身份自覺。這種態(tài)度一直影響這我。”
2006年春,小學五年級的肖亞洲就已經為幾個農民工子女被迫交納高額借讀費給北京教育部門寫信。并最終促使該問題得到解決。“現(xiàn)在看起來很稚嫩,但我沒有順從、麻木或者只在口頭抱怨,而是用文字說了心里想說的話。今天,如果再遇到這樣的事情,我還會選擇當年的做法。”
作文和時評的“平衡點”
進入高中階段,課業(yè)負擔十分繁重。為了寫時評,肖亞洲總是利用早晨和午休時間,匆匆瀏覽當天網上熱點新聞,捕捉評論由頭,下午和晚上做一些醞釀,晚自習回家后挑燈夜戰(zhàn)寫就。“寫得最瘋的時候是高二,幾乎一天一篇。”
但是學習畢竟是肖亞洲的“主業(yè)”,為了不耽誤學習,他經常琢磨如何提高學習效率,然后將全部精力用在構思和寫作上。除此之外,就是利用節(jié)假日查漏補缺,“從高一開始,我沒度過一個完整的寒暑假,長假和兩周一次的休息也經常在教室度過。”
兩年下來,肖亞洲的成績始終是學校的10名左右。這樣辛苦的生活肖亞洲卻甘之如飴,“當你對某件事情充滿激情,你總能在逼仄甚至嚴酷的環(huán)境中,找到并擁有一塊心靈的綠洲。”
如今,肖亞洲已經高三了,在老師和家長的建議下,暫時“封筆”,全心備戰(zhàn)高考。但長年的習慣,讓他“看到某些新聞,總有些不吐不快”,只好寫一些一、二百字的短評。“這已經是生活的習慣。”

肖亞洲生活照 圖/受訪者提供
“思想成熟”的肖亞洲并不覺得自己“另類”,也不像一些人認為的“有才情的孩子一定不合群”。相反,這個大男孩一直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在同學中也人緣極好。
“如今社會上很多評論90后的詞語都是負面的,但我所在的班級每周都會舉辦‘時事論壇’。每個同學會選取一個社會熱點問題討論,人人都能表達自己獨特新穎的感悟和思考。我也能在和同齡人的交流中獲得靈感。”肖亞洲覺得,“90后們已經以自己的方式綻放。我們大多數(shù)并不像前輩擔心的那樣,而是能夠獨立思考、客觀表達的一代人,對社會有責任和擔當?shù)囊淮恕!?/p>
現(xiàn)實生活中,肖亞洲并不犀利,甚至有些細膩。他的一位同學母親因病去世,生活拮據(jù)。肖亞洲想幫助這位同學又擔心傷害他的自尊心,便從自己的生活費中省出300元錢,悄悄地放在那位同學的書包里。“至今他還不知道是誰放的。”肖亞洲說。
不過,這個讓很多家媒體“驚艷”的時評作者,卻也有不得不面對的“成長的煩惱”。“我一直不肯迎合程式化的應試作文,所以作文考試分數(shù)一直不高,很不服氣。”肖亞洲說,他想在自由寫作和應試作文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效果甚微。
距離高考還有半年,肖亞洲還在為自己的作文成績沖刺著,“最近的一個愿望,就是作文成績能沖進一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