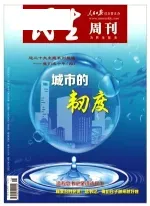未曾褪色的青春
□ 本刊記者 鄭 旭 郭 鵬
未曾褪色的青春
□ 本刊記者 鄭 旭 郭 鵬
青春的挽歌永遠會與厚重的歷史互為共鳴。
據記載,受“文革”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在1968年處于衰退狀態,工農業總產值比1967年下降4.29%,大多數工礦、企業無法招收新工人。
與此同時,招生考試制度被廢除,造成大批66—68屆初、高中畢業生(俗稱“老三屆”)積壓在城鎮,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那年,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之后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現年59歲的唐根榮向《民生周刊》記者回憶說。
事實上,在這場令眾多“新生代”難以咀嚼的歷史運動中,有近2000萬名城市青年走進農村,其中有54萬人來到遙遠又陌生的東北邊陲。他們如同蒲公英的絨傘,散落在北大荒那片肥沃卻又沉寂的黑土里。
險被射落的夢
1968年,唐根榮15歲。
盡管生于上海,但在“文革”思潮鼎沸的年代,斑斕的霓虹已經難以尋覓,“紅色”浸染著每個人的精神世界。熱血澎湃的他,用一把鋸條磨成的刻刀,在書桌的一角歪歪扭扭地刻下“永遠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幾個字。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為題,報道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報道還印有毛主席語錄:“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這是毛主席的指示!”唐根榮跑到當地知識青年報名接收點,希望能到邊疆參加生產建設。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工作人員在審閱材料后認為他年齡不符合“知青”條件。
唐根榮告訴記者,自從上了中學,他就從未哭過鼻子。即便那次因為嘴饞偷了家里的糧票去換雞蛋,被父親知道后挨了一頓痛打,他也沒掉一滴淚。然而,看到鄰居家早自己幾年畢業的青年都無上光榮地被歡送時,他只能躲在屋子里大哭一通。
“不是因為男孩子的自尊心受了挫,而是覺得沒有成為知青的一員,就等于沒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唐根榮承認,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稱謂讓青年一代猶同追夢一樣奔赴祖國各地。去不上,夢想便被射落,心里的那個結要用幾年或更長時間來解。
這個心結讓此后的唐根榮自我糾纏著,加上青春期的莽撞,他變得易怒而不思進取。打架、堵鎖眼、和家人吵嘴斗氣等都是他那時的發泄方式。唯一能讓他稍作安靜的,是每天花上一分錢,在弄堂口的書攤讀上幾本小人書。
不可回避的是,“文革”讓當初許多和唐根榮一樣的青年,錯過了汲取文化知識的黃金時期。“那個時候喜歡看連環畫,這樣一來,即便遇到不會的字,也不會影響心情。”唐根榮說。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70年。
這一年勞動節剛過,唐根榮的一位同學跑來告訴他,新一批知青名單已經公布,只是沒有看清名單中有沒有他。興奮的唐根榮顧不得將手中的小人書還給攤主,就拔腿跑向了學校,害得同學被攤主留下做了“人質”。
在400多人的名單中,唐根榮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唐根榮后來才知道,他被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4師37團(現為黑龍江省農墾總局牡丹江管局856農場)。盡管并不曉得要去的地方離上海有多遠,但在唐根榮的精神世界里,去了兵團就能保衛邊疆,就能有一支鋼槍分發給他,于是他越想越興奮。臨行前,他向送別的家人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并立下如不立功絕不回家的誓言。
北大荒有張床
4天3夜的火車,2800余公里的行程,讓平生第一次走出家門的唐根榮和同行的100余名上海知青有些吃不消。
“見有些女知青想家,年長的知青就開始給她們鼓勁兒。”
唐根榮這一批知青中,有來自各個學校宣傳隊的同學,于是有人拿出口琴、笛子等樂器,演奏了《歌唱祖國》、《唱支山歌給黨聽》等紅色曲目。再后來,大家就以學校為單位,開展拉歌比賽。
白天的時光在此起彼伏的歌聲中度過,可到夜間行車,難以入眠的知青們就會竊竊私語。
“男同學會講看過的英雄故事,女同學大多講一些父母兄妹的囑托。也有曾經去過黑龍江的知青,渲染黑龍江冬天會凍死人,一些膽小的女同學被嚇得偷偷哭了起來……”唐根榮說,火車上,他在夜里想的還是那支鋼槍。
這群上海知青在哈爾濱火車站短暫停留后,沿途經過了亞布力、牡丹江、雞西、密山直至終點虎林。最終,這支知青隊伍由最初的百余人減少到30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后有50余萬城市青年來到北大荒,成為軍墾農場開發建設的生力軍。

“每到一站,就有一批知青下車,去往他們人生的第二故鄉。”唐根榮從虎林站下車后,被37團派來的卡車接到了團部(現為856農場場部),同批來的還有北京和天津的知青。
寬闊的廣場上塵土飛揚,團部領導在一個水泥臺上,做了簡短卻熱情洋溢的歡迎辭。那充滿力量且沙啞的口音,與唐根榮熟悉的上海話截然不同,讓他幾度差點笑出聲來。
領導話音剛落,唐根榮想,是不是該發槍了?但他沒有等來想要的結果。
唐根榮被隨后而來的11連指導員點了名,和幾個北京、天津知青一起上了馬車。馬車在泥濘的土路上走了1個多小時才到達連部。一路上,女知青連呼景致壯美,唐根榮卻低頭盤算著:“如果到了連隊不發槍就打道回府。”
“下了車,好多人從僅有的幾棟磚房里冒出來,幫我們拿行李。”唐根榮從口音辨別,這里有天津人、山西人……他們是一年前來到11連的知青。
唐根榮清楚地記得,他到連隊的時間是1970年5月23日。那天下午,連里的指導員讓木匠把破好的木板搬進男生寢室。在兩垛由8塊磚壘成的“床腿”上,木板搭成了一張床。唐根榮從行李包中取出一條薄薄的褥子,鋪在了上面。
“那張床,是我來到北大荒睡的第一張床。”晚飯過后,唐根榮想早點睡,就拿出一塊上海牌檀香皂準備洗漱。同寢室的東北知青將香皂拿去聞了一下,問能否借用,被唐根榮拒絕了。
“后來有知青回農場聚會,還提起這件事,說上海知青小氣。其實我真不是小氣,是因為當時就帶了這么一塊香皂。在計劃經濟年代,香皂是北大荒兵團里的緊缺物資。”唐根榮說。
師者如父
盡管一支鋼槍在手是唐根榮的愿望,但在知青生活中,擁有一項過硬本領才是當時連隊上下最為推崇的現實目標。于是,3個月基本農田勞動結束后,唐根榮開始有了學習技術的沖動。
“晚上躺在床上想我能干什么,突然,我覺得當個木工也蠻好。為廣大知青做些小家具、農用工具應該是件很快樂的事吧?”第二天,唐根榮提了兩瓶高粱酒來到連隊的木匠師傅家,剛一推門,就看見同寢室的其他知青早已在此排隊,他等了半天最終還是退了出來。
“那么多人學一項技術,別說師傅沒時間,就算學有所成,以后有木工活也不一定能輪到我。”唐根榮說,此后的半個月里他想過學養殖、獸醫,但都沒能下定決心去拜師,直到有一天,他從團部回連隊的路上,發現了正在保養車輛的拖拉機手。
拖拉機手名叫王炳志,是當時11連乃至全團的機務能手。從某種程度上說,王炳志改變了唐根榮的生活。
據唐根榮回憶,王炳志起初并未理會他的存在,只是低頭擦拭著柴油發動機的零部件。直到一個小時后,王炳志抬頭見唐根榮還沒走,才有意無意地搭了一句話。
“我師傅當時問我是不是知青,我膽戰心驚地說是,話音剛落,他就聽出我是上海人。”那天他給王炳志打下手,忙得不亦樂乎。王炳志見他人機靈,眼里有活,于是打心底喜歡上了這個上海知青。
那天日落以后,王炳志讓唐根榮次日中午到連隊的機務場集合,可直到過了午飯時間,唐根榮也沒見到王炳志。下午王炳志來到唐根榮的寢室,發現他正在給家里寫信,眼中蓄滿淚水。
“師傅問我是不是想家了,我點點頭。他說,連隊就是你在北大荒的家,我們都是你的親人。” 唐根榮激動不已,連向王炳志喊了三聲“師傅”。
原來,那天早上王炳志去團部圖書館給唐根榮借書,回來的路上,被其他連隊叫去幫忙修理拖拉機,才有了中午的“爽約”。
此后,周邊連隊的拖拉機手都知道,11連的王炳志收了一個上海知青做徒弟,每年的春播、秋收,兩人形同父子,耕作在北大荒那片廣袤的田野上。

圖/鄭旭翻拍
回不去的家
1979年,知青返城的消息從北京傳到唐根榮所在的連隊。半信半疑的知青起初只是私下議論,待返城政策真正落實的時候,反倒讓一些知青犯了難。
“我們有些女知青在政策落實之前已經嫁夫生子,返城對于她們來說已經不太現實了。我們一些男知青更是如此,如果真的返城了,就要背負拋棄妻子的罵名。”
唐根榮告訴記者,參照政策所明確的標準和條件,他是可以返城的。可回到上海又能做什么呢?在他看來,自己唯一的技能就是駕駛和修理拖拉機。上海那么大,哪個單位會用拖拉機手呢?
事實上,1969年至1979年十年間,全國各地共有4792名知青在856農場工作和生活過。此后絕大部分知青因政策逐步落實和放寬,先后回到了他們的第一故鄉。
1980年,選擇留守在北大荒的唐根榮和當地一名軍墾戰士的女兒喜結連理。婚后,連隊的人們發現,唐根榮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人交談時,鄉音淡了許多;“東北小燒”每頓飯也會喝上二兩;每到秋天,他會在愛人的幫助下腌制高寒地區特有的酸菜……
如今的856農場第11連已經完成“撤隊建區”,成立了第十管理區。作為管理區黨組成員,唐根榮說自己其實沒有改變。“當年選擇了留守,是為了更好地融入;今天真的融入了,但我們還是知青。知青其實就是一枚印記,只要烙在了心口,就永遠不會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