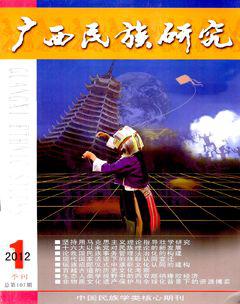壯族政治文化的演變與發展軌跡分析
陳強
[摘要]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嶺南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至今,壯族政治文化的演變與發展的軌跡為: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當代壯族政治文化存在的問題是:壯族“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程度不足導致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成分不高;壯族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不足導致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成分不高。
[關鍵詞]壯族;政治文化;阿爾蒙德;演變與發展?
[作者]陳 強,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副教授、博士。廣州,510630
[中圖分類號]C9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2)01-
Analysis on the Track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Peoples Political Culture
Chen Qiang
Abstract: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ree counties Guilin, Nanhai and Xiangjun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ix countries by Qinshihuang, the track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peoples political culture is such a track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regional political culture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attached political culture → regional political culture + participated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Zhuang people ;political culture ;Almond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在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阿爾蒙德的理解一直以來被認為最具代表性。他1956年在美國《政治學雜志》發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并將其界定為某一民族或社會對某一政治系統以及各種政治問題的態度、信仰、感情、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認為每個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他在1966年出版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明確提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所形成。”[1]( P.29)
我國政治學者王惠巖主編的《政治學原理》提出:“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個國家中的階級、團體和個人,在長期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形成的某種特定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模式。”[2]( P.231)可以看出,這一定義與阿爾蒙德的定義是很接近的。
阿爾蒙德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書中提出政治文化的三種類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他解釋到,地域型政治文化是地方自治性質的文化,“中央政府的專門機構幾乎不可能觸及到市民、鄉民和部落民的意識。他們的取向傾向于非專門化的政治—經濟—宗教取向”[3](P.20),依附型政治文化是絕對服從中央政府性質的文化,“臣民只意識到特定的政府權力并在感情上取向于它”,“在已發展成民主制度的政治系統中,這種依附取向是情感的、規范的,而不是認知的。”[3](P.21)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性質的文化,參與制政體的個體成員“在政體中傾向于適應一種自我‘活動者的角色”,“趨向于積極地參與政治”。[3](P.22)
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學者專門研究壯族的政治文化,僅有一些零星的關于壯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倫理的研究成果。筆者經過研究認為,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嶺南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至今,壯族政治文化的演變與發展的軌跡如下: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
一、壯族政治文化的第一階段:依附型政治文化
現代民族學、歷史學界公認壯族是由中國古代嶺南的越人的一支發展而來,其先民乃是百越中處于部落階段的西甌、駱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遣五十萬軍隊進入嶺南,設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派官吏進行直接統治,從此壯族地區受到中央封建王朝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嚴密控制,“使得還處于部落階段的西甌駱越先民還來不及實現民族的統一及建立完整的國家機器便逐漸覆沒了”[4](P.17)。“封建王朝早在壯族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就采取了嚴酷的統治,這就是為什么壯族沒有形成自己統一的民族意識的原因。”[5](P.62)
在中原中央政府的直接而強有力的統治下,壯族地區民眾逐步接納和服從中央政府。同時,隨著漢族文化對壯族地區的影響日益加深,壯族民眾對中央政府和中華民族的認同度越來越高。“壯族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正是在與華夏—漢族的長期互動過程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其內涵和特征也是表現為對中原地區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感。”[6](P.104)
秦以來的壯族政治文化很明顯屬于依附型政治文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封建集權專制政體上的。
二、壯族政治文化的第二階段: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
唐朝初年,中央封建王朝在壯族聚居地區左、右江和紅水河流域實行“羈縻政策”,建立羈縻州縣,任命壯族首領為都督、刺史,“以夷制夷”,由其直接統治壯族地區,而中央政府的統治改為間接統治。所謂“羈縻”,即既要用“羈”,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壓力加以控制;也要用“縻”,以經濟和物質的利益給予撫慰。實行“羈縻政策”之后,中央政府對壯族地區的駕馭還是很強的,壯族地區民眾依然服從于中央政府。但是,壯族地區由壯族首領直接統治和管理,這就使得壯族地區多了一層地方自治的色彩,當然,這層色彩還是比較淡薄的。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壯族政治文化是復合型的,即地域型政治文化(萌芽狀態)+依附型政治文化。
羈縻政策下中央封建王朝的橫征暴斂給壯族民眾帶來的沉重負擔使壯族民眾不堪忍受,屢次反抗起義,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儂智高起義。1052年,北宋中央王朝乘儂智高起義失敗之機,在壯族地區建立和實行土司制。土司制是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中央“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雄者為首領,籍其民為壯丁”[7](P.312)。土司制鞏固了中央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土官完全由壯族首領擔任,實行壯族聚居地區自治,但又在中央王朝可掌控的范圍之內。“土司制度中,土官占據著一定的地盤,但絕不允許他們互相之間有來往,他們只能各自和王朝保持聯系,定期進貢和上朝,在漢官的監督和控制下,統治自己所管轄的那一塊地盤。”[5](P.62)土司制度是中央駕馭與地方自治的結合,這種地方自治的自治程度比起羈縻制度下的壯族地區自治更高一些,這表現在土官的權力比羈縻時期的壯族官員的權力更大一些,土官自詡“六坡八甲,任吾駕馭;一街四方,由我管理”(全茗(今大新縣)土官祠堂對聯)[8](P.313)。然而,中央王朝給土官定了許多規矩,即“相應的制度和規章,如土官承襲制度、審案制度、春秋大祭、出入衙門制度、衙門例規、踩棚制度、進貢制度、兵制、迎賓儀典、土地制度等等” [9](P.313)。可以看出,土司制度下的壯族政治文化也是復合型的,即地域型政治文化(鞏固狀態)+依附型政治文化。
三、壯族政治文化的第三階段:依附型政治文化
壯族地區的土司制度持續了近千年,直到“改土歸流”。“改土歸流”是指改土司制為流官制,中央政府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目的是解決土司割據的積弊,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
張聲震主編的《壯族通史》提出,壯族地區土司制度的“改土歸流”從明朝初期就已開始。[10](P.656)這一政治改革的背景是壯族土官與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銳,土官們的獨立意識日益強烈,反對中央王朝對其管轄。對此有損于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苗頭,明王朝忍無可忍,下定決心“改土歸流”。上述《壯族通史》認為,壯族地區土司制度的“改土歸流”過程經歷了五六百年,直到1928年土司制度的最后消失。為何如此長久?“明初,由于土司制度處在上升發展階段,基本上適應著生產力的發展,顯示出其生命力,改流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故‘改土歸流的阻力很大,出現改流后復土的現象。明末清初,由于封建地主所有制因素的萌芽和增長,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農奴階級為擺脫土官農奴主的統治而不斷起來斗爭,土司制度趨向衰落,改流的條件具備,故清初大規模‘改土歸流得以推行” [10](P.656),再沒有出現復土的情況。
改土歸流后,壯族地區土官們的勢力遭受重創,逐漸凋敝,地方自治被取消,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得到恢復,中央權威得到樹立和加強,壯族地區民眾重新直接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大樹底下。這時的壯族政治文化重新回歸秦以來的依附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的層面緩慢消失了。
四、壯族政治文化的第四階段:地域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
民國時期,廣西壯族地區主要處在桂系軍閥集團的統治之下。桂系集團有舊桂系集團與新桂系集團之別。“舊桂系集團的民族觀念是模糊而無明確界限的,所以它的民族政策也是朦朧不清的。”[10](P.939)而“新桂系民族政策的實質,總的來說,仍是歷代民族強迫同化政策的延續。”[10](P.939)
民國時期爆發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壯族人民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他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創造了輝煌的業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史冊增添了光輝的一頁,他們與全國人民一道,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贏得了本民族的解放,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10](P.963)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廣西右江地區誕生了一個工農民主政權。1929年12月12日,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恩隆縣(今田東縣)平馬鎮召開,一致通過關于建立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決議案,選舉產生以雷經天為主席、韋拔群、陳洪濤等為委員的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即蘇維埃政府)。11名委員中,壯族委員有5名。在紅七軍幫助下,東蘭、鳳山、百色、奉議、恩隆、思林、果德(今屬平果縣)、隆安、向都(今屬天等縣)、凌云、那馬(今屬馬山縣)、都安、那地(今屬天峨縣和南丹縣)、河池等16個縣先后成立蘇維埃政府或革命委員會,其中13個縣的第一任主席是壯族干部。[10](P.979)
右江工農民主政權是一種區域性政權,可被視為地方自治的政權。“右江工農民主政權的創建,開創了在以壯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地區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先例”[11](P.12)。在右江工農民主政權管轄區域內,廣大勞動人民有四項民主權利,包括政治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罷免之自由”[12](P.235))、平等權利(包括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官兵平等以及平等地獲得土地等權力)、進行勞動、改善勞動和生存條件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右江工農民主政府政府由選舉產生,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還體現在他們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各級工農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和各項具體政策都必須經過各級工農兵代表會的充分討論并通過后才能發布實施,由于各級工農兵代表會的成員來自人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故能保證政府的各項政策體現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意愿。”[11](P.13)
右江工農民主政權的意義非同尋常。“從壯族發展的歷史來看,這是壯族人民第一次擁有并行使民主權利。右江地區曾長期實行士司制,直至1929年,‘改土歸流才全部結束,在土官的統治下,壯族人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可言,甚至連做人的基本權利也沒有” [11](P.13)。
從政治文化層面分析,右江工農民主政權時期的壯族政治文化既有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成分(區域性政權、地方自治),也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成分(民眾積極參與政治,充分享有各種民主權利),因此可謂之地域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廢除了過去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或強迫民族同化政策,尊重民族自治要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1952年12月,廣西的西半部建立桂西僮族自治區,1956年春改為自治州。1958年3月,建立以原廣西省地區為范圍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僮族”改為“壯族”)。1958年4月,建立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建立廣東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行,使壯族民眾得到了政治平等和自治的權利。當時的壯族政治文化主要屬于地域型政治文化,其中也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成分,但這種成分與右江工農民主政權時期比較起來,顯得很不夠。
改革開放后,為了使民族區域自治走上法制化道路,國家于1984年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依法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該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應當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組成人員,應當合理配備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員。該法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于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自治機關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準,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出臺,對壯族加強和鞏固民族自治非常有利,可進一步提高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成分。
改革開放后,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參與型政治文化成分逐漸有所提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基層民主在壯族地區得到實踐。1980年全國第一個自發成立的村民自治組織在廣西壯族地區的宜州合寨村出現,合寨村成為“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1979年,合寨村農民自發分田到戶,調動了生產積極性,然而原來的生產隊變成了空架子,農村管理出現問題。1980年1月,合寨村果地屯召開全屯戶主會議,決定成立村民委員會,選舉蒙光新為村民委員會主任,并制定“村規民約”,決定用村規民約進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合寨村于1982年成立“議事會”(即“村民代表會議”),由村民推選出的曾擔任過鄉村干部的有威望的老人、參政議政能力強的黨員以及部分現任村干部組成,村里重大事情須由“議事會”討論研究,所做出的決定,經村民會議通過后提交村委會辦理。合寨村推行“村務公開”,在村民委員會所在地設置“明白墻”(專欄墻報),將村民自治事務、村里重大建設項目、財務開支、村民意見征詢與反饋等情況及時向村民公開。合寨村創造的村民自治的許多舉措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的重要內容。合寨村的偉大創舉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的高度重視。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民政部等派出工作組進行實地考察,充分肯定了這一壯舉。1982年12月修訂的《憲法》確立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則,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我國農村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此后,村民自治在壯族地區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不斷得到完善。
壯族地區的村民自治,意味著壯族農民積極參與農村民主管理,以實現“當家作主”的愿望。這顯然是一種參與型政治文化。
其次,越來越多的的壯族民眾開始萌生公民意識。公民意識意味著關心國家和社會治理,負有社會責任感,積極參與政治,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各項政治權利,同時積極維護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壯族的傳統觀念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沖擊,愈來愈多的壯族民眾調整心態,更新觀念,逐漸樹立一些現代觀念(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等觀念)。其中一部分壯族民眾開始摒棄具有封建時代特色的臣民意識,樹立了公民意識。這使得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成分有所提高。
五、當代壯族政治文化存在的問題
當代壯族政治文化可歸結為地域型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然而,這兩種政治文化的成分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先說地域型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成分主要體現在壯族的“民族區域自治”。雖然壯族在這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也存在不足。“現在的問題是,廣西是否敢于利用《民族區域自治法》所提供的法律保證,充分行使中央賦予的自治權和自主權。”[13](P.307)原因何在?“一方面是壯族作為自治民族,自治和自主意識不夠強烈,不敢大膽地行使自治權和自主權。另一方面,自治區內的其他非自治民族,主要是漢族,對廣西行使自治權和自主權缺乏正確的認識。”[13](P.307)壯族自治不足的一個明顯表現是壯文的普及和使用不受重視,至今廣西境內壯文版的報紙僅有《廣西民族報》一家,壯語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完全沒有,這與西藏、新疆、內蒙古等自治區形成強烈的反差。
再說參與型政治文化。雖說越來越多的壯族民眾開始萌生公民意識和參政意識,但是這只是剛起步,離建立一個成熟的壯族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得到的政治知識和政治訓練較少”,壯族民眾“對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知識知之甚少,他們相當多的政治行為都是非制度化的”。[14](P.126)另外,壯族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和水平都顯得比較低。學者朱少雄和劉汶認為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雖然廣西壯族地區的大部分公民都參與過基層民主選舉等政治活動,但是他們參與政治活動的次數仍然偏少。其二,廣西壯族地區真正具有明確的政治參與意識的公民甚少。“在很多情況下,很多人是無意識地進行了政治參與,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政治參與。在他們的深層次意識中,并沒有政治參與的意識和動機,更沒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和義務感。”[14](P.127)其三,由于缺乏明確的政治參與意識,壯族地區民眾的政治參與主要是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時,為了保護利益而產生的一種類似“刺激—反射性”行為[14](P.127)。
六、當代壯族政治文化的發展趨勢
上述存在問題已經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關注并探索解決路徑。關于壯族的“民族區域自治”程度不足的問題,一些專家、學者呼吁廣西進一步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自治權和自主權,并提出一些措施。比如,2010年5月,以梁庭望教授為首的全國120位壯族專家學者聯名發表了致溫家寶總理的《關于盡快開設廣西壯族自治區壯語衛星電視頻道的建議信》,信中提到“開設壯語衛星電視頻道是國家法律賦予壯族人民的權利”。如果相關措施得到落實,壯族的“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地域型政治文化成分將進一步得到增加。
關于壯族政治參與程度不足的問題,這問題與我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可以預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深入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縱深推進,壯族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水平將逐步得到提高,壯族民眾將逐步轉變成現代公民,壯族公民社會將逐步形成,壯族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與水平將大有提高,壯族政治文化中的參與型政治文化成分將日益濃厚。
參考文獻:
[1]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王惠巖.政治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M].馬殿君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潘春風.對古老壯族文化傳統的現代化探討[J].廣西民族研究,1988(04).
[5]夏雨.壯族文化討論綜述[J].廣西民族研究,1988(04).
[6]李富強.壯族是創造的嗎—與西方學者K. Palmer Kaup等對話[J].桂海論叢,2010(02).
[7](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轉引自梁庭望.壯族文化概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8]黃現璠.廣西壯族簡史[M].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轉引自梁庭望.壯族文化概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9]梁庭望.壯族文化概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
[10]張聲震.壯族通史[M].民族出版社,1997.
[11]李玫姬.右江工農民主政權對壯族政治發展的影響[J].廣西民族研究,2000(02).
[12]《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寫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M].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13]周光大.壯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建設[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14]朱少雄,劉汶.淺析廣西壯族地區政治發展特點[J].法制與經濟,2009(10).
[15](美)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
[16]馬國川.何方:政治民主化潮流第四波[J].財經,2011(8).
[17]陳明凡.越南政治革新的主要績效和基本經驗[J].新視野,2007(3).
[18](美)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劉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