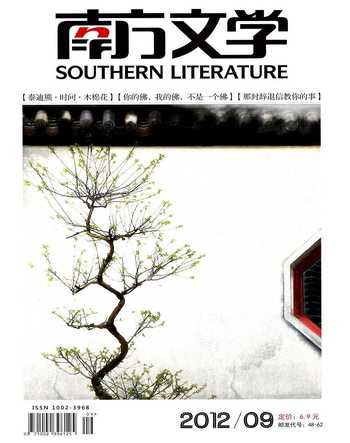大聲
@安妮寶貝:站在窗前觀望收割后的麥田,一輛反向行駛的火車猛然穿梭而過。若提前做好準(zhǔn)備,心里也不會有驚嚇。呼嘯而至的事物,通常都不是意外,而是通常已趨近我們很久,在它前來的道路上進(jìn)行了很久。如果人的視線不被局限于眼前可見的范圍,就可以見到它的來源和因由。讓你所等待著的人和事,自然而劇烈地來到。
@余華:某天在上海,與《紐約時報》記者巴爾博扎聊起作家這個職業(yè)。我說自己在寫作一部小說時,時刻想著盡快寫完,可是寫完后又有一種失業(yè)般的難過。所以作家這個職業(yè)的特征就是不斷去尋找新的工作,然后不斷失業(yè)。
@麥家:我十七歲離開浙江,四十好幾歲才回來,在外待的時間夠長的啦。我曾以為我都不會回來了,因?yàn)槠春途嚯x曾是我向往的。我一直以為,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個關(guān)注內(nèi)心審美的人,遠(yuǎn)離故鄉(xiāng)和親人,精神上有點(diǎn)兒流離失所不見得是個壞事。無論寫作還是創(chuàng)作,雖不一定是從思念開始,但一定從思念結(jié)束。
@余中先:有時候,文學(xué)翻譯不應(yīng)該去追求華麗,而要堅持原文本來的質(zhì)樸。有的讀者很喜歡漢語漂亮的譯文,認(rèn)為這樣才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xí)慣,而根本沒有想到,原文的風(fēng)格大致是什么樣的。原文中的描寫,如果大致是白菜湯,在翻譯時,你不能把它變?yōu)樯徸痈蚨垢X;原文的土豆泥,你不能變成紅燒肉。
@不加V:有時感覺好像坐了10年的牢。忽然出來了。別的人在挑剔你的衣裳,你的語言,你的舉止,在說你關(guān)進(jìn)去的這些年,外面已經(jīng)是誰誰的天下,誰誰比你更紅了,比你更犀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