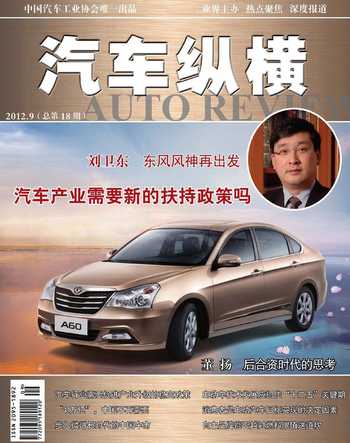車記—親歷·轎車中國30年(節(jié)選七)
李安定

入世后的2002年,中國轎車產(chǎn)量從上年的70萬輛增加到110萬輛,增長了53%!讓全球汽車業(yè)目瞪口呆。從此“井噴”一詞,幾乎陪伴了中國汽車市場整整十年。
12億人口的中國,每年只賣70萬輛轎車,與年銷量1500萬輛的美國不可同日而語,誰都會看到這中間的發(fā)展空間有多大。對國際汽車大廠商來說,爭奪這其中的甜頭是必然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國際汽車跨國公司的準入限制逐步放開,美國通用、福特,德國大眾、奔馳、寶馬,日本豐田、本田、日產(chǎn),法國雷諾、PSA,意大利菲亞特,韓國現(xiàn)代、大宇、起亞,幾乎全世界主要汽車品牌都在中國找到了合資伙伴。
以前人們關注著,又有誰來到中國?現(xiàn)在懸念沒有了,該來的全來了,汽車“世界杯”轉移到中國舉辦,余下的將是更加激烈的競爭。
新中國的汽車工業(yè)當時已經(jīng)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五十年來,曾經(jīng)是“只有卡車沒有轎車”的汽車工業(yè),是“只有公車沒有私車”的汽車工業(yè),然而在2002年,“全球化”和“轎車進入家庭”,兩大推舉力讓中國汽車工業(yè)發(fā)生了史無前例的大變革,成為中國汽車工業(yè)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開始的分水嶺。人們幾乎轉不過神來,那么多“沒有想到”迎面而來:
一是沒有想到轎車進入家庭的勢頭會如此迅猛,老百姓長期被壓抑的購買力釋放出來,市場出現(xiàn)“爆發(fā)式”行情。春節(jié)期間,北京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前的馬路被云集的選車者完全堵死。當時北京交管部門平均每天辦理新車上牌500輛,光是1月15日這一天,就上牌708輛。各企業(yè)推出新產(chǎn)品的頻率加快。一年里,三十多款新型轎車令人眼花繚亂。賽歐、夏利2000、派力奧、POLO開創(chuàng)了緊湊型家庭車細分市場;年中,中華、寶來1.6、西耶納問鼎中檔車市場;年末,威馳、索納塔、嘉年華、高爾夫、千里馬挾強勁的宣傳攻勢而來。盡管中國老百姓的汽車消費還遠不成熟,但是終于第一次可以在市場上像選購彩電一樣選購轎車了。
二是沒有想到2002年轎車各廠家的價格戰(zhàn)一觸即發(fā),并且立刻短兵相接。2002年1月29日,菲亞特小型車派力奧在南京投放的當天,夏利2000和賽歐宣布降價,雙雙跌破10萬元,南京菲亞特董事長恰巴和總經(jīng)理茅曉明在投放儀式前緊急研究對策,當晚宣布派力奧1.3升基本型以84900元的最低價迎戰(zhàn)。1月份的頭20天,單車降價一萬元以上的轎車就有富康新自由人、海馬、紅旗、賽歐、羚羊等。重慶奧拓和吉利分別以3.8萬元和2.9萬元創(chuàng)下主流車型和新生代的最低價格紀錄。持幣待購的老百姓終于放開了錢袋,轎車銷量的八成以上為私人消費,兩三年前這個比例想也不敢想。
三是沒有想到跨國公司熱衷的不是出口整車,而是紛紛進入中國合資建廠。“準入”變得平等,世界汽車“6+3”格局中幾乎所有的跨國公司都在中國找到了合資伙伴,中國和國際汽車業(y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福特集團首席執(zhí)行副總裁馬克·菲爾德對我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均GDP已經(jīng)接近發(fā)達國家,總人口相當于英國,而英國的汽車銷售量在歐洲排名第二。歐美一些大集團,在中國開拓市場,往往作一二十年的戰(zhàn)略考慮,他們看中的是2015年前后的潛在市場。
四是沒有想到困擾汽車工業(yè)多年的頑癥——“散亂差”的產(chǎn)業(yè)結構正在得到改觀,依照市場規(guī)律進行的兼并重組取得突破性進展。上汽集團持股韓國大宇10%,開創(chuàng)中國汽車工業(yè)進入世界汽車資本市場的先河。上海通用作為一家合資企業(yè)以50%的股權重組煙臺大宇,更創(chuàng)造了國內汽車兼并的新模式;東風集團與日產(chǎn)的全面合作,不但獲得轎車新的增長點,更為主導產(chǎn)品載重汽車的崛起贏得了新契機;一汽兼并天汽,進而與豐田聯(lián)手。沈陽、廣州、南京、重慶、北京、寧波等一批獨具實力和特色的轎車基地與三大集團比翼齊飛,形成3+N的新格局。
盡管如此,“爆發(fā)性行情”當時還只是轎車進入家庭消費的導入期,只是“點”上而不是“面”上的旺銷。“面”上多數(shù)中小城市,轎車私人消費遠遠沒有成為汽車消費的主流。在內地城市,普通市民買私家車甚至會被視為露富,怕單位和鄰居懷疑錢的來路不明而卻步。我看過湖南衛(wèi)視的一檔節(jié)目,說的雖然是家庭轎車,可是主持人問及幾位嘉賓,家里買了車沒有?剛才還說得熱熱鬧鬧的嘉賓們頓時變得支支吾吾。
說是“導入期”,企業(yè)還在市場的增量上“跑馬占地”,真正的競爭還沒有開始。當時我提出中國消費市場的“金字塔”理論:產(chǎn)品價格每往下走一個臺階,主流消費群體的底座面積就會呈幾何級數(shù)增加。家轎普及期的到來還有待于轎車在車型、價格方面繼續(xù)走下“金字塔”。如果普及到了金字塔基座的鄉(xiāng)鎮(zhèn)一級,市場之大恐怕將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2002年,幾個大城市中熱銷的主流車型價格在8萬~15萬元之間,打開更大市場的車型價格恐怕在5萬~10萬元才更有沖擊力。
我曾經(jīng)把家庭轎車比作“踮起腳才能摘到的果子”,但是人均GDP3000美元的城市和GDP1000美元的城市,老百姓能夠“摘到的果子”無論車型和價位必然有很大不同。我去天津開會,看見街上跑的大部分汽車還是久違的“小面”。距離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卻仿佛回到十年前,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