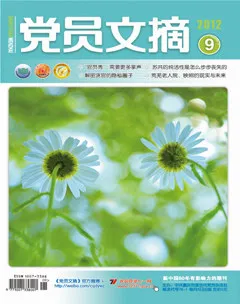七彩人生
李斐然
在過去40年里,威廉·菲茲西蒙斯親手為哈佛大學(xué)挑選每一個本科生。可當(dāng)年他試圖敲開哈佛大門的第一個回應(yīng),是一句響亮的“不可能”。
那是上世紀60年代,哈佛還被認為是一所“為精英階層量身定做”的大學(xué)。沒有人相信窮人家出身的威廉能夠上哈佛,連他的老師都拒絕為他寫推薦信,并極力勸道:“那地方不屬于我們,你不可能融入哈佛的。”
然而他們沒有料想到的是,威廉不僅進了哈佛,還留在哈佛,成為招生“最高長官”,并最終改變了哈佛招生錄取的面貌,讓這所名校從那些不起眼角落里,接納了更多像他一樣被認為“不可能”的人。
如今,哈佛大學(xué)招生辦公室已經(jīng)可以驕傲地在公文中寫道:哈佛以能夠給予每個人公平機遇為特色。而推動這件事的威廉,也被哈佛老校長盛贊為“大學(xué)的良心”。
到底什么樣的人能夠上哈佛?
在美國乃至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想要從威廉那里知道:作為哈佛招生錄取的最高把關(guān)人,你想要什么樣的學(xué)生?
威廉總是看著那些期待的眼睛說:“對不起,其實我們并沒有公式化的規(guī)則。能夠讓身邊的人變得更好的人,就是我想要的人。”
考過SAT(學(xué)術(shù)能力評估測試,相當(dāng)于美國的“高考”),提交申請資料,就可以成為哈佛入學(xué)申請者。所有申請者的資料會被分工不同的四個人仔細研讀,然后,包括威廉在內(nèi)的五人評審小組會召開討論會,每個申請者至少討論一小時。最后,由評審小組全體投票決定。
“你所獲得的學(xué)術(shù)成績很重要,但是我們也會考慮很多其他指標——社區(qū)參與、領(lǐng)導(dǎo)能力、工作經(jīng)驗等。”威廉說,“我最期待的是打開每個人的申請文件夾,看到一個個人生故事,它們是如此真實。”
為了“討好”這位哈佛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錄取官,人們給他寄來各式各樣的禮物——餅干和棗泥糕,DIY版的《時代》周刊,還有人送來一個畫有自己頭像的大圓盤。
在一次校園電視臺的采訪中,男主持人揚著眉毛打趣問威廉:“說真的,有沒有人給你施點美人計?”
“這倒是沒有,這就是原則問題了。”威廉大笑著回答,“另外,請千萬不要再給我寄黑巧克力了,我的家鄉(xiāng)盛產(chǎn)巧克力,這招對錄取根本沒用。”
對于那些絞盡腦汁吸引錄取官注意的學(xué)生,威廉建議道:“你不需要去哥斯達黎加,你也不需要去國外做什么轟動的事情,如果去麥當(dāng)勞打工可以融入社會,這也是個好主意。”
在華盛頓的一次招生會議上,當(dāng)一個驕傲的母親在威廉面前夸夸其談,稱贊自己的兒子“非常積極進取、勤奮好學(xué)、有真正的學(xué)者風(fēng)范”時,這位高個子男人只是彎下身,認真地問躲在母親背后沉默的孩子:“你平時喜歡玩什么?”
去哈佛吧,
但是不要丟掉你的靈魂
對小時候的威廉來說,哈佛完全是陌生的。他的父母都沒上過大學(xué),全家的生計就是靠經(jīng)營一個加油站及旁邊的小便利店。那時候沒有人想到,在這條窮人住的街上會走出一位哈佛畢業(yè)生,甚至最終給哈佛帶來了改變。
高個子的威廉很有運動天賦,是學(xué)校里的曲棍球明星。當(dāng)時大家對他的最高期待,就是做一名職業(yè)曲棍球手。
雖然哈佛大學(xué)距離威廉的家只有15英里,但在他看來,卻感覺“有半個地球那么遠”。對這個窮人區(qū)的孩子來說,生活就是每天睜開眼睛后,開始為當(dāng)天的面包而努力。
高中畢業(yè)前夕一次偶然得到的參觀機會,讓威廉見識了15英里外的哈佛生活。第一次踏進哈佛校園,威廉吃驚地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世界:“我覺得這里不是和家里差了15英里,而像是差了3000英里。”
回到家里,威廉作出了自己的決定:到哈佛大學(xué)讀書。
這樣的想法嚇到了他身邊的人。“不可能!”連續(xù)兩位老師拒絕為威廉寫推薦信,并且他們極力勸他不要申請哈佛:“你會因為貧窮而被排斥,格格不入,被迫退學(xué),在那個只屬于富人的地方,失去自己的靈魂。”
“就像是每一個青春期的叛逆少年,當(dāng)時的哈佛對我來說就像是禁果,越是這樣,我的好奇心就越是促使我前進,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樣子。”威廉說。
威廉說服了歷史老師羅伯特·奧布萊恩為自己寫推薦信。最終,他憑借自己優(yōu)異的成績和突出的曲棍球特長被哈佛大學(xué)錄取。
威廉要去“不屬于自己的哈佛”了。在他踏上行程之前,奧布萊恩送給他一個裝裱起來的紀念框,上面寫著一句拉丁語,大意是“不要讓痞子把你打敗”。
在哈佛,繼續(xù)做我自己
在威廉還沒搞明白“痞子”指的是哪些人的時候,他先被這個陌生世界嚇了一跳。這個1962級哈佛新生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跟自己住了18年的小屋不同,這里寬敞豪華的餐廳里擺著閃亮的餐具,學(xué)生休息室里鋪著木地板,墻上掛著鍍金邊框的畫像,伸手可及的地方都是皮質(zhì)家具。與他一同到達的同學(xué)們穿著時髦的服裝,相互打量著彼此昂貴的花呢夾克、絲綢領(lǐng)帶和駝絨大衣。
在這一堆衣著華麗的富家子之中,威廉身上還穿著高中時候的卡其布外套。
威廉發(fā)現(xiàn),自己的女性同學(xué)少得可憐,大概只有八分之一的比例,更不要說不同膚色的少數(shù)族裔了。
與此同時,威廉也開始明白為什么他的老師會口口聲聲宣稱這里“會讓人失去靈魂”。威廉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他的同學(xué)走到他身邊,扭著脖子斜著眼,向他的衣服里面看,想要瞥到標簽。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這里保持我的身份,繼續(xù)做我自己。”威廉說。
當(dāng)同學(xué)們在那些會費昂貴的學(xué)生俱樂部暢談未來的時候,威廉加入了曲棍球校隊,代表學(xué)校打贏了幾場比賽。同時,他廣泛涉獵,選修了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和心理學(xué),獲得社會關(guān)系專業(yè)學(xué)士學(xué)位。后來他又在教育學(xué)院攻讀了碩士和博士學(xué)位。
畢業(yè)前,威廉“跟每個普通學(xué)生一樣,四處發(fā)簡歷,找工作”, 但最終,威廉聽從導(dǎo)師喬治·戈爾瑟斯的意見,進入哈佛大學(xué)招生辦公室工作,并于1974年開始擔(dān)任招生負責(zé)人。
“我被這份工作背后無窮的機遇迷住了。”威廉說,“想想看,你可以為身處世界某個角落的學(xué)生帶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遇,為那些適合的人打開哈佛的大門,讓他們能夠享用這所大學(xué)所能提供的資源,因而有更好的機會把世界變得更好。”
撼動美國高校
錄取制度的變革
1986年,威廉升任招生辦公室主任,兼管獎、助學(xué)金事宜。威廉終于有機會開始推進自己籌劃已久的改革——中止哈佛大學(xué)的提前錄取制度。
用哈佛前校長德里克·伯克的話來說,這項制度“讓占優(yōu)勢的人占盡了便宜”,它大大增加了富裕學(xué)生的錄取機會,是富裕家庭通往名校的便捷門。
威廉決定要關(guān)上這扇門。
然而,說服人們廢除這項已實行數(shù)十年的制度十分困難。直到2006年,伯克校長才終于宣布,哈佛愿做全美第一個徹底取消該制度的大學(xué)。
這一決定震驚了美國教育界。美國游說機構(gòu)“教育管理”的執(zhí)行理事說:“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聽到時我眼里含著淚水,幾乎要哭出來了。”
在打破特權(quán)的同時,威廉在任的第二把火,是建立起更為有力、覆蓋面更廣的獎、助學(xué)金制度,給予貧困家庭更多補助。他每年指派40多名錄取官,飛往美國乃至世界各地,讓那些受困于“不可能”的年輕人——從美國阿巴拉契亞山區(qū)牧羊人的女兒,到緬因州賣龍蝦的老板之子,甚或是中國青藏高原的藏民——意識到自己有機會改變?nèi)松?/p>
威廉不僅認識每一個由他錄取的學(xué)生,還在默默關(guān)注著他們。這個當(dāng)年被同學(xué)偷看衣服牌子的校友,為他的學(xué)弟學(xué)妹們設(shè)立了一項“秘密基金”。
這像是一個神秘組織,由威廉所指定的助學(xué)金工作人員秘密操作。他們有一份保密名單,上面是家境貧寒學(xué)生的通訊方式。當(dāng)這些學(xué)生遇到說不出口的窘迫時,威廉的神秘組織就會給他們寄去禮物——一張校園新年音樂會的門票、一張突發(fā)急病需要的支票、一套面試需要穿著的正裝、一件冬天保暖的外套,甚至是一張回家的機票……
一切都是秘密的,沒有人公開發(fā)送名單,不涉及自尊問題,這就是從不露面的威廉送給每個哈佛貧困生的禮物。
他重新定義了哈佛大學(xué)
其實,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每個走進哈佛的學(xué)生,都會收到來自威廉的禮物。
其中一項禮物,是一筆資助“間隔年”的獎學(xué)金。威廉鼓勵學(xué)生申請,拿著這筆錢,用一年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比如到全世界旅行,去接觸完全不同的人生。
“盡情地去玩耍吧,去看看世界的樣子,不要一心做個‘補習(xí)戰(zhàn)士,我可不希望你們的引擎在到達哈佛大門前,就已經(jīng)耗得沒油了。”威廉說,“也許你會在這一年發(fā)現(xiàn)你的‘人生節(jié)點,從而更明確回到哈佛后,你想要得到什么。”
“在哈佛,我不知道誰是貧困生。每個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一樣讀書,一樣旅行。我們唯一的不同,大概只在于接下來,你要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哈佛學(xué)生安德里安·斯博恩說。
“回顧這么多年來哈佛的改變,景象實在令人振奮——這里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女性、少數(shù)族裔學(xué)生,以及原本人生軌跡在另一端的人們。”威廉說,“能夠在過去幾十年參與到這場錄取改革,把更多的人拉入可以實現(xiàn)夢想的行列,我感到很榮幸。”
“威廉改變了人們對哈佛的看法。”伯克這樣評價威廉,“對于哈佛,人們有種印象,這里是所精英大學(xué),到處都是來自富人家、上得起預(yù)備學(xué)校的書呆子。但威廉卻成功地打破了這一禁錮,讓你發(fā)現(xiàn)在這么牢不可破的制度下,還有人能頂著重重壓力,生生闖出一條路。”
美國媒體也評論說,“威廉重新定義了哈佛大學(xué)”,這位被稱為“哈佛大學(xué)的良心”的人,同時也是“整個美國大學(xué)招生錄取界的良心”。
當(dāng)然,威廉40年的堅持也“得罪”了不少人。校園電視臺采訪他時,男主持人忿忿地抱怨:“嘿,哥們,咱們說點實際的,難道你就不能給我們多招幾個漂亮姑娘嗎?艾瑪·沃特森,演《哈利·波特》電影的那個,要是招她來,你不也省得滿世界跑去宣傳招生嗎?”
威廉仰著頭哈哈大笑,認真地回答道:“可是我只看才華。”
(摘自2012年6月13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