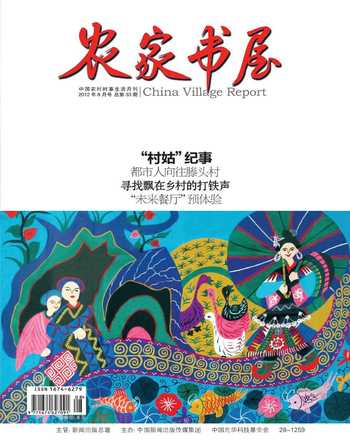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落實公民權益不容拖延
胡明剛



當下進入“世界工廠”務工的農民工已經不是那些曾經吃過苦、挨過餓、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老一代農民了,隨著這批農民工逐漸返回農村,他們在工廠中的位置大多被他們的子弟所代替,這些年輕的中學、中專或職校畢業生是一代受過較好教育的農村青年。
新生代農民工有何特點?“這些年輕人在艱難地適應工廠單調重復的生產節奏之前,就已經在學校生活中養成了都市生活方式。他們廣泛使用互聯網、工余時間與同伴好友頻頻聚會,進入各種娛樂場所消費。都市生活方式的養成決定了他們中多數人的發展預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聯合組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在最近發布的調研報告《困境與行動: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民工生產體制”的碰撞》中,這樣概括新生代農民工的特質。
課題組于2011年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三個農民工相對集中的區域,分別選取廣州、上海、北京等三個大城市,對新生代農民工開展了問卷調查。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中所在城市流動人口的性別、產業、職業、區縣分布進行配額抽樣,共采集有效問卷1259份。為進行縱向比較,調查還涵括了老一代農民工的部分樣本,新生代和老一代樣本數比例約為4:1。最終的樣本分布基本符合預定的抽樣方案。除了問卷調查,課題組還在珠三角進行了長期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收集了農民工集體抗爭的若干一手個案材料;此外,課題組還收集了國家統計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關于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題研究和相關數據,進行綜合比較研究。
難以化解的矛盾
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新的社會群體特征:他們與城鄉、企業、國家的關系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超過一半人接受過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他們更為徹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如消費模式發生轉變、社會關系逐漸由親屬老鄉網絡轉向同學同事網絡、普遍使用互聯網、認同城市價值觀等等。
以互聯網的使用為例,新生代農民工中有85.7%的人會上網,平均每天的上網時間長達2.7小時。他們自身的發展定位也主要放置在城市,打算未來繼續在城市而非老家發展的比例高達58.4%。對城市生活的適應和接納同時意味著對農村老家的疏離,他們中有44%的人完全沒有務農經歷。在企業中,他們也不再僅僅是埋頭干活,掙錢吃飯,而是對規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義和個人發展前景產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調查表明,他們比老一代更加厭惡“農民工”這個提法,重新界定自身與國家的關系,獲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也更為強烈。這使得國家通過司法規制將農民工的維權行為限定在個體的、基本權利范圍內的傳統做法難以為繼。新生代農民工所具有的新特征與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并延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矛盾。
“農民工生產體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與“工廠專制政體”。“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等安排交由他們在鄉村地區的老家去完成,城鎮和工廠只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維持”的成本。國家通過一系列規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戶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對勞工集體組織爭議權利的約束等固化了這種制度。
“工廠專制政體”主要表現為生產過程中高強度、長時間的簡單勞動、微薄的工資待遇、嚴苛的管理制度、骯臟、惡劣與危險的工作環境等。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時,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這一點上與老一代相差無幾。他們中有13.6%受過工傷,7.6%得過職業病。如果考慮到外出務工時間因素,就可看出,他們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傷害。此外,他們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還低574元。
新生代農民工新的社會群體特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像老一代那樣采取“候鳥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鄉之間,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長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整個過程。當這個趨勢由于各種制度約束而難以實現的時候,必定產生新工人對舊體制的巨大不滿。體制不改變,則沖突在所難免。
逐步廢除“農民工生產體制”
調查組認為,逐步廢除“農民工生產體制”應是改革進一步深化的一個基本方向。隨著我國中等教育普及,勞動力構成逐漸改變,老一代、低學歷的農民工逐步退出勞動力市場,新生代、受過中高等教育的農民工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我國當代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他們與現行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必定發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沖突。“農民工生產體制”已經難以維系,必須加以破除,而這正是調整勞動關系,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
調查組建議,在工廠中落實農民工的“工業公民”身份,在城市中落實農民工的“社區公民”身份。“工業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廠中不僅僅是勞動者,受到經理層的管理和約束,而且還享有“公民權利”,有權就自己的工資、工作條件和其他相關問題提出訴求。
工業公民權利包含很多內容,但在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議價機制。在“農民工生產體制”中,集體議價機制的缺失導致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長期以來處于低水準狀態,難以反映市場用工、物價水平、企業利潤等方面的變化,阻礙了工人通過程序正義實現自身利益。
課題組認為,從現在開始逐步為新生代農民工著手落實“工業公民”的權利已有可行條件:第一,農民工自身素質已有極大的提高。很多工人開始利用互聯網和各種渠道獲取企業和行業相關信息、查詢法律知識并認真汲取其他企業的工會運作和集體談判經驗。
第二,基于經濟訴求的行動更容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狀態。在課題組搜集到的新生代農民工集體行動案例中,經濟目標都非常明確,不符合企業利潤狀況的加薪要求和激進的政治訴求微乎其微。
第三,法律和市場是農民工行動和談判的兩根準繩。工人在行動過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動方式有沒有違法;在提出訴求和進行集體談判時,往往將物價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資水準、市場用工狀況、企業利潤等指標作為最重要的依據。集體議價機制的實現,將是實現程序上的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途徑。同時,由此帶來的收入分配結構的改變還將促進消費,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社區公民”身份主要指農民工有權享受在地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包括農民工及其子女有權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醫療等在內的各種公共服務。完全實現農民工的“社區公民”權利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只能逐次推展,但是從現在開始就要努力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慮和各項具體的政策設計。
近幾年農民工與本地人之間爆發的一些劇烈的群體性沖突已經表明,為新生代農民工落實此種“社區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已是一項不容拖延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