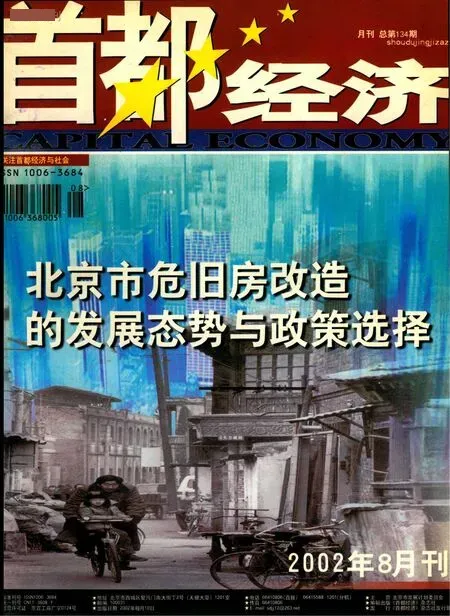現階段存貸比宜放寬不宜取消
郭世邦
只要商業銀行盈利模式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只要商業銀行依然存在貸款沖動,監管層就不會輕易取消存貸比管理
從去年以來,一些專家和部分商業銀行人士強烈呼吁監管部門取消銀行存貸比管理,媒體上也不斷有類似的報道或觀點出現,其訴求基本上集中在是否要徹底取消銀行存貸比管理,或是放松存貸比指標,尤其是改變75%存貸比指標值上。
我認為,短期內取消存貸比管理幾無可能,適當放寬存貸比指標是一個可能選擇,但何時放寬、放寬到什么程度,仍取決于監管者甚至高層決策者的意愿。
存貸比管理的利與弊
1994年,人民銀行決定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試行限額下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1998年人民銀行決定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控制,改為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全面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
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是對銀行的資產和負債規定一系列的比例,從而實現對銀行資產控制的一種方式。通過資產負債比例管理,使銀行資產實現合理增長,達到穩健經營,消除和減少風險的目的。
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是《商業銀行法》的核心內容之一。人民銀行當年公布了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10項監控指標和6項監測指標,其中存貸比指標作為10項監控指標之一,而且根據當時的情況,規定了這個指標值不能超過75%。對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來說,這個指標還要更低一些。
之所以存貸比指標成為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重要指標之一,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之前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信貸控制都是以限額管理為主,無論商業銀行的存款多少,只要不突破限額,就可以放貸款。各家商業銀行對分行管理也是如此。以至于有些分行的貸款大于存款,比如當時的東北幾家分行,而有些分行的貸款遠遠小于存款,比如北京分行等。限額管理的不足之處不必多說,但好處是直接,易于管理。一旦取消限額管理,人民銀行就無法準確預知全年的信貸投放量,所以在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指標中,列入了存貸比指標,雖然相對于限額而言,存貸比指標是一個彈性指標,但人民銀行最初在確定各家商業銀行具體存貸比指標時,一般都采取“倒推法”,即先測算全年信貸投放量以及預估存款增量,然后計算出存貸比。
二是銀行的盈利模式也決定了要實行存貸比管理。在1998年取消限額管理時代,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于存貸利差和存放人民銀行所得利息。如果一家銀行的存款多,貸款少,就意味著它支出多,收入少,銀行的盈利能力就較差;如果一家銀行的存款多,貸款也多,就意味著它支出多,收入也多,銀行的盈利能力就很好。由于我國的存貸款利率是以人民銀行公布的基準利率為基礎,各商業銀行間的凈息差基本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商業銀行的利潤就與可貸資金的數量高度正相關。因此,對銀行而言,存貸比自然越高越好。但從風險角度講,存貸比例又不宜過高,因為銀行還要滿足存款客戶日常現金支取和往來結算的需求,這就需要銀行留足一定的備付金(現金和在人民銀行存款),如存貸比過高,這部分資金就會不足,有可能導致銀行出現支付危機。所以銀行存貸比例不是越高越好,應該設定一個監管比值,這就是存貸比指標,1998年以來規定的商業銀行最高存貸比例一直為75%。
在既定的存貸比下,如果商業銀行的存款額越大,其可貸資金的額度也就越高,這樣存款就成了各家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的生命線。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由于網點眾多,且具有品牌優勢,其吸收存款的能力比較強,因此其存貸比相對較低。但對于不具有網點優勢和品牌優勢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尤其一些地方商業銀行,本身又想做大規模,其吸收存款的壓力就比較大。所以,這些銀行對取消存貸比管理的呼聲就比較高。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商業銀行呼吁取消存貸比指標,主要還是為了自身利益,更多出于放款沖動。
當然,存貸比管理的弊端也是不言而喻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它限制了貨幣乘數的擴大,尤其限制了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比如在75%存貸比控制下,只有當貨幣乘數在4以下時,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才能有效發揮,超過4之后,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就只能是調節流動性,而不能傳導貨幣政策效應。
現階段取消存貸比的
可能性不大
一是存貸比管理和指標受法律保護。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了商業銀行實行存貸比管理,且明確存貸比指標為75%,要取消存貸比管理,或放松75%存貸比指標,就必須修改商業銀行法,而這并非一朝一夕、說辦就辦的事。
二是監管部門也有不同聲音。商業銀行呼吁取消存貸比,大多出于自身放款沖動,有些專家呼吁取消,是考慮到目前放款不足,試圖通過取消存貸比,給商業銀行松綁,以便向實體經濟多投放貸款,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但事實上,目前貸款投放量低的原因不是商業銀行不愿放款(當然也有部分銀行受制于存貸比而不能放款),而是實體經濟有效信貸需求不足,單純依靠放松存貸比,是解決不了貸款投放不足的問題的。另外,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日前也在金融時報撰文表示,目前單純依靠信貸增長助推經濟不可持續。所以,即使巴塞爾協議III中有很多指標有助于解決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但在目前情勢下,監管部門也沒有意愿取消存貸比管理。何況從總體而言,我國銀行業的存貸比并未達到75%,75%并沒有對銀行業整體放款構成限制,只是對局部銀行構成了限制,而這也恰恰是銀行差異化監管的要求。
三是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并未改變。從1998年到2012年,整整過去了14年,但商業銀行依靠息差獲取利潤的盈利模式并未完全發生改變,商業銀行80%以上的收入仍來源于利息,有的銀行在90%以上。去年以來,隨著外界對銀行各種收費的質疑,銀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依靠中間業務獲取利潤的動力受到了較大抑制(雖然商業銀行獲取這種中間業務收入的途徑和方式方法有待商榷,但一刀切式的打擊方式也是不可取的),銀行重回依靠息差收入時代。在這種情勢下,商業銀行放款沖動將比14年前更加強烈,尤其是那些上市銀行,甚至有可能為了利潤放松風險,鋌而走險。如果在此時取消存貸比管理,有些商業銀行就會借機盲目擴張資產,從而有可能導致支付危機的出現,甚至有可能由局部支付危機引發全面金融危機。君不見,在人民銀行允許存款利率上浮10%之后,就有很多商業銀行將其掛牌利率一浮到頂,就是這種沖動的表現。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源于存貸比指標限制的結果,如果取消存貸比限制,商業銀行完全可以從金融市場上獲得資金去放款,就不會盲目地爭搶存款了,這雖然也是個說法,國外的很多商業銀行也都是這么做的,但要知道,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往往具有同向性,一緊俱緊,一松俱松,當你真正需要錢時,可能別人也都需要錢,這樣一方面有可能市場上根本無錢可借,另一方面即使有錢可借,其成本也可能比高息攬存還要高。這并非危言聳聽,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由于銀行之間的信任出現危機,不僅同業拆借市場資金利率高企,而且幾乎無法從同業拆借市場拆借到任何資金。
再借鑒一下信貸資產證券化過程,就知道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去年3月份兩會期間,多家商業銀行大佬強烈呼吁管理層盡快推出信貸資產證券化,而今年管理層真的推出了,響應者卻寥寥,為何?因為去年各家商業銀行都受制于貸款規模有限而不能充分放款,所以他們希望把一部分貸款轉出去,以便騰挪規模;而今年貸款投放不足,誰又愿意把貸款轉出去呢?這就是同向性。
也有人說,在今年這樣貸款投放不足的年代,放開存貸比,讓商業銀行加大貸款投放,不正好支持了實體經濟嗎?如果果真如此,倒也是一件好事。但正如前面所言,今年貸款投放不足不是銀行沒有投放意愿,而是實體經濟對信貸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從實體經濟層面解決問題,光靠銀行一廂情愿,或單純依靠釋放流動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何況,今年是貸款投放不足年,即使放寬存貸比,應該也不會帶來什么風險,但如果明年實體經濟對貸款需求過度呢?難道那時我們再恢復存貸比管理嗎?
所以,只要商業銀行盈利模式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只要商業銀行依然存在貸款沖動,監管層就不會輕易取消存貸比管理(除非中央高層決策),至多對各行存貸比做靈活調整,比如調高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貸比指標,甚至允許部分商業銀行存貸比突破75%紅線(這還不知道是否需要人大解釋或授權呢?)等。
(作者單位:深圳發展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