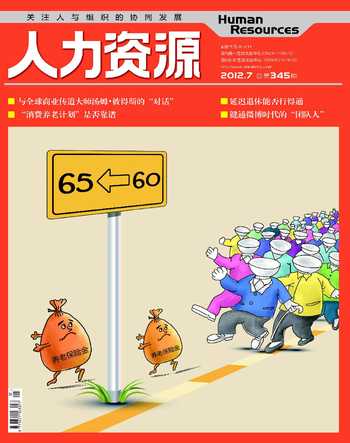應對工傷管理之困
陳敕赫



工傷,顧名思義,就是勞動者因工負傷。表面上看似簡單的工傷,在實踐中卻充滿紛繁復雜的法律規定,以及勞資雙方的激烈博弈。于是,很多用人單位絞盡腦汁,想出了各種辦法來應對工傷成本高、糾紛難處理的問題。
【案例1】:
2007年5月10日,北京鐵路局職工楊某在施工時,被鐵棍擊中頭部受傷,單位對其進行了相應治療。然而回到家中休養的楊某時常感到頭暈、惡心、頭痛、失眠。15日凌晨,楊某突然揮刀砍傷熟睡中的妻兒后自殺身亡。警方委托精神疾病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的結論為:楊某作案時存在嚴重的抑郁情緒,在抑郁情緒影響下發生擴大性自殺。楊妻認為丈夫是頭部受傷造成的外傷性精神病,從而導致自殺,故于25日向海淀區勞動保障局提出申請,要求認定楊某工亡,但勞動部門以“自殘或自殺不得認定為工傷”為由,認定楊某不屬于工亡。
一審敗訴后,楊妻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既無證據證明楊某在頭部受傷后還受過其他傷害,也無證據證明楊某受傷前有精神疾病,應認定楊某自殺時的精神狀態是由于頭部受傷引起的。在該精神狀態下,楊某的自殺行為與工作中受到的頭部傷害存在因果關系,應認定為工傷。故撤銷原判,并要求勞動局重新做出認定。
【案例2】:
2007年3月15日,通州市某公司員工吳某在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經法院調解,吳某與被告達成調解賠償協議,并獲賠38000余元。同時,吳某向所在地勞動部門申請工傷認定并被確認構成工傷。吳某經鑒定構成九級傷殘。
由于該公司未為吳某繳納工傷保險,吳某遂申請仲裁委要求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并終止勞動關系。仲裁委做出支持吳某的裁決,該公司不服提起訴訟。通州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損害的,侵權人已對勞動者(受害人)進行了賠償,并不影響受害人享受工傷待遇,因此對該公司提出的吳某享受工傷待遇時應扣除交通事故侵權人已賠部分的主張不予支持。故判決該公司承擔醫療費、護理費、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合計68000元。
以上兩個案例所反映出的問題,都只是有關工傷問題的冰山一角。下面就結合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以及工傷待遇享受三個方面分析工傷員工管理過程中可能涉及的一些問題。
工傷認定謹防陷誤區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理解,工傷認定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事實上的勞動關系,即受傷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應當建立有勞動關系。這是構成工傷的前提條件;
第二,發生人身損害事實。需要存在人身損害事實,且不包括財產損害和其他利益損害;
第三,人身損害與工作有因果關系。即人身損害需在工作地點、工作時間或因工作原因導致。也就是平時所說的“三工因素”。對此,現行法律也進行了一定范圍內的擴大解釋;
第四,不存在排除性情形。即法律法規規定的自殺自殘、醉酒吸毒、故意犯罪規定的除外情形。
以上條件缺一不可,同時具備方可被認定為工傷。
基于上述規定,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為了規避工傷風險,設計出了各種方式,回避勞動關系的建立,從而規避工傷風險。然而,由于一些用人單位對法律法規的誤解,卻導致了更大的法律風險。
誤區一:協議決定用工性質
有些單位不清楚什么叫勞務工、臨時工,想當然地認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協商好是什么工就是什么工,有的甚至還簽訂相關協議,約定雙方之間是某種勞務關系。一些在家待業人員被召為兼職工、實習生的情形也就屢見不鮮。由于是兼職工、實習生,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會保險,就似乎很正常了。
實踐中存在這樣誤區的用人單位不在少數。其實,不管是兼職工,還是實習生,都有其特定的法律條件,只有符合這些條件,才能構成相關的勞務工種類,而并非跟其編制或者工作內容、工作時間相關。例如,兼職,所需要的條件就是,勞動者必須已經有全日制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余,到另一家單位工作,相對于另一家單位來講,才叫兼職。
可見,勞務關系的界定,并不是通過雙方的協議就可以解決的,其中還需要滿足一些法律規定的前提條件。因此,一定要區分理解清楚,不能想當然地處理,否則就可能因為處理不當,而導致社保未繳,勞動者工傷保險的所有責任就都由用人單位承擔,此時用人單位的損失就非常大了。
誤區二:不簽合同就沒形成勞動關系
有些單位對法律的了解還不是很透徹。認為工傷是跟勞動關系相關的,勞動關系又跟勞動合同有關,于是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理出了一條脈絡,即:簽了勞動合同,才形成勞動關系;形成了勞動關系,才有工傷一說。遵循這個脈絡,要想避開工傷問題,不簽勞動合同就可以了。對于這個誤區的分析,可參考對第一個誤區的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誤區三:心存僥幸,與工傷概率博弈
有些用人單位對不給員工上保險心存僥幸,心想自己都已經實行了這么長時間了,也沒碰到問題。對工傷發生的概率、法律后果和工傷繳納成本相互權衡,覺得可以承受,就擅自決然保持原有的違法狀態。這一種選擇,對于單個程度也不嚴重的工傷案件來說,公司確實能承受,但是有一個隱藏的風險可能被企業忽略了,就是在勞動者當中的“羊群效應”,一旦有員工發生工傷后,提到了社保問題,那么其他員工就有可能集體向公司主張社保權利,這對公司來講,就將是一場“災難”。
誤區四:業務外包給自己的員工
有些用人單位,聽說業務外包可以將所有的勞動法上的風險,包括工傷風險轉移給承包方,于是非常積極地將所有能外包的業務都外包出去了,而選擇的承包方是各部門的負責人。這樣,如果出了什么問題,用人單位可以將責任推給相關的承包人,稱這是外包,與己無關。應該說,業務外包轉嫁風險,是避免工傷風險的一個好方法。但如果使用不當,反而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麻煩”。
《勞動合同法》第94條明確規定:個人承包經營
違反法律規定招用勞動者,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發包方跟個人承包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換句話講,上述這種將業務發包給自己員工的做法,如果這些承包人在履行承包協議的過程中,違法招用勞動者,那么一旦發生《勞動法》上的風險,將由用人單位和承包人共同承擔,而聰明的勞動者往往會選擇向發包方(即企業)主張權利。
所以,不能片面地理解外包轉嫁風險的問題,隨隨便便地外包,只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風險。
誤區五:員工過錯,不應認定為工傷
這在實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勞動者存在操作失誤,或者違規操作導致損傷時,用人單位往往覺得不公平,明明是勞動者自己的過錯,單位已經履行了各種應盡的義務,憑什么還要認定為工傷,憑什么最終還要從單位撈走一大筆錢。這是很多用人單位無法理解的一個問題。
上述這種觀點,是人內心最原始的公平觀念。但是,在現代法治意義上,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也是公平的內涵之一。故在有關工傷保險的規定中,用人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即只要發生了工傷事故,用人單位都應當承擔工傷保險的賠償責任,不能以自己不存在過錯或以勞動者存在過錯為由,來減輕或免除自己的責任。
勞動能力鑒定切勿掉以輕心
工傷認定的完成,可以說是對勞動者人身損害事實的一個定性。而勞動能力鑒定可以說是一個定程度、定量的環節,可以說是工傷流程中最為核心的環節。
勞動能力鑒定是指勞動能力障礙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礙程度的等級鑒定,所以又有人稱之為傷殘等級鑒定。勞動能力鑒定的內容,包括勞動功能障礙等級鑒定和生活自理障礙等級鑒定。
勞動功能障礙等級鑒定,是確認受傷勞動者因工傷使其勞動能力下降的程度。按照規定,勞動功能障礙的等級分為十級,最重是一級,最輕是十級;生活自理障礙等級鑒定分為三級,分別是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受傷勞動者發生工傷,經工傷認定,待治療傷情相對穩定后,若存在殘疾、影響勞動能力的,應進行勞動能力鑒定。確定相應勞動功能障礙等級和生活自理障礙等級后,以此為依據確定其應當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
實踐中,除了個別工傷勞動者消極躲避、拒絕鑒定的情況外,很少出現勞動能力鑒定方面的糾紛。
對于勞動能力鑒定,《工傷保險條例》是有明文規定的。對于拒絕進行勞動能力鑒定的勞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停止其停工留薪期待遇。但是,此處需要注意的是,在處理此類問題時切勿掉以輕心,特別需要注意將通知受傷勞動者進行勞動能力鑒定的回函保留好,以備不時之需。
落實工傷待遇成“重災區”
經過工傷認定和勞動能力鑒定后,就面臨著工傷保險待遇計算的問題了,只需按照法律法規規定確定承擔方和數額即可。但是,如果用人單位未繳社保,則所有工傷保險責任都將由用人單位承擔。由于工傷保險待遇涉及到了用人單位成本支出的問題,所以實踐中碰到的問題還是不少的。
問題一:停工留薪,遙遙無期
少數受傷勞動者了解到“工傷停工留薪期工資待遇不變”的規定后,不斷開具休息證明,以此為名,賦閑在家。無需工作,還能領全額工資,何樂不為?加之醫院開證明簡單無比,有此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停工留薪期的時間,應當由已經簽訂服務協議的治療工傷的醫療機構提出意見,經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后通知有關單位和工傷勞動者。如果該
勞動者傷情嚴重或者特殊情況需要延長期限治療,則需要經過市級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方可適當延長,但最多再延長12個月。
可見,停工留薪期的長短,并不是受傷勞動者說多久就多久的,也不是說勞動監察大隊說延長就可以延長的。
問題二:工傷私了,是否有效
對于這個問題,立法并無明文規定,而在司法實踐和理論界卻一直存在爭論。主要有如下三個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協議無效,理由是工傷認定、賠償是國家強制執行的范圍,協商私了顯然屬于違反了強制性法律規定。
第二種觀點認為協議有效,理由是勞動法相關的規定,賦予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自行和解的權利,如果賠償額合理合法,協議應屬有效。
第三種觀點認為,如果用人單位在與勞動者簽訂私了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侵犯國家利益的情況,勞動者可以主張該私了協議無效;如果私了協議存在重大誤解、顯失公平,則勞動者可以向法院申請撤銷或者變更該私了協議;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形,應當認定該私了協議有效。也就是說,這種觀點結合了民法和勞動法的相關規定。
對此,筆者認為,參照《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認定其效力應該是可取的。
首先,工傷私了協議也屬于一種合同契約,而且其并不像勞動合同那樣有什么特殊性,所以應該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
其次,協議無效,只會將法律關系復雜化,出現累訟等增加司法成本的情況。
再次,如果直接認定工傷私了協議有效,那么就容易出現用人單位濫用其強勢地位,肆意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情形。
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參照《合同法》的有關規定來執行。即原則上該私了協議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勞動者能夠舉證證明簽訂協議時,用人單位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的,勞動者可以主張該私了協議無效,同時主張相應的工傷待遇;如果員工感覺該私了協議存在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則可以向法院申請撤銷該協議。
問題三:侵權與工傷競合,如何賠償
被第三者侵權,同時構成工傷的員工,如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
對此,很多地方立法開始對這個問題做出一些規定。但是,由于各地對此問題的認識不同,兩種觀點皆而有之,各方處理各持己見:
第一種觀點,認同“補充賠償”模式。理由為民法調整受損應遵守“填平原則”,獲得“雙倍賠償”就有不當得利之嫌了。該觀點以《上海高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賠償與第三人侵權損害賠償競合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四川省《關于貫徹<工傷保險條例>的實施意見》,以及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為代表。
第二種觀點,主張采取“雙倍賠償”的模式。理由為《勞動法》屬社會法,而非民法,故法律關系受各自的法律調整。此觀點雖暫無地方立法予以明確,但不少地方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卻均采取了此做法。
筆者認為,地方有相關法規政策的,結合實務環境自然按照地方的規定執行即可。對于當地沒有相關法規政策對此進行規定的,則相對比較麻煩,從理論上來講,這其實是一個權利競合的問題,但是因為有了跨越法律屬性的爭議,已經難以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只能依附于所在地的實務操作口徑。當然,筆者在這里也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勞動部門能盡快協商配合,對此問題進行立項調研,給出一個明確、統一、操作性強的依據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