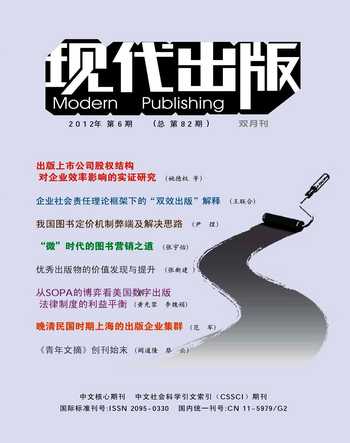晚清民國時期上海的出版企業集群
范軍
摘要:企業集群是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的相關產業或某特定領域內大量互相聯系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及其支持機構在該區域空間內的集合。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出版業形成了自己的企業集群,產生了人才集聚效應、學習與創新效應、制度效應。這種企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經驗,至今對于我們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晚清;民國;上海;出版;企業集群
亞當?斯密很早就注意到了企業集群這種現象。他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企業集群”的概念,但進行了實質性論述。在他看來,由于社會分工,產生了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質的中小企業以完成某種產品的生產聯合為目的而結成的群體。韋伯則在企業集群的概念中引入集聚因素,強調集群是企業的一種空間組織形式,是在某一地域范圍內相互聯系的集聚體。后來還有不少學者對此問題發表了見仁見智的觀點,例如威廉姆森把企業集群界定為介于純市場組織和層級組織之間的中間性組織,羅森斐爾德側重探討社會關系網絡及企業間的合作對企業集群活力的決定性影響,而邁克爾?波特提出了垂直企業集群和水平企業集群的定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們采取求同存異的方法,就可以得出關于企業集群的基本認識:企業集群是指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的相關產業或某特定領域內大量互相聯系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及其支持機構在該區域空間內的集合。企業集群有自身的類型、特征和效應,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區域特色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里,我們以企業集群理論來觀照晚清民國時期上海的出版企業,無疑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這對于我們今天出版企業的建設、出版產業的發展也具有多方面的借鑒價值。國務院2009年發布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提出,要鼓勵打造文化產業集群,促進產業集聚和發展。包括出版業在內的文化產業在打造產業集群方面無疑是可以,而且有必要從歷史發展中吸取有益經驗的。
一、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形成
晚清民國時期的上海是中國無可爭議的出版中心。其中心地位既體現在上海出版業的社會影響、文化貢獻,又體現在它的企業業態、產業規模、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方面。而出版企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正是一個城市作為全國出版文化中心的重要標志。老上海出版企業集群就是在滬上婦孺皆知、聞名遐邇的福州路文化街上孕育、成長和壯大的。
福州路東起中山東一路,西到西藏中路,全長1453米。19世紀50年代筑成界路(今河南中路)以東一段,早期稱勞勃三渥克路,后因附近有基督教倫敦會傳教機構,故又稱布道路、教會路。1864年筑完全程,1965年以福建省福州市命名,老上海稱其為四馬路。福州路文化街一般指河南中路以西,福建中路以東的福州路及其周圍的山東中路麥家圈、河南中路的棋盤街、山西南路和昭通路一帶。自1845年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麥都思等人在今福州路南的山東中路路口開設墨海書館起,19世紀中期在棋盤街上先后涌現了文瑞樓、著易堂、掃葉山房、樂善堂、萬卷樓書坊、廣益書局及吳鞠潭,胡開文、曹素功、周虎臣墨莊,榮寶齋、大吉樓箋扇,西泠印社等。到20世紀初葉福州路文化街初步形成,至20世紀30年代達到鼎盛。據《全國書店調查錄》序中載,到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福州路一帶有報紙數十家、雜志數百種、新舊書肆三百余家,可謂九州皆知,天下共曉,影響波及于海內外。
從福州路到南京東路的山東中路一段早期叫廟街、望平街,在該街附近有1850年由字林洋行創辦的滬上第一份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后改名為《字林西報》。1861年字林洋行又創設了滬上第一份商業中文報紙——《上海新報》。自1872年創刊的《申報》、1893年創刊的《新聞報》等數十家報館、報紙集中在此出版發行,這條街便有了報館街之稱。福州路書店(出版社)的源頭是1844年的隆泰洋行,它經營樂譜、商業辭典、航海歷、中國海岸水路圖等,后來才有了由上海縣城遷來的墨海書館。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申城書店向北移至河南中路福州路,20世紀以來先后開設了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傳薪書局、開明書店等。由于福州路書業日趨繁榮,又有有正書局、生活書店等一批創設于外路段的出版發行機構云集到該路段謀求發展。到抗戰爆發前,福州路一帶的新舊書店已有三百多家。此時,資本雄厚的出版機構幾乎都集中在福州路。上海出版的圖書占全國的90%,福州路的商務、中華、世界書局三大巨頭就占全市的60%以上。福州路不僅是上海,也是全國圖書出版、印刷、發行的中心。
老上海的出版文化企業集群既有邁克爾?波特說定義的“水平企業集群”,眾多“扎堆”的出版機構共同享有終端產品市場,使用共同的技術、技巧以及相似的自然、人文資源;同時,也有所謂的“垂直企業集群”,即通過買賣關系來連接的眾多關聯企業集群。除了報館、書業機構云集,福州路一帶文化用品業、文化娛樂業也異常發達。如儀器文具業方面,起初是隆泰洋行開其端緒,后在河南中路棋盤街出現,有以經營傳統文房四寶的鴻寶齋、文瑞樓等。1870年屯鎮胡開文筆墨社在河南中路開業。19世紀后期有德隆昌、萬亨和紙號,商務、美生印書館(兼營文具)的相繼開設,使該路的儀器文具業初露端倪。20世紀初期,我國首創唯一的科學儀器館在河南中路開辦,使該路傳統文房四寶向現代儀器文具轉化。接著有周虎臣、周兆昌、曹素功筆墨莊云集福州路附近,該行業的營業規模日益擴大。隨著辛亥革命成功和“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人民群眾對文具儀器的需求日趨增加,加之周圍新聞業、出版業的蒸蒸日上,市內外文具業進一步向這一中心地帶聚集。抗日戰爭前后,著名筆墨莊和日商掘井謄寫堂,大正、大井洋行等又一次在此落戶,至上海解放前夕福州路及附近儀器文具店鱗次櫛比,成為中西文具兼備、文化用品齊全、批發和零售兼顧的儀器及文化用品集散地。
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形成,除了與其他企業集群相同的成因外,租界的出現與發展也是重要的緣由。朱聯保編撰的《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所記出版單位(主要是圖書機構)近600家,空間以上海市區為限,時間自鴉片戰爭后上海辟為租界時起,至上海解放后私營書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為止。作者在列于該書卷首的《漫談舊上海圖書出版業》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二三年,上海縣城外北面郊區,辟為租界,后被英、法帝國主義蠶食擴充到西北郊區。外國傳教士來上海在租界內所設出版機構先后有數十家,有稱書館(如墨海書館)、書院(如林華書院)、書室(如格致書室)、書會(如同文書會)等。這些傳教士辦的出版機構,從好的方面說,是把西方社會科學思想、自然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來,出版了一批啟蒙讀物;從壞的方面說,他們是進行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平心而論,我國人在租界內經營出版事業比較方便些,這是事實。”作者通過列舉20世紀30年代文化街一帶不同路段出版機構的名稱,充分展示這里企業集群的繁盛景象。這些出版發行單位,大多是在本地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也有從外地遷移而來的。朱聯保說:“群益書社是1907年由長沙分設到上海的(該社曾設分社于日本)。美華書館是先在寧波而后于1895年移到上海,新學會社也是辛亥革命前由寧波移來上海的。寧波與上海通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地理位置、人文經濟等均不及上海港發展之快,故有由寧波移來上海的。”還有北新書局因軍閥的迫害由北京南遷上海后,在魯迅大力扶持下創造了不俗的業績,更是書業佳話。新月書店、《語絲》、《現代評論》等新文學出版機構,也在20年代后期紛紛離開北平,移駐上海,開辟了新的出版天地。
至于汪孟鄒開辦于蕪湖的科學圖書社,后又把大本營搬到上海創建亞東圖書館,更是出版企業集群的典型表現。亞東圖書館一度在福州路江西路口福華里內經營。“陳獨秀認為亞東設在里弄內營業不能開展,由于他的建議,乃于1919年在五馬路(今廣東路)棋盤街西首租得門面,坐北朝南雙開問。那時正值‘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由他介紹經售北京大學出版部的書籍,營業很好。”天時地利人和,亞東圖書館成為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一份子,才創造了自己新文化出版的輝煌。出版產業的專業化和地理集中,使得上海不僅成為了近現代中國出版業的絕對中心,也成為亞洲最富活力與影響力的出版中心之一。
二、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效應
地域性的企業集群能夠釋放出一種集群效應。這種集群效應既是企業集群存在的合理基礎,也是企業集群不斷完善的推動力。邁克爾?波特認為這種新的空間組織形式能獲得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經濟外部效應、空間交易成本的節約、學習和創新效應以及品牌與廣告效應。仔細分析,我們發現晚清民國時期上海福州路一帶出版企業集群的效應主要表現為人才集聚效應、學習與創新效應以及制度效應。
先說人才集聚效應
作為內容產業的現代出版對文化人才有著特殊的需求。新出版業的產生和發展固然離不開新的印刷復制技術、新的經營方式與盈利模式、新的讀者群體與市場空間,但更重要的是離不開新型的獻身出版事業的各類文化人。晚清時期上海之所以能成為全國出版中心,形成企業集群,除了工商業發展為上海出版業提供了技術革新的動力,大面積租界的形成為上海出版業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政治和文化環境,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上海開埠以后崛起了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群。吳永貴這樣論述這個群體的來源:“其中有來自歐美的文化人,他們大多有教會背景,傳教之外,從事著包括出版在內的文化方面工作,其出版活動對中國新式出版具有先導性和示范性;有因為戰亂而來上海的中國各地知識分子,先是19世紀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使受戰爭破壞嚴重的江、浙、皖地區的文化人涌入上海,繼而19世紀末的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又有一批知識分子進入上海避難;也有出于謀生需要而來上海的文人,他們多身具一技之長,考慮上海文化市場發達,主動到上海尋找發展機會。另外,在津浦鐵路通車以前,四川、兩湖等內地人到京師去,要經過上海轉海輪北上,內地青年若到日本留學,上海更是必經之地,上海以其特殊的地位,在當時簡直成了西學在中國的‘批發站和‘中轉站,求西學,奔上海成為當時知識界的普遍心理。”這些新型知識分子群體與傳統的士大夫無論是價值觀念、人生理想,還是知識結構、謀生手段都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或從事著譯,或參與出版,構成了新式出版最為重要的作者群體和出版力量”。有了適宜的土壤和環境,又集聚了人才——這個出版事業最重要的無形資本,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出現便水到渠成。
文化人才的匯聚為出版企業的創設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其中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企業創業的動力之源;反過來,眾多出版企業的成立、遷入、發展和壯大,也起到了筑巢引鳳的效果。晚清時期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近代出版的第一個人才群體薈萃之地,留學生群體則成為最廣泛的報人群體,前者根據地就在上海,后者的集群效應于滬上也有所體現。而更為典型的商務印書館,匯聚了近代出版最大的人才群體于此,并影響到出版企業集群的形成和各類人才的凝聚。商務的各路英豪中,不乏企業管理人才、市場營銷人才、印刷技術人才,最能導引出版業的還是其編譯所的編輯著譯人才群體。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鼎盛時期,商務編譯所擁有的專家學者型人才多達三百多人,不遜于國內任何一家知名大學和專業研究機構。用今天的話說,商務的人才隊伍成了它的核心競爭力。“以商務印書館為人才的母體,現代幾大出版機構的創辦人都是從商務印書館掊離出來的,如中華書局的陸費逵、開明書店的章錫琛、大東書局的呂子泉、世界書局的沈知方,以商務印書館為近代中國出版人才的母體,分蘗了諸多的出版人才群體。這成為新出版的一個特點。”如果用胡適的話說,一家大的出版文化機構是一種“勢力”,我們似乎也可以認為,一個出版企業集群就是一個“磁場”,一個海納百川、吸引人才的“磁場”。
次說學習與創新效應
企業集群是培育企業進行學習和創新的溫床。企業位置相互毗鄰,企業類型彼此相同或相關,客觀上為它們的互相學習借鑒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競爭的壓力也自然而然成為企業探求與創新的動力。企業如要生存以及更好地、更持久地發展,則必須在模仿中創造,在學習中超越,打造屬于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近現代上海出版企業間往往通過模仿中的學習來克服新生企業的某些缺陷,迅速提升自我,發展壯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可以說,商務模式對上海出版業具有示范效應。“商務印書館開辟了中國現代出版印刷事業,商務的成功帶動了上海一批現代出版機構的涌現。有人把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的創立,看作是商務模式的延續和擴大。”除了中華、世界,還有大東、開明等重要書局,一些中等規模的出版機構,也大都學習商務模式,創業初或為獨資,或為合伙,后來先后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即便是在內部管理機制、機構設置、人員晉用,以及市場布局、營銷手段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借鑒了商務的成功經驗。
企業集群的學習創新效應有時也表現為競爭中的學習與開拓。中華在與商務展開教科書全面競爭的同時,在辭書、古籍、期刊諸多領域也發力角逐。商務有《辭源》,中華則編《辭海》;商務有《四部叢刊》,中華則出《四部備要》;商務有《教育雜志》《小說月報》等名刊,中華也刊行《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說界》等“八大雜志”。針鋒相對,雖似“拷貝”,其實又多自己的特色和風格,內容形式皆有突破。
還有滬上群星璀璨的中小書局,在大社名社的擠壓下,更是向專、精、特、新的方向拓展。出版企業集群的存在,克服了新企業因新而有的不利,推動了創業,也使后來者不斷學習和探索。亞東圖書館的古代白話小說標點分段、泰東圖書局與創造社的聯姻、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新型畫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文學叢刊、上海雜志公司的主打期刊營銷、生活書店的大膽作風等,無不體現出現代企業集群的特殊效應。不學習無以生,不創新唯有死。百花齊放,萬馬奔騰,上海灘眾多出版文化企業在市場中各展長才。而大型書局如“五大書局”——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的市場份額遠勝他家,產業集中度之高也遠勝于今日之中國出版界。
再說制度效應
作為一種組織形態,企業集群處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前者有合約、產權等,后者有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無論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這種制度在近現代上海出版企業集群中都有明顯體現。
企業集群運行機制的基礎是信任與承諾。這種人文因素是維持集群內企業所形成的長期關系的紐帶,并使集群在面對外來競爭者時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與滬上出版企業集群相伴而生的是書業同業公會。自1874年以來,隨著上海出版業的迅速發展和相關企業集群的出現,出版行業協會紛紛成立并不斷發展,先后組建的書業公會有上海書業公所、上海書業商會、上海新書業公會、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上海市華商書業聯合會、上海書業聯合會、上海特別市書業同業公會、上海市書商業同業公會、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上海特別市裝訂書業同業公會、上海市鉛印業同業公會、上海市簿冊裝訂商業同業公會、譯書公會、譯書交通公會等等。這些由出版經營者自發建立并經政府核準的行業組織旨在“謀求同業之利益,維護同業之信用”。汪耀華編著的《上海書業同業公會史料與研究》收錄了上海書業同業公會各組織1906年到1953年的重要章程、業規、劃一圖書價目實施辦法及相關應用附件等。這些書業同業公會通過道德自律與法規行規他律的相互協調,對于出版企業集群建立公平的交易市場,維護行業的經濟利益,保護出版者的合法版權,加強經營者的道德自律,最終促進出版業良好生態環境的形成,推動上海地區乃至全國新書業的健康發展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出版企業集群內,除了通過行業協會加以協調和管理外,企業相互之間也自覺加強溝通,以協議等方式來共同維護市場秩序,避免惡性競爭。例如,1921年底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就簽訂了銷售小學教科書的協議,計二十一條,內容包括發行折扣、回傭、贈品、對分局補貼限制以及違約罰款等,十分細致,具有可操作性。“為了減少競爭的負面影響,1935年陸費逵代表中華書局多次約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幾家主要的出版社,商討同行業規,試圖用一種行規來約束彼此的行為。”
從一般意義上說,政府也是企業集群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它通過政策制定,選擇合適的廠商進駐集群,維護集群秩序,并通過特定的集群政策,形成適合有利的制度來促進集群的發展。“在近現代出版史上,不論先前的清朝政府,還是后來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在出版管理上,基本上都采用了預防制中的注冊登記制,并同時通過制定各種相關出版法律,建立各種審查機構,采取各種追懲手段,增加其管控力度。另外,政府鼓勵甚至要求各地建立報業和書業公會,通過行業協會進行管理,也是政府管理出版業的主要手段之一。”近現代史上三個不同政府對待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的態度不盡相同,但登記制而非審批制的基本企業設立制度,法律的、經濟的而非主要是政治的、行政的管理方式,加之租界這個“特區”的特殊保護,使得滬上出版企業在并不安定繁榮的大環境下仍然創造了書業奇跡,企業集群的效應也得以充分展現。
三、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出版企業集群深處的思考
通過企業集群的理論來反觀漸行漸遠的晚清民國上海出版業,我們頓生無限感慨,也有一些困惑。從出版企業集群來看,老上海留給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其一,出版的中心是不是一定要靠近甚或同化為政治的中心。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的中心逐步移至上海,告別北京和南京,對出版業應該是幸事。過濃的政治氛圍、過強的政府干預、過多的計劃管制,往往不利于出版企業的發展。其二,出版企業集群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產物,其形成和發展都要遵循市場的法則和經濟的規律,自發性和內生性是它的特點。現今的北京聚集了全中國差不多40%以上的出版機構,但并沒有顯示出企業集群的特色和效應。其三,出版企業集群的出現,需要相對寬松自由的文化政策和適合的法律保障。企業沒有自主創設、優勝劣汰乃至自生自滅的權力,就不可能由少而多,集聚成群,匯涓涓細流成大江大河。其四,企業集群特別是中小企業集群并不是簡單的企業“扎堆”。它作為復蘇的產業組織模式,成為在全球生產系統中與巨型跨國公司互補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應對外部沖擊方面,集群比單獨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強。現在除了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區,一律按省(直轄市)級設立大型出版發行集團,未必比中小企業集群更有活力,更能抗擊風險。國外如美國紐約新媒體及其產業高度集聚,意大利、印度的一些中小企業集群成效顯著,我國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快速發展,也大多是得益于中小企業集群。此外,出版企業集群的出現有利于人才群體性的形成。一個出版機構,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自己的人才群體,沒有自身的人才高地,要想在國內國際的激烈競爭中占據優勢,無疑是十分困難的。
晚清民國時期出版業的發展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經驗也不乏教訓。老上海出版企業集群給我們留下的更多是有益的啟示。今天的出版業應從前人那里學習些什么、怎么學習,實在還很值得深思。出版產業的壯大、出版事業的繁榮,企業是載體,人才是根本,制度是關鍵。克服急功近利的政績思想,遵循經濟活動的普遍規律,積極營造良好的適宜出版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政治環境、文化政策和產業生態,刻不容緩。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出史版話
印刷術發明前的手抄本書籍
從大約公元6世紀,直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書籍都是由抄寫員依據一系列常規來復制的。這些復制員通常身為修道士,在被稱為抄寫室(scriptoria)的修道院工場里工作。他們的一部分工作是抄寫復制宗教儀式方面的著作,以滿足教育新教徒和禮拜活動之需,但他們也曾復制同樣用拉丁文寫作的世俗書籍。抄寫工作在羊皮紙或牛皮紙上進行,這些紙事先要折成頁,標上記號,打上格線。然后,紙張會被切割成頁,再摞成層疊狀。如果需要復制很多本,母本就會被分給多個抄寫員,每個抄寫員就他自己的那部分提供多個復本。工作由一個主事負責監管,他給抄寫員提供羊皮紙、筆、墨和尺子。為了防范火災,禁止使用人工光源,抄寫只在白天進行。抄寫員只負責用黑墨水抄寫正文,留下書名、標題和首字母由文字裝飾匠(rubricastor)用紅筆填上。
為了提高速度,一本書的抄寫會分派給多個小組承擔,因此不同風格的書寫方式會在同一本書中出現。
(摘編自[英]戴維?芬克爾斯坦、阿利斯泰爾?麥克利里著,何朝暉譯:《書史導論》,商務印刷館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