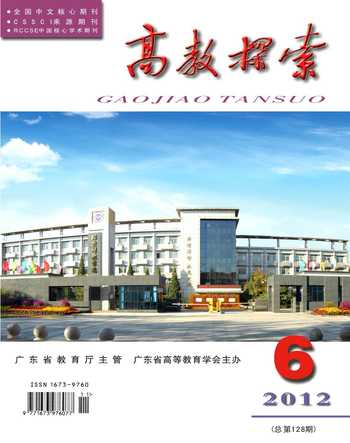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困惑、省思與進路
收稿日期:2012-05-10
作者簡介:高桂娟,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后。(上海/200092)
摘 要: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論與應用”、“思辨與實證”之間的困惑暴露了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薄弱的問題,問題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自主性的衰微。高等教育研究自主性衰微的外在表現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內在癥結是高等教育研究“科班出身者”未能做到學術上的獨立自主。高等教育研究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除了孜孜以求學科的“知識邏輯”以外,尤其要加強學術共同體的建構,“科班”與“雜家”整體改進。
關鍵詞: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學科;學術共同體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在發展中出現的或需要預見的問題都向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對一系列重大問題和熱點問題的深入分析和前瞻性的解答,都需要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有所進展。與此同時,作為一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國,龐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隊伍如何推出高水平的、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如何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舞臺實現平等對話等等,也迫切需要加強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影響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因素包括多個層面,最核心層是和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直接相關的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視角、思想深度、方法立場等等;中觀層面是高等教育理論創新的制度環境,包括學術評價制度、出版發行制度等等;宏觀層面還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以及歷史文化背景等等。本文從長期困惑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問題出發,并主要從微觀層面進行分析,以期探尋提升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水平的進路。
一、困惑:制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矛盾與問題
回顧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狀況,不難看出研究者們研究定位的困惑和搖擺不定。譬如,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思辨還是實證?這些既相互統一又存在對立的一些關系,在具體的研究活動中難以把持,日積月累,也就成為困惑和阻礙高等教育理論發展的老問題。
(1)理論與應用。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從一開始就以兩條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軌道發展:一條以基本理論和學科建設為主;另一條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主,開展應用性、開發性研究。而從學科定位上講,高等教育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是教育學的二級學科。它將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用于解釋和解決高等教育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并在應用研究中不斷充實、提高、完善高等教育學科的理論。[1]這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研究的另一條軌道——“學科”本身也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且在學科歸屬上,雖然劃為教育學的二級學科,但實際上卻和教育學相距甚遠,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無法直接拿來研究和解釋高等教育領域的現象和問題。現實狀況是,高等教育學究竟是學科還是領域存在著諸多爭議,高等教育研究的應用性色彩日趨濃厚。由于相對于其他學科,高等教育學沒有學科壁壘的限制,高等教育研究隊伍具有最大的開放性,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遵循“來者不拒,一視同仁”的原則:無論是教育專業的“科班出身者”,還是其他專業的“半路出家者”,甚至“業余愛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學科行列,都可以在學科領域發表自己的觀點,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成果贏得同行的尊重。[2]這在極大地繁榮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同時,帶來的問題是,大量工作總結、經驗報告式的文章充斥著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這讓“科班出身者”感覺到高等教育學“沒有學問”了。問題還不僅如此,許多高等教育學專業的“科班出身者”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高等教育的實踐狀況,在一些高等教育管理者和高校一線教師眼中,他們的研究大多屬于空談無用。于是乎,各種級別的課題反復重申的就是“應用價值”和“社會效益”。為了贏得學校、政府和社會重視,為了獲取研究資源,高等教育學的“科班出身者”也更加注重應用。其結果是,與中國高等教育熱火朝天的改革實踐相比,高等教育理論研究顯得門庭冷落,高等教育理論對高等教育現象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高等教育理論無法有力地指導和引領實踐。
我們一向遵從理論聯系實際,理論來自于實踐,又指導實踐。但倘若只是關注整體的教育實踐而不加以分解,并進行充分的論證,這樣建構的教育理論是否會因其模糊、混沌而陷入到處充斥著大而無當的“正確的廢話”的困境?[3]這是其一。其二,“‘理論聯系實際的濫用給我們帶來的是理論的貧乏,實踐的落后。……大學問的頂端就是理論,很可能還是很抽象的理論”[4]。可見,要加強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要做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學問,必須加強基本理論研究,但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如何克服學科性先天不足的短板?如何在應用性的汪洋大海中搭建通往理論研究的通途?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2)實證與思辨。與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相對應的困惑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實證與思辨之間的偏頗。高等教育研究長期以其應用性見長。既然是研究,其底線應該是依照胡適所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尊重事實,注重論證。但實際上,“求用”的研究為了“時效”,不免短視急躁,再加上“非科班者”大多缺少研究方法的系統訓練,導致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整體的深度不夠。
基于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現狀,徐輝與季誠鈞兩位教授提出了有關“實證與思辨”的分類,并歸納了“反映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實際情況”的定性與思辨方法的特點。在此基礎上,他們指出,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中方法意識淡薄,思辨傾向嚴重。[5]
也許是矯枉必須過正,近年來,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中,量化和實證之風大有后來者居上的趨勢:課題的申報與結題驗收常常要看“工作量”的大小,亦即是否有量化和實證研究;翻翻教育類的學術期刊與人大復印資料《高等教育》,冠名以“調查”、“實證”的論文越來越多,且通篇布滿了大量的數據、數學推演和圖表。在此需要我們置疑的是:
其一,高等教育活動作為紛繁復雜的社會活動,過度強調量化是否會遮蔽或曲解其豐富和鮮活的內容?“雖然現代社會著魔似地竭力要測量每一件事物,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只有具備像實驗室那樣精確條件的地方,才有可能測量出精確的結果。可是,是否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實驗室的精確條件呢?事實上,當需要人們參與的諸如教育、經濟或選舉之類的重要問題處于關鍵的時刻,你不可能得到像實驗室條件那樣的東西。”[6]可見,量化本身也具有多種局限性,實證和量化數據的獲得不僅取決于研究者本人操作的規范性,也取決于研究對象的真實狀態,由此誰能保證數據的準確性乃至真實性?不真實和不準確的數據又如何能揭示事物的真相或規律呢?
其二,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規模雖然龐大,但并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學術共同體,研究者多屬于散兵游勇式的“單打獨斗”。而數據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大規模的定量研究尤其如此,這顯然是單個的研究者無法完成的。仔細閱讀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中大量的量化和實證研究的文本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多局限于某校、某市或某省,且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簡單的問卷調查和簡單的“相關分析”。這樣的研究,其成果和價值都不免令人生疑。更讓人擔心的是,由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組織建設不到位,數據的采集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往往被采集者占為己有或束之高閣;且大規模的研究項目極容易落入高層教育行政管理者之手,因為只有他們才擁有更多資源,也極容易調動人財物進行大規模的定量和實證研究。這樣所導致的學者的邊緣化勢必進一步惡化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環境。
其三,每個觀察均是理論之光照耀下的觀察。更重要的是,每個觀察均可被劃入由許多理論構成的理論等級之中。我們必須說,一個觀察是在哪一種理論指導下做出的觀察?[7]“我們使用統計數字越多,偉大的真理越容易從我們的手指間溜走。”[8]在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薄弱和滯后的前提下,量化和實證研究如何保證其質量和水平?
其實,針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思辨傾向嚴重”的指責,馮向東教授進一步撰文明晰了思辨與實證的含義及其二者的關系,指出“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分類不是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狀況恰當的描述,呼吁不必忌諱思辨而是要把握好思辨,所有的理論,包括實證研究中的理論假設和質的研究所主張的“扎根理論”,都是思辨的產物,沒有思辨就沒有理論。應該要求的是思辨的深刻性而不是“去思辨化”。[9]可惜在大家都急于表現自己的研究屬于“硬科學”的情境中,馮向東教授的呼吁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此我們需要警覺的是,在愈演愈烈的、以磅礴的數據掩飾低層次的研究風氣之下,如何彰顯理論研究的重要意義?理論研究是否會更加邊緣化?
二、省思:自主性衰微對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侵蝕
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論與應用、思辨與實證之間的矛盾與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尷尬。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這種尷尬地位,和高等教育研究自主性的衰微不無關系。自主性是指,人作為文化主體在其他研究領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它的實質是突出知識主體(人)在認識過程中的中心地位。[10]自主性衰微在此處指的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為外力所左右,喪失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無法關注高等教育本身,而導致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種種偏離。
自主性衰微的外在表現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依據胡建華教授的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包括組織、隊伍、成果三個方面的泛化。高等教育研究組織的泛化,主要是指許多掛著“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牌子的機構并沒有開展高等教育研究活動。高等教育研究人員的泛化,不僅表現在許多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內的研究人員并不研究高等教育,還表現為作為學術團體的高等教育學會的一些成員也不在從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學會作為學術團體,其成員應是學術工作者、研究者,這是學術界的慣例與常識。)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泛化是指,在數量頗豐的論文、著作中,有許多其實不能劃入“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之列。[11]
自主性衰微的內在癥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科班出身者”(主要指高等教育學科的研究生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專職人員)未能做到學術上的獨立自主。
客觀地說,高等教育研究的“科班出身者”不乏對理論研究的探索,但通常采取的是“拿來主義”方式:要么借鑒其他學科的概念體系與分析路徑;要么是舶來國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謂的“先進理論”。前者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引入了其它學科的概念措辭,在用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措辭方式‘說話、‘寫作和‘思考”[12]。不可否認多學科觀點和視角研究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但“高等教育越是走近相關的學科,越是與其他學科深度融合,則越是難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理論和知識系統”[13]。后者則無視“借鑒”的本土化要求,對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缺少合理的繼承,對本國的高等教育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提煉,試圖以“普適性”為憑據,直接用國外的“先進理論”解決中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一味地尊奉外域理論,其結果是落入“從屬理論”的境地:研究內容主要是翻譯、介紹、詮釋國外理論研究成果;研究形式主要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但比較研究只是一個空殼,基本上是復制別人的思想、理論、定理、觀點、結論和假說;對中國自己的經驗、理論卻不屑一顧;研究成果上基本沒有原創性的發現、理論,更為重要的是沒有開創性的研究領域和問題,只是亦步亦趨地跟隨、模仿、驗證。[14]
“拿來主義”式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只是在做理論的尋找和復制工作,沒有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咀嚼工作,無法創生新的理論增長點。這使得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新概念層出不窮,語言表達晦澀難懂,思想內容空洞漂浮,其成果常常成為與我國高等教育實踐隔離開來的“科班出身者”的自說自話。
“拿來主義”折射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班出身者”缺乏學術上的獨立自主的另一種表現,那就是“唯書”、“唯上”。“唯書”是指盲目地推崇“經典名著”,但又不求甚解、生搬硬套;“唯上”是指對各種“權威”頂禮膜拜、人云亦云,缺少反思和批判精神。
缺乏學術上的獨立自主更加惡劣的表現是,目前一些高等教育學科的碩士、博士“讀書只為稻粱謀”,把學問當作謀取功名利祿的手段,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態讓他們注重短期效率、盲目追蹤“熱點”,很難做深入系統的研究,更無法靜下心來做純理論研究。周作人曾說過:“單靠文學為謀生之具,這樣的人如加多起來,勢必制成文學的墮落。”同理,如果把高等教育研究僅僅當作謀生之具,這樣的人如加多起來,也勢必制成高等教育研究的墮落,這對于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危害尤其嚴重——“因為經濟所難以克服的短視而對基礎理論研究不會十分慷慨,所以那種為學術而學術者往往是比較清寒的”[15]。沒有“十年磨一劍”的毅力,沒有“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氣度,是很難做好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
三、進路: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科班”與“雜家”的整體改進
從學科的角度分析,學科不僅僅是基于知識的分類,其思想內涵尤指“在一門知識里受教,即是受規訓而最終具備紀律(discipline),亦即是擁有能夠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素質”[16]。長期以來,但凡講到高等教育理論建構問題,大家不約而同地都要講到“高等教育學”學科問題;講到“高等教育學”學科問題,又不約而同關注的是知識建構問題。而學科里的“人”,尤其是“人”的“自主自持”的素質問題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依據上述分析,高等教育研究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除了孜孜以求學科的“知識邏輯”以外,尤其要加強學術共同體的建構。
“科班出身者”應該是最有條件進行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群體,同時“科班出身者”也是構筑學術共同體的中堅力量。終身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愛德華·希爾斯認為,大學對業余者的勝利得益于科學和學術成就所要求的專門化的出現。較之于業余者的自我教育,大學里系統的尤其是研究生階段的培養,更有利于專門化。研究的專門化助長了科學和學術共同體的超越地方的特點及其層級。專門化更易于確定注意力集中的中心,確定來自這些中心的研究課題,提出、應用和建構觀點,詮釋和成就標準。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家或學者,就要求他是一個專門家(fachmann)。[17]
我們平日所說的“科班出身者”本義亦是此處的“專門家”。 高等教育學科的“科班出身者”如何才能達致專門家呢?古人所云“博曉古今,可立一家之說;學貫中西,或成經國之才”,這對我們不無啟迪。從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問題出發,“博曉古今”、“學貫中西”更要聚焦于歷史和哲學領域。
教育理論研究的命題是真命題還是偽問題?對一個真命題的解答,其論證材料是否清楚?其研究結論是否具有前瞻性?這些教育理論研究自始自終需要斟酌的問題,都根植于歷史的土壤中。在高等教育史領域頗有建樹的劉海峰教授曾發文“初探”、“再探”、“三探”、“四探”高等教育史研究對于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重要價值。高等教育學奠基人潘懋元先生也一向強調研究教育理論應有一定的教育史知識,這樣才能了解高等教育的內在聯系,研究才能有深度、有遠見。缺乏歷史分析,往往只能就事論事,浮于表面。潘先生還通過魯迅之言“治學先治史”重申了學習歷史對掌握理論、研究學問的重要。[18]另一方面,反思、追問、批判,這些教育理論研究必要的思維和過程都需要哲學為我們提供養料、奠定根基。“哲學的精神在于必須求貫通,必須追問到澈底,從這一方面來說,我們可以把哲學當作一個訓練。換言之,即可以訓練人們的頭腦,使他有很快的聯想力與分別心。習哲學的功用在于使學習的人們訓練成了一副敏銳的腦筋。能夠自己運思,又能夠發現古人思想中聯絡處與間隙點。”[19]
歷史與哲學對于教育理論研究的裨益從涂又光教授的治學可見一斑。涂又光教授在教育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見解,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和理論研究的創新性成果。涂又光教授提出以“教育自身”為核心的教育本體論、以知行關系為核心的教育認識論、以反芻律和經驗律為核心的教育方法論、以復歸于無知為中心的教育過程論;他的關于校園文化育人功能的“泡菜壇子理論”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關于教育應定位在文化里的“三Li說”是人們在研究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關系時繞不過去的一個“理論制高點”。涂又光教授對于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的創建,是和他在文史哲方面的精深造詣密切相關的。涂先生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是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高足,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的資深教授,長期主講“中國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學”。他在課堂教學和闡明問題時,古今中外的典籍信手拈來。正是由于他博古通今,精中曉外,他對教育的認識與論述才可能十分系統、非常本質、極富創見,既站在歷史高度上具有戰略意義,又身處我國實際中可以具體操作,既繼承了我國優秀的教育傳統,又吸取了世界先進的教育經驗,被譽為“才學識兼具、精氣神俱足的智者”。
眾所周知,歷史和哲學的素養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非一兩門課程、幾本教材能夠解決問題的。這至少需要高等教育學研究生靜下心來博覽群書,有走進“象牙塔”的體認,方能有走出“象牙塔”的底氣;這也至少要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專職人員有“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持守。但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所處的中觀制度環境是,研究生的求學面臨學制短、課程多、就業壓力大的問題,專職研究人員則面臨“publish or perish”(出版還是滅亡)的嚴峻現實。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素質的培養和提高還需同時推進學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譬如,要改革高等教育學研究生招生培養制度,“學術性”學位遵循“少而精”的原則,控制招生數量,實行嚴進嚴出,輔之于充沛的學術資源、良好的生活條件,確保他們能夠“衣食無憂地做學問”。改革目前學術評價與晉升制度過度量化的弊端,更要根除學術腐敗的毒瘤,輔之于良好的學術扶持、資助和獎勵制度。總之,“拔苗助長”、“立竿見影”式的政策和制度,都不利于學術的長遠發展。這如馮友蘭先生所言,為致用而學術,容易犯一種短視急躁病。結果學術研究不好,因而也無從致用。“為學術而學術”,不以致用為意,反而可以得到學術之大用。[20]以此為出發點,中國高等教育學科乃至人文學科的制度設計,要吸納寶貴的歷史資源,不能丟棄我國歷史上的“養士”傳統。春秋戰國時期,養士、爭士蔚然成風,養士風尚造就了重視人才、重視知識的氛圍,對繁榮學術培養士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鑒古知今,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繁榮,不僅需要研究者具有“為學術而學術”之精神,也需要制度設計者具有“為學術而學術”之雅量。
當然,“科班出身者”的孤軍奮戰是遠遠不夠的。鑒于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最大的開放性,其隊伍組成幾乎涵蓋了和高等教育相關的各種人員,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水平的提升還需要“半路出家者”、“業余愛好者”等等“雜家”的整體跟進。這需要加強“雜家”的學術規范,提高其理論研究的素質和能力,喚醒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著的研究者”的覺悟。其途徑有二:一是在壓縮高等教育學“學術性”學位的同時,積極發展“職業性”學位教育,滿足高校管理人員以及廣大教師進行高等教育研究的需求,并保證高等教育研究的質量;二是建立穩定有序的培訓制度,如定期開辦高等教育學的高級研修班,使廣大“業余愛好者”有機會了解高等教育研究全貌,系統掌握科學研究的規范和方法。在此方面,我國師范院校面向基礎教育的培訓,有許多經驗值得借鑒。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1]中國實現由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轉變,亟待提升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高度和深度,這是高等教育研究面臨的新的挑戰和機遇,也是以高等教育研究為志業者的使命和責任。
參考文獻:
[1]潘懋元,劉小強.21世紀初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進展與問題[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8):30-39.
[2]潘懋元,李均.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來居上 異軍突起[J].中國高等教育,2009(18):15-20,41.
[3]李潤洲.教育理論何以稱為理論[J].江西教育科研,2007(12):3-7.
[4][15][20][21]張楚廷.高等教育哲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163-164,165,165,160.
[5]徐輝,季誠鈞.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現狀及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04(1):13-15
[6][8][美]David Boyle.為什么數字使我們失去理性[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3,5.
[7][德]漢斯·波塞爾.科學:什么是科學[M].上海:三聯書店,2002.79.
[9]馮向東.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思辨”與“實證”方法辨析[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0(1):172-178.
[10]范進.康德文化哲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86.
[11]胡建華.試析高等教育研究的“泛化”現象[J].現代大學教育,2003(1):33-36.
[12]周玲.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5(2):68-72.
[13]陳洪捷.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學科發展與范式變遷[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0(4):2-12.
[14]吳巖.從屬理論現象與教育理論研究創新[J].教育科學研究,2003(7-8):23-25.
[16]華勒斯坦.學科·知識·權力[M].北京:三聯書店,1999.13.
[17][美]愛德華·希爾斯.學術的秩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36-38.
[18]潘懋元.高教歷史與高教研究[A].黃宇智.潘懋元高等教育學文集[C].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425-426.
[19]張東蓀.科學與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