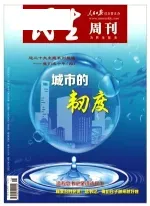高向軍:嵌入秦巴山區的女人
陳沙沙

12月的四川省儀隴縣金城鎮籠罩在陰雨之中,空氣潮濕。道路順著山勢上下起伏,似乎無論往哪個方向行走,都避不開滿腳泥濘。
然而,有數十名農民并沒有受到天氣的影響,他們聚集在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儀隴鄉協”)小小的會議室中,聆聽一個女人庖丁解牛般的講解。
這個女人叫高向軍,53歲,她身穿深紫色的繡花棉服,帶著沾著污漬的袖套,講到重要處,還不時握緊拳頭敲打桌面。
高向軍稀疏的頭發簡單地挽成一個發髻,雖然神情疲憊,但言辭鋒利。
近幾年來,關于“小額信貸危機——‘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困”的新聞早已在網絡上四起,作為最早一批在國內踐行“窮人銀行”的代表,引入“公益小額信貸”概念的高向軍會對此如何回應,對于一直從事的事業,她是否也心存質疑……
“這輩子有意思的事太多”
“任何體系,完全復制到中國都會‘水土不服。但是尤努斯模式的核心是好的,負面評論大部分來自不懂的人。”說話間,她無意識地抬頭看了看墻壁上的照片。鏡框中,一位異域的白發老者笑容和藹地攬著一位長發的東方女子。那是2002年,高向軍第三次前往孟加拉學習小額貸款機構管理,與“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教授的合影。
對于1959生人的高向軍來說,生命旅程中“有意思的事太多。”
1991年,對政府體制改革深感“危機”的她,一邊拿著縣政府辦公室秘書每個月40元的工資;一邊雇了兩個人,在政府大院里開起了小賣部。
“全縣人都罵我想錢想瘋了。”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風潮,遠遠沒有惠及這個窩在秦巴山區里的小縣城。人們對于她的行為更多地是“輕視”。但也正是小賣鋪帶來的“巨額”收入,讓高向軍有了第一次北京之行的路費。
19年前,帶著“玩”的心態,高向軍和一位在四川省外經貿部門工作的朋友前往北京,恰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準備在四川做一個“參與式的農村扶貧與婦女參與的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這個事情很偶然!那些老外看到一個漂亮的‘小姑娘,都新奇得不得了,因為從來沒有人來‘要項目。”看到能為縣里“拿錢”,高向軍來了干勁。返回儀隴后,她開始馬不停蹄地準備申請材料。
當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委派的兩名外籍專家進入儀隴后,縣公安局竟把他們當成了“特務”,并命令高向軍“護送”他們從成都出境。
“真的很傷心,我和外籍專家抱著哭。”高向軍曾對當時“自閉”的環境頗有微詞。那次,她在成都逗留了兩天梳理情緒。又經過兩天泥路的顛簸,才回到儀隴的家中。看著鏡子中的“土猴”,高向軍蹲在地上哭了……但她仍選擇堅持。
1995年,在老縣長的支持下,縣政府設立了儀隴縣項目辦公室,任命高向軍為項目辦主任,以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的援助起步,注冊了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
1996年,“膽兒大”的高向軍到孟加拉走馬觀花式地考察了格萊珉銀行的小額貸款項目,又在晏陽初學院學習了鄉村發展理論,回來就照葫芧畫瓢地開始實踐。
1998年,UNDP項目結束,但七八千農戶的錢仍在貸款中滾動,儀隴鄉協轉型為一個獨立的民間公益組織。
“難死了,但我不抱怨誰”
17年來,儀隴鄉協作為一個“社會企業”的輪廓漸漸清晰,并引來了國內眾多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前來取經。至今,已為近20萬貧困人群提供過9000多萬元無需抵押擔保的小額信貸服務。
“我自認為是不應該干這個的,但不是能人也干不了。”這句話怎么聽,怎么透著股“自夸”。 但突然想起,記者聯系之初,高向軍堅持“面對面” 的采訪方式,“我的心路歷程怎么可能在電話里說得清。”
1995年至1998年,儀隴鄉協業務量相當大,全縣有七八千農民參加,但高向軍卻有苦難言。
“本金、還款、利息、風險金等等都在一個賬上,分不出來哪跟哪, 一鍋粥。我們只知道收支帳,不知道金融帳。”短時間內,儀隴鄉協的規模擴大了,接受小額信貸的農民多了,卻沒有管理信息系統,沒有風險控制系統,一切手續都停留在“手抄本”的原始狀態。
“我們是有熱情,但不代表有能力。”為了避免“糊涂賬”越滾越大,1998年,高向軍暫停了業務流動。為了穩定“軍心”,她再次請求聯合國專家設計管理方案。“看到老外,我就哭了。我說你們怎么只給錢,不給方法的。”
在2004年,儀隴鄉協改革啟動時,她決定把審批權下放,讓分支機構獨立,但要求工作人員入股,共同承擔風險。自此,儀隴鄉協開始步入正軌。
然而,引進的管理系統并不完善,給儀隴鄉協后來遭遇的困境埋下了“伏筆”。“聯合國設計的管理方案‘水土不服,當年我們只能花錢買系統。誰知道系統是單機操作,不能聯網的。”
2008年,高向軍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與此同時,儀隴鄉協的問題再次顯現,管理體系不完善,風險體系漏洞頻出。
“員工們擔心我在病中操心,遇到了沒有還款的壞賬,他們就自己做賬,用假的新增貸款來掩蓋壞賬。農民的小額貸款常常幾天就要到款,總部又無法核查。這些金融危機就越埋越深,越來越大。”
2011年4月,高向軍再次停止了協會所有的業務。半年的內部調整中,她采用“背靠背”的方式查找壞賬、精簡人員、建立審批委員會、重新收回業務員的審批權力……
2012年初,高向軍在北京組織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國內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參與。在會上,她把儀隴鄉協的經歷合盤道出。“他們曾經都來我這學,我是有罪過的啊。”
“資金互助只是紐帶”
有一次,10個村莊合力種辣椒,委托儀隴鄉協統一采買種子。“我從儀隴買到成都,沒有人敢賣給我。因為我要簽合同。這說明什么?里面肯定有假種子!”
“為什么?因為農民不懂,農民沒有組織,沒有博弈的能力。”那段時間,高向軍經常這樣自問自答。
之后,儀隴鄉協將她的想法付于實踐,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出臺之前,2005年儀隴鄉協就已經嘗試孵化“農民社區公民社會組織”。
“100戶農民有1000個想法,想統一太難了。”在農民組織的建設過程中,高向軍的隊伍需要“手把手”教農民如何團結,如何統一面對市場,甚至如何和企業談判。
針對中國農民的“個性”,高向軍開始尋找紐帶讓農民聯合起來——資金互助的“村基金”,它的性質就像獨立于儀隴鄉協之外的、農民自己的、以村為單位的“小額信貸”。
“入股的農民每年還會拿到分紅。”農民自愿入股,儀隴鄉協用地方財政支持的資金等額配股,“農民入股500元,相當于入股1000元。”
被問到“農民都到本村貸款了,儀隴鄉協的客戶不就少了?”
“光靠協會的本金,怎么可能惠及更多的人啊。他們的小額信貸是儀隴鄉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要教會農民自己做。”高向軍回答。
“通過資金的聯系,農民會產生互動,更團結,而且會支持自己社區的建設。”這是尤努斯模式在儀隴的“因地制宜”。
目前,已有19家農民社區公民社會組織扎根儀隴。“其實,現在已經不是怎么幫農民在經濟上發展,更重要的是農民教育。一路走過來,農民高興,我們就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