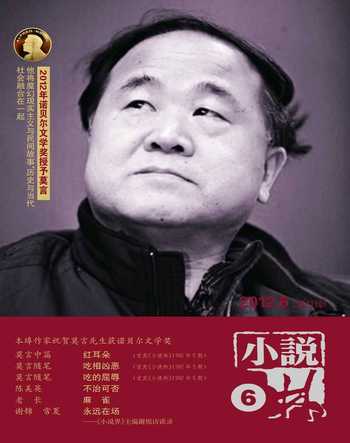麻雀
她媽又在叫她起床了,依舊連叫三聲。三聲都很輕,不過還是呈遞進的趨勢,后一聲總要略高一些。最輕的自是第一聲,輕得近乎毫無效果,就續了第二聲。這一聲在她聽來亦真亦幻,那期間,她一半還沉在睡夢里;另一半卻已行進于醒來的路途上。第三聲發出來的時候,聽到叫聲的同時,她還嗅到從廚房彌散過來的煮粥的氣味。
林菲一向都是先吭嘰了兩聲,側臥的身體隨之平躺過來,并不睜開眼睛,只用更換的造型表示她已經醒了,只是還要抱殘守缺地再賴上一陣。
此刻,是早上六點,就是說距院通勤車抵達父母家附近的站點兒還差半小時的時間。那么,刨除賴床的一陣,余下的時間還有二十多分鐘。在這段時間里,她需要做的是起床、洗漱以及簡單的描畫,接著再到廚房喝一碗她媽煮好的粥,直至更衣踏出家門——這一切必須環環相扣。只有這樣,之后才不至于連跑帶顛地朝通勤車站點兒趕,否則很有可能被落下——這種事不是沒發生過,害得她還得打車去追,付一筆無謂的支出。
父母家的小區是十幾年前落成的,位于一個鐵路貨運站旁邊。站內總有列車出入,鏗然的鳴響與站外櫛比的空車配貨點兒上隨時停靠的重載卡車聲交相呼應,不分晨昏晝夜。以至于連燥熱的夏夜,住戶們都很少開窗戶。不然,休想睡消停。很多人都為此憤憤不平,罵咧咧地說這鬼地方真他媽住夠了,哪天有錢一定到清靜的地段買一套房子。也僅僅那么罵兩句痛快一下嘴算了,過后還是得茍且地住下去,或許直到終此一生。
睜開眼睛之前,林菲常常于恍惚中躺進另一間屋子里。那是一棟臨江而立的高層,比眼下這間寬敞許多。厚實的窗簾遮住了清亮的晨光,屋內始終停滯在黎明的昏暗中。不過,也無須用眼睛去分辨,那些氣派的歐式家具也能一一地排列在她心里的位置上。望見它們,她即刻會滋浮起一絲怡然的感覺來。在那等情境下,她根本無須匆匆起床,匆匆洗漱,匆匆喝粥,再匆匆去趕通勤車——她身邊正睡著一個男人,是她老公濱子。待他醒來,會用一輛雷克薩斯載著她,兩人先到常去的那家廣式茶樓各自喝一碗魚片兒粥,而后再送她去上班……
門廳里傳來輕微的開門聲。她睜開眼睛抻了個懶腰,隨之翻身下床,其間,聽見跨到門外的她爸壓低嗓音用京戲念白的腔調對她媽說,拜拜,夫人。
她爸從小就喜歡京戲,生旦凈丑各類唱腔和念白張口即來,全都韻味十足。他總念叨說等將來老了就去當一個票友,每天除了泡戲園子,再就是與聚在公園里老戲迷們去擂臺比武。現如今,他已然到了當初所說的那個將來的年紀,卻仍在給人賣手腕子開出租車。既做不成票友,只能尋機自享其樂了。
快滾蛋吧!她媽戧了她爸一句,再不乏溫情地叮囑他小心開車,隨后嘎達一聲帶上了房門。
洗漱的期間,她媽已為她盛好一碗粥晾上。洗漱完畢,那碗粥恰好溫度適宜。
坐下來喝粥的時候,她媽呆愣地立在旁邊,先嘆了口氣,之后叨咕說自己昨晚又做那個夢了。
哪個夢呀?林菲抬眼瞥著她媽問。
她媽說,還不是以前咱家住過的平房外屋地房門的那個夢嘛。
于是,她就從她媽的眸子里瞥見了一扇斑駁扭曲的門。門上安著一把暗鎖,已松動成一副岌岌可危的樣子——這都要歸罪她哥,那家伙經常忘記帶鑰匙,就拿自己的腳代替。久而久之,鎖上的螺絲便脫扣了。
平房沒有室內廁所,外屋地備著一個搪瓷便罐供一家人夜里用。她媽說總夢見自己起夜來到外屋地時,那把松動的暗鎖發出嘎達嘎達的響聲,分明有人正企圖破門而入,令她膽戰心驚,跌撞地撲上去,一邊用力抵住,一邊喚她爸快點兒出來。她扯著嗓子叫喊,聲音卻始終卡在喉嚨里涌不出來,以至于每次都在那個環節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
她媽最初講起這個夢的時候,林菲曾煞有介事地充當了一回解夢的周公,問她媽白天都干了什么。
她媽說,我能干啥,不就是拾掇屋子、洗衣服、買菜、做飯嘛。
這一切當然跟那個夢扯不上關系,她就再問她媽最近一陣都想了啥。
她媽失神地望望她,說,還不是總想你的事兒嘛。
她頓時垂下了眼皮,半天才抬起來,嗔怪地乜著她媽說,你不一天到晚老瞎尋思就啥事兒都沒了!
……
通勤車站點兒距離父母家的小區大約五百米,不是一條直線,需輾轉曲折地穿過幾條街巷,還要跨過一座跨線橋。由于之前的環節都把握得恰到好處,接下來,她盡可以將步子邁得不慌不忙的。
初秋的早晨透著幾分涼意,不過,街上的人多半都沒添加衣服。日間太陽依舊火辣,添了最終也得剝下來,太費事。何況對于女人來說還不乏其他理由:這座城市的夏季很短,致使她們沒多少機會展示自己的婀娜,自然不忍輕易遮蔽起來。
林菲卻與人不同,早已將裙子換成了長褲,還在里面套上一條線褲——她絕不敢忽視給她作診斷的那個醫生的告誡。那個醫生當時一邊搖動著他那應該是患有頸椎病的脖子,一邊拖著半死不活的腔調說,要小心著涼啊,不然病情加重了就麻煩了。
加重了會咋樣呢?她怯怯地問。
尿毒癥。醫生冷冷答道。
當她和濱子兩人大眼瞪小眼地對視的期間,醫生的脖子總算搖舒服了,停下來問她是否結婚了。
結了。濱子囁嚅地替她回話。
醫生翻著眼皮瞄了瞄濱子,隨后將眼睛瞥在濱子和林菲的空隙間,說,那你們暫時最好別同床……
濱子愣愣地看醫生,再扭過臉來看她,仿佛沒聽明白似的。
……
每當踏上那座跨線橋,林菲總要不經意地朝橋下瞥一眼。
橋下幾排并行的鐵軌正映著亮晶晶的晨光,從東邊的一個高坡下延伸過來。貨運站就坐落在高坡的對面,此刻,一列車皮正泊在站上卸貨。貨運站的后頭是父母家的小區,很不規整,朝向各不相同:一部分朝南;一部分朝東;還有一部分朝向模糊。當年樓體上涂刷的淡綠色幾乎褪盡了,還生出一塊塊的霉斑。與父母家小區遙遙相望的坡頂上,立著幾棟去年落成的高層。由于位置上的優勢,呈現一副傲然的架勢。想必其中的住戶居高臨下地瞥見父母家的小區時,眼里定會泄出一絲鄙夷的神情。那神情令她很不舒服,暗自叨咕一句說,不就是高層嗎,誰沒住過咋的。其間,還有一次身居于臨江而立的那棟高層的屋子里,倚著一扇寬大的落地窗,朝遠處開闊的江面望過去……
在站點兒候了一陣,通勤車就到了。她款款上了車,對稀落分散在座位里的幾個同事瞇眼笑了笑,眼神卻是躲閃的:她不想面對別人眼中的猜疑,更不想他們問自己為何最近總住在父母家里那等問題。
當初,諸多同事都見識過濱子迎娶她時那場婚禮的氣派的陣容。而舉杯賀喜之間,她也從一些人的眼神里聽到了嘁咕嚓咕的聲音。大家都看透了她嫁給一個相貌跟她比起來出入似乎大了點兒的濱子,無疑是看中了人家的豐衣足食。這一點,她不想否認,但被別人私下里講究,還是覺得不快,上翹的嘴角不禁微微下壓了一下。不過,很快便又恢復了笑瞇瞇的模樣。
而眼下,她的處境分明與當初大不相同了——盡管濱子尚未提出離婚,她卻預感到這種僵持的日子是終究不會太長的。那么,當大家獲悉了內情以后,肯定會背地里重復先前的交頭接耳,甚至還會有人暗自幸災樂禍的。她決不能給他們任何機會。
她尋個空位子坐下來,刻意掩口打了個哈欠,以示自己尚處于惺忪之中,接著合上眼睛做起打盹兒的樣子。
即便閉上眼睛,林菲也能領略車窗外的景象。那景象在一個個早晨和一個個傍晚間翻閱的次數太多,已然爛熟于心了。不過某一刻,她還是將眼睛欠開一條縫隙,朝位于江濱大道旁的一排林立的高層瞥過去,并迅速從中尋到一扇窗戶。
她重新閉上眼睛,又感覺自己躺在那間屋子里了,還感覺濱子正睡在身邊,側躺著,由于臉上的皮肉較厚,一部分五官已被擠壓得走了形。
她曾為一覺醒來瞥見如此一張臉而悄然失落過,甚至對自己當初的選擇甚感后悔。心說,如果此刻看到的是一張心儀的臉,或許日子過得差一點兒也無所謂了。當她把眼睛從濱子臉上移開,在屋子里環視了一遭后,則又對自己說,知足吧,眼下的這種日子有多少人掙了一輩子命都沒能過上。別人不說,自己的爸媽不就是例子嗎。再者說,就算找一個模樣滿意的,也未必會像濱子那么待見她。她深知自己多年來已被父母嬌慣成了一副小姐身子,根本不會操持家務。濱子卻很傾心她,從沒把這看成不足。以至婚后一年多里,她始終都享受著好吃懶做的生活。可現在,自己是否還能回到那套房子里,繼續做它的合法主人,她已經不敢確定了。
少許,婆婆一張哭喪的臉浮到她的眼前來。
自從她被查出毛病以后,婆婆的臉就陰云密布起來,還尋到她父母家理論過幾次,說他們早就知道林菲有病卻有意瞞著她和濱子,這分明是在坑濱子。
此番言語不禁令林菲又羞又惱,哭了,抽泣著對濱子說,你媽憑啥這么說呀?既然她這么說,那我也別再坑你了,咱倆干脆離婚算了!
話一出口,她就后悔了,生怕濱子會就勢順著她搭造的斜坡滑下來。
說啥吶?濱子臉紅脖子粗地嚷道,我媽愛咋說咋說唄,我不是沒那么說嘛!
她把頭扭到一邊不看濱子,松了口氣。
隨后不久,她又感覺危機四伏起來。那個醫生的告誡,她當然不會忘,恪守起來也不難。本來,她就對和濱子之間的纏綿有些抵觸,一向都是在濱子提出要求時禮節性地盡一下義務,還要看心情:心情好了,興許會讓濱子盡興;若是不好,還沒等折騰幾下,她便打起哈欠,甚至有時還干脆催促他快點兒做完。
濱子當然也沒忘記那個醫生的話,但他卻熬不住夫妻同床而又始終守在自己的疆域里按兵不動,經常伺機越過界來冒犯她一下。此時的她分明有足夠的理由將其拒之疆界以外,一次次地抵擋了濱子的攻勢。有一次,濱子的攻勢格外兇猛,險些突破了她的防線。情急之下,她竟在推開他的時候罵了一句滾。
她的聲調并不高,卻透著十足的狗急跳墻。濱子頓時轟然坍塌了,尷尬地靜默了一陣就咕咚一聲跳下床,將自己封閉到另一間屋子里苦苦修行去了。
此后的夜晚,兩人就過起了各自為營的日子。只是夜里,白天里依然一如從前。起初,她覺得這樣倒挺好。時間長了,卻漸漸也會想這種相安無事的夜晚對濱子是否有失公平的問題。還由此導出了下一個問題,那就是既然濱子在她這里得不到想要的東西,能否偷偷到別處去找呢?
她便惴惴不安起來,開始注意起濱子的動向。結果,后來一天真的尋到了蛛絲馬跡。
那天,濱子前來接她的時候,身上香噴噴的,面皮間還透著滋潤,一看便知是剛剛洗過澡。在外面洗澡倒沒什么,問題在于濱子跟她解釋說是為了陪一個客戶的時候躲躲閃閃的。于是,她就猜想濱子在洗澡時捎帶干了別的。于是,一連幾天臉上都沒有好顏色。
其實,林菲后來也曾想過,就算濱子在外面背著她干了別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她應該盡量容忍一些。如果她不容忍,長此下去濱子也未必會一直容忍她的。
這么一想,好顏色又回到了她的臉上。不僅如此,接下來的一天,當濱子將她送到單位時,她下車之前還在濱子的胖臉上吻了一下,隨后親昵地說了一聲拜拜老公。這等舉動可是以前從沒有過的,竟讓濱子對著她的背影呆愣了半天才掉頭離開。
……
通勤車駛離濱江大道多時了,林菲仍遲遲不肯游離出那套房子。夜幕已然降臨了,吞沒了寬闊的江面,窗外黑漆漆一片。
此前,她經常希望能獨自一人待在那套房子里。那樣,她覺得自己主人的身份仿佛更為貨真價實。她會悄然地這里走走,那里轉轉,就算是窗外像眼下這樣一片黑暗,她也能從黑暗中尋到一望無際的內容來。這樣的機會并不多。視線中,濱子近乎隨時都在一旁干擾著她。
眼下,機會終于來了,她卻難以進入自己希望的佳境,非但進入不了佳境,反而暴跳如雷起來。因為,濱子當天沒去接她,而且之前也沒打電話告訴她。更可氣的是當她把電話撥過去時,這家伙還拒不接聽,害得她一直在學校傻等,連通勤車都沒坐上。他們學校又處于市郊,根本打不到出租車。后來就給她爸打了求救電話,而她爸說自己已經交班了。無奈之下,她只好叫了一輛拉腳的摩托車把自己送到有公交車的路段……
一路上,她一邊氣惱,一邊揣摩起濱子最近一段時間是否有異常的表現,便想到他當天送自己到單位時,自己沒有吻一下他的臉。其實,她時常忘記這個潛心設計的禮節。若是往常,濱子定會哎哎地伸過胖臉來提醒她。在她行使了這個禮節之后,濱子還會把她攬過來,將一個吻狠狠地還在她的嘴唇上。這一切,并沒在當天早晨被再次重復。她想,自己親濱子不過是在蓄意營造溫情,偶爾為之也罷了。可濱子不一樣,對于他們兩人眼下這個唯一親昵的動作,他忘了,恐怕說明他對這個吻已然不感興趣了。
回到家里后,林菲再給濱子打了幾次電話,得到的始終是和之前毫無二致的結果。后來急了,想給婆婆打電話詢問一番,猶豫再三,終于沒敢。她清楚現在的婆婆根本不愿搭理她。
直到第二天中午,濱子才打電話跟她解釋說昨天因為陪客戶吃飯沒顧上去接她,后來還喝多了。
當時,她的怨氣還沒消,只是礙于正在食堂吃午飯,眾目睽睽的不便發作,只是冷著臉嗯嗯地應他。哪成想濱子接下來竟告訴她說自己當天下午要出差,還說最近一段時間不能接送她了。
走你的吧,不用管我!她生硬地回了一句就掛斷了電話,其間,禁不住想哭,連忙端起餐盤離開餐桌,把尚沒吃完的飯菜統統倒掉了。她本想不把自己的異樣暴露給他人,結果卻適得其反——如此浪費的舉動將食堂管理員惹惱了,當眾狠狠羞臊了她一通。大家的眼睛便齊刷刷地瞥了過來……
有濱子的夜晚,盡管他們分別守在各自的屋子里,她也不會感覺空蕩,更不會因為黑暗而心生恐懼。接下來的日子則不同了,各類猙獰的惡鬼總是不請自來,勢頭甚至超過了她對于自己未來的不祥預感。為此,她先是生出暫且回父母家住一陣子的想法,可轉瞬就將這個想法放棄了。她現在決不能離開。現在離開,如果濱子真的像她料想的那樣,是想解下她這個包袱,自己無疑是主動掃地出門了。她還想過讓她媽過來陪她住一陣,后來也放棄了。她知道婆婆從沒瞧起過自己的家人,一旦得知了消息,會覺得她媽是乘虛而入地享受別人的好日子來了。
濱子走之前說最近一段時間不能接送她了。看來,肯定不會一天兩天就能回來。這就是說,她再感到害怕,也只能咬牙挺著。
她開亮了所有的燈,使整套房子明如白晝,然后,才顫顫地鉆進被窩里。進了被窩,她還是不敢合上眼睛。只要合上眼睛,所有光亮會頓時化為烏有的……
第一夜,她是在似睡非睡間熬過來的。第二夜,她的恐懼感多少被困倦削弱了幾分。第三夜,她比前兩夜明顯踏實了一些。從第四夜開始,她竟嘗試著將其他區域的燈一盞一盞地關掉,最終,只留下臥室床頭上一盞了。這還不算,她還將那盞燈的光亮調得十分微弱。
對于自己在近幾日的歷練中取得的成就,她還沾沾自喜起來,心里發著感慨說,很多的恐懼,其實都屬于庸人自擾。只要不老胡思亂想,它也就沒趣兒地躲到一邊去了。
那應該是幾天來她沉入夢境的最快的一次,卻沒成想竟在半夜時分被客廳里傳來的輕微的開門聲驚醒過來。起初,她懷疑自己做了一個噩夢,可凝神細聽了一陣,便證實了一切并非虛幻,頓時心驚肉跳起來。不過,只是一瞬而已,隨后,就斷定是濱子回來了。
這些天里,她對濱子的怨氣一直沒停息過,只是在恐怖的夜晚跟前淡弱一些罷了。眼下,濱子回來了,深更半夜的不說,之前還連招呼都不打,更令她忍無可忍了,真想沖出臥室狠狠發泄一通。可轉念一想,覺得似乎應該先看看濱子接下來的反應再說。于是,她就一直靜靜地躺著,仿佛根本沒覺察到任何動靜一樣。
門外開始響起了腳步聲,很輕,在客廳里轉了一圈兒。她想,這家伙轉悠啥呢?難道是想推門進來和她打個照面嗎?如果是那樣的話,她可不想搭理他,不管他是輕聲地對自己說一聲,老婆我回來了,還是躡手躡腳地摸過來在她的嘴唇上親一下,她都要做出一副渾然不覺的樣子,直到他訕訕地離開為止。
然而,屋外的腳步聲只是轉了一圈兒,就踅進另一間屋子里去了。一時間,她竟又感覺很是失落。
轉日,林菲若無其事地出了臥室,眼睛卻瞥著另一間屋子,見屋門正開著,就悄悄瞥了進去。結果,并沒瞥見濱子的一根毫毛,倒是覓到了一片狼藉……
警察當日便證實了她家是被盜了,損失了兩件裘皮和一塊勞力士。
盜賊深夜入戶行竊的事情并不少見,其中也不乏在家里有人的情況下。不過,隨后她和濱子還是分頭遭到警察的訊問——既然房門上沒發現絲毫撬軋的痕跡,也就不排除內鬼的可能。
對她的訊問,就在那套房子里;而濱子卻是在電話的另一頭。他確實沒回來,若不信,他可以用當地的座機來證實。
警察煞有介事地訊問過了他們兩人之后,就鳴金收兵了。此后,也沒有相關的下文,不了了之。而無論怎樣,她也不敢在這套房子里繼續住下去了……
學院的位置,原本是一片片近郊農民的莊稼地。自他們遷到這里之后,其他一些院校和一些居民小區也陸續紛至沓來。莊稼地也就逐漸被蠶食掉了。
他們教研室里共計六人,四女兩男。六人中,除了主任已人屆中年,其他幾個都與林菲相差不多。
主任是這個教研室的元老,也是他們院里為數不多的帥氣的男性。當初,林菲曾暗自對這個頂頭上司心生過好感。她的好感當然不僅僅是傾慕于這個男人的帥氣,他家境的殷實以及各方面的能力也都是令她仰望不已的。她想,女人就應該嫁給這等男人。
主任輕易就讀懂了林菲眼里的內容,開始對她日漸關心起來,或者下班時主動開車送她,或者搞來各類演出的票與她一起去看,當然也不乏請她吃飯一類的事情。無論是與主任置身于車里還是劇場和餐館中,林菲心里總顯得很復雜,會時而愜意,時而惆悵。愜意是因為近在咫尺的是一個充滿成熟魅力的男人;惆悵是因為這個男人早已屬于別的女人了。
盡管他們兩人的關系不乏幾分曖昧,主任卻沒有過更進一步的舉動。或許他曾那么想過,又怕引火燒身吧?不過,相對其他人,他對林菲還是關照得更多一些。
踏進辦公室的時候,主任還沒到。他是上司,不用像部下一樣到那么早。其他人都在忙活著掃除。主任喜歡干凈。據說,是在有潔癖的老婆嚴厲管教下磨煉出來的。他要求部下每天到單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掃辦公室,若是他來時看見屋里不宛若真空一般,就會大為光火。
自得病以后,林菲就對自己格外呵護起來,即使在單位,覺得也應該相應得到照顧。起初,當大家忙活的時候,礙于情面,她也會煞有介事地擺擺干活兒的造型。同事們都知道她身體的狀況,會故作體貼地說你放下吧,這點事兒我們干就行了。久而久之,她連造型都懶得擺了。可也不忍眼睜睜看別人忙,索性躲到自己上課的舞蹈房里去躲一陣風頭。
一進舞蹈房,頓覺一股涼風迎面撲來。她想起昨天下午召開了一個對院領導綜合測評的大會,無非是去給領導們投人氣票。由于去的匆忙,她當時沒顧上關窗戶。散會后,已到了發通勤的時間。結果,窗戶就整整開了一夜。幸虧沒下雨,否則屋子里的地毯可就遭殃了。
正準備過去關窗戶的一瞬,耳畔突然傳來一串撲啦啦的聲音,隨之再看見一只小東西從地上騰空而起。她不禁驚栗地尖叫一聲逃到了門外。
她顫顫地湊向了屋門上方的玻璃,發現一只小鳥正滿屋子亂飛。看來,這小東西一不留神,竟順著敞開的窗戶誤闖了一個并不屬于自己的世界。眼下,無疑是被她嚇到了,正驚慌失措地尋路而逃呢。
林菲決定暫時先守在門外,等那只鳥沿原路飛出窗外再進去。等了半天,那只鳥一直都對窗戶上的玻璃和布滿墻上的鏡子做出錯誤的判斷,竟連連碰壁。這未免讓她很是著急,忍不住拉門進了屋,使勁扇著手,將它朝那扇敞開的窗戶趕。
小鳥不識她的用意,誤以為她是要捉自己,愈發慌亂了,連續撞在窗戶和鏡子上,砰砰的聲音一下下地撕扯著她的心,每一下撕扯,都讓她的心生出一陣疼痛的震顫。
終于,鏡子上發出一個最為沉悶的碰撞聲。隨之,小鳥便栽到了地上,使勁掙扎著。掙扎了半天,沒能再飛起來,就放棄了。
她悄然湊到近前,看清是一只麻雀,想起從小她爸就總喜歡管自己叫小麻雀,直到現在還偶爾會那么叫她。
她躬下身子試探地將手伸過去,在麻雀身上觸了觸。麻雀睜了一下眼睛,即刻又閉上了。她再觸一下,麻雀又將睜眼的動作重復了一次。而這一次,僅僅睜開了一半。
她頓時生出一陣凄楚,想,它恐怕是死了,卻不甘心,一邊繼續用手觸它,一邊高聲叫著,哎,醒醒!醒醒……
麻雀始終沒做絲毫反應。她只好無奈地直起身來,愣愣地看了它一陣,開始思忖如何處置掉它。其實,這并不難,從地上捏起來朝窗外一丟就是了。可她不敢,雖然她剛才還用手指觸過它,但那時麻雀還活著,現在卻分明已成為一具尸體。
猶豫半天,她才扭身拿過撮子和笤帚,顫顫地將麻雀掃進撮子里,來到那扇敞開的窗戶跟前,剛將撮子伸出窗外,又收了回來。窗臺上正鋪滿上午清爽的陽光。她想,它或許并沒有死,只是暈過去罷了,大概過一會兒就能在暖暖的陽光下蘇醒過來。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把麻雀倒在了窗臺上……
這時,辦公室的方向有人拖著長聲喊她,讓她去接電話。
……
與辦公室還間隔若干距離,林菲就聽見里面傳出一陣嘻嘻哈哈的說笑聲。她停下腳來,疑神疑鬼地側耳靜聽了片刻,直到確認了笑聲的內容和她無關后才邁進屋來。
對于大家的說笑,她并無心摻和,不過還是假作一副饒有興致地問,說啥吶,樂成這樣?而不等有人回答,便自顧接電話了。
喂,電話里傳出了濱子的聲音。
她心里頓時一陣慌亂,連忙說,等我給你打過去,就掛斷了座機,然后,從椅子上抓過挎包取出手機來行蹤鬼祟地出了辦公室,其間,還用余光瞥瞥大家——并沒人在意她的反應,仍沉浸在先前的內容里。
自打濱子出差走了以后,他們兩人只通過幾次電話,多半是濱子打來的,無非是草草的問候和解釋自己還得過一段時間才能回去。是她主動打給濱子的,只有一次,就是發現家里被盜那天報警之前,主要為了核實他當晚是否回來過。
雖然濱子拿出了他根本沒回來的證明,林菲還是覺得其中有詐:為什么早不被盜晚不被盜,偏趕上她獨自在家的時候被盜呢?她不禁猜想此事很有可能是濱子策劃的,把鑰匙給了他人,制造了一個被盜的假象。如果是這樣,那只能說明一點,濱子確實是想要遺棄她了。礙于情面,難于當面直說,就先拿出差做借口躲避她,而后,又跟她耍了這么一套低劣的把戲。
她越想越認可自己的猜測,也就越覺得濱子可恨起來,暗自發狠說,既然你跟我來這手,那我也就不客氣了,就跟你抻著,絕不主動跟你提出離婚……
直到重新返回舞蹈房,她才撥通了濱子的電話。
電話里的濱子明顯有些支吾,說自己前一陣回來過一次,不過沒待兩天又走了。
林菲只是冷冷地嗯著,沒有其他言詞。
后來,濱子也似乎沒話了。
她就說,要是沒事兒我就撂了。
濱子這時才說,下班后等我去接你。
……
林菲的身影遠遠地映在舞蹈房寬大的鏡子里。由于沒開燈,加之窗口又懸著陽光,那身影只是一個孤零零的輪廓。
下班后等我去接你,下班后等我去接你……
濱子最后撂下的那句話始終拖著一串回音來來去去,她也一再努力地分辨那串回音里浸透的內容,時而想,或許事情并沒朝著她當初預測的方向發展,一切只是自己庸人自擾罷了;時而又想,或許濱子終于被她抻煩了,忍不住了,接她只是借口,真正的用意是想和她當面攤牌……
某一瞬,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她在鏡子里瞥見了那扇窗戶的窗臺,發現竟然空蕩了。她連忙回過頭去,得到了與鏡子一致的現實,還是不信,懷疑那只麻雀是被一陣風吹落到外頭去了,扭身過去,將身子探出窗外四下尋覓了一陣,一片羽毛也沒尋見,縮回身來。
看來,一切果然像她希望的那樣,那只麻雀真的起死回生,重新飛回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窗前的陽光十分炫目,林菲瞇起眼睛朝湛藍的天空中勾描的幾條高壓線望過去。高壓線上正落著幾只麻雀,唧唧喳喳地叫著。她想,興許那只重生的麻雀也在其中,正跟同伴們白話自己大難不死的經歷呢。
她收回眼睛,又恍惚看見了另一幕:是多年以前,她剛參加了藝術學院考試回來,看見一只喜鵲在她家對面一棟樓頂上嘎嘎叫個不停。她媽當時還說,這該是個好兆頭……
她的眼睛又亮了一下,莫非這又是一個好兆頭?
以前,濱子一概都是尚沒到下班的時間就發短信告訴林菲他已經到了。接到短信之前,林菲多半都是守在舞蹈房里等他。這樣,更便于提前溜走又不被其他人覺察。
不過,眼下她并沒按慣例行事,一直待在辦公室里與同事們一起嘮著閑嗑。她要等到大家都披掛整齊去趕通勤車時與他們一起出門。她要讓他們都看到濱子來接她……
對于大家東西南北的話題,林菲雖不時插話,內心里卻一直沿著自己的方向走著。在她的方向里,濱子已經到了,坐在那輛雷克薩斯里先給她發了短信,而后便扭過頭來朝門口張望著;在她的方向里,她也來到了門口,神情有些局促,垂著眼簾,始終猜想著自己坐進車里時,濱子會是如何表現;在她的方向里,濱子仍像從前一樣沖她齜牙傻笑一下,緊接著嘬起胖乎乎的大臉上的一張嘴朝她賴賴地湊過來,而她由于久別的生疏,竟忸怩地推就了一下……
轉瞬,她也則又沿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走起來:她坐進車里時,濱子雖然齜牙沖她笑了,不過笑得勉強而又尷尬,接下來也沒再做任何其他動作,只是瞄了一眼她的臉淡淡地說,好像氣色好多了。
那么,之后還將是什么呢?大概濱子會將她拉到一家既幽雅而又安靜的餐館里,與她共進一頓最后的晚餐。通常,只有他們兩人一起吃飯時,濱子很少喝酒。這一次,想必他會借助酒力來將心里的愧疚沖刷掉。當然,終于說出要跟自己離婚時,他興許會顯出幾分難過,甚至會憋憋屈屈地流幾滴眼淚,說他也不愿意這么做,可是……可是……
別可是了!她應該就此打斷他,告訴他現在說這些已經沒勁了,還是說說究竟該怎么離吧。濱子應該清楚這話的意思,還應該早已盤算好了補償她的價碼。那就痛快地表態算了,讓她聽聽開價是否令她感覺滿意。如果不滿意,她一定會跟他討價還價的……
前廳里鋪就的花崗巖水面似的浸著傍晚的陽光和林菲一行人的倒影。雖然被一雙雙腳踏得嘎達嘎達地響,卻始終波瀾不驚。
尚沒來到門口,林菲就透過玻璃門瞥見了那輛雷克薩斯。她的神情并沒現出任何變化,十分泰然,可心卻跳得異常急劇。當然,這一點也只有她自己能覺察到。
作者簡介:老長,本名仉立國,1963年出生。1987年畢業于哈爾濱師范大學藝術學院美術教育系,現為中學美術教師,黑龍江省美術家協會會員,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小說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芙蓉》、《小說林》、《廣州文藝》等文學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