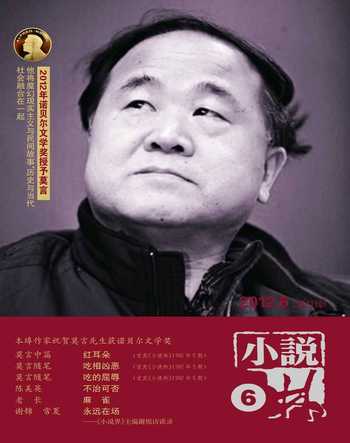第一萬名祭品
金鈴子基本上不講理。她畫油畫,刺繡,兢兢業(yè)業(yè)練毛筆字,光著腳丫子爬樹,像個(gè)女巫似的吟唱詩經(jīng)或楚辭。她聲明,“這一切都是為詩歌服務(wù)的”,因?yàn)槲ㄓ性姼璨攀悄康模笆怯脕碜非蟮摹薄2贿^,她卻把自己概括為:歌者,繪畫者。
若試圖邏輯金鈴子,那大約會(huì)被活活悶死。在“用來玩”的油畫里,金鈴子的無理更加肆無忌憚:她的馬顏色深粉,正在從淺草上起飛。她的花恨不得攬盡世間的奢華。她的女人身裹金蛇面朝大海。那種迎面刷來、帶有壓迫力的色彩,極容易令人想起同樣不講理的他們:以色彩為愛情的夏迦爾,艷麗而神秘的奧基弗,或者幾乎只使用藍(lán)與紅的塔馬約。
如果金鈴子沒有如此廣泛的涉獵,那么她一定是妖精變的,她偏得了太濃厚的天賦。看看這個(gè)玩得興致勃勃的人在玩什么?她要抵達(dá)某種極端的執(zhí)意有如愛情一樣強(qiáng)烈。
全部由原色構(gòu)筑的“惑”系列,使一個(gè)玩家的野心無可掩藏——玩得興起的時(shí)候當(dāng)然是有的,但她似乎不大在意沿途的風(fēng)景,她要找的是原點(diǎn)。在時(shí)間的盡頭,具象的一切都將被忽略。響亮的紅與黑使主體與背景完全混淆,它們對(duì)峙亦互補(bǔ),構(gòu)成了難解難分的詭譎空間。它們都是實(shí)體也都是空隙,都是躍動(dòng)也都是靜止。這樣一個(gè)原點(diǎn)是反概念的,拒絕瑣屑與累贅,具有簡(jiǎn)單明了的秩序,渾然一體,不可分析。繪畫不體現(xiàn)時(shí)間的長度(萊辛《拉奧孔》)嗎?在詩人涂畫的大惑之中,我忽然覺得,這窮追不舍的表達(dá)里,時(shí)間也被揉成一團(tuán),揉進(jìn)了原色內(nèi)部。所謂時(shí)空,原本就是難解難分的。所以,在恰如其分的想象里,大惑化為安寧,強(qiáng)烈化為均衡與純潔。
這消弭一切界限的大混沌,也許正是世界的本色吧。我們的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略無分別。所以,高更有追問不休的《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么?我們往何處去?》,便一定會(huì)有旋轉(zhuǎn)的《舞蹈》。所以,梵高在自己的肖像中,畫盡了世間一切表情——其中的滄桑各自不同,但也都如嬰兒般懵懂。
生命可能在怎樣的維度上打開,是一個(gè)因人而迥異的問題。藝術(shù)品與主體的一體關(guān)系,也許是現(xiàn)代藝術(shù)最可貴的發(fā)現(xiàn)之一。俗世的一切欲望,或盛開成為繁花,或燃燒成為灰燼。化欲為花,也許正是藝術(shù)最本質(zhì)的用途。馬蒂斯說,他無法區(qū)別對(duì)生活具有的感情和表現(xiàn)感情的方法。梵高瘋狂地?fù)]霍顏色,“不是要達(dá)到局部的真實(shí),而是要啟示某種激情”。
要用力,花才會(huì)開。金鈴子懷有從不萎頓的激情,她需要的只是有力更有力的手段。在這玩出來的布面油畫中,不僅色彩,連輪廓和透視比例都是狠辣的,為了表達(dá)的痛徹,她不吝于夸張和變形。她的色彩關(guān)系及輪廓關(guān)系,簡(jiǎn)單明了又刁蠻無道。你不得不承認(rèn),在某種意義上,造型方法越簡(jiǎn)單,越不明就里,畫面的抽象性越強(qiáng),表達(dá)力也越強(qiáng)大。因?yàn)椋谖唇?jīng)規(guī)則損傷的想象力中,生命的強(qiáng)烈性才可能得以充分的體現(xiàn)。
然而這種強(qiáng)烈的主觀性卻是以頗具功夫的準(zhǔn)確筆觸造成的。油畫的制作過程是繁瑣的。我不大能夠想象金鈴子會(huì)在筆法上循規(guī)蹈矩。并非沒有耐心。她完全有耐心慢慢熟悉直至洞悉一種規(guī)矩。但她不會(huì)恪守,她打破規(guī)矩毫不吝惜。這些颶風(fēng)般的筆觸,與其說來自她得天獨(dú)厚的直覺,不如說得自對(duì)理性或規(guī)矩的傲視。她的筆觸的確是謹(jǐn)慎的,但這謹(jǐn)慎并沒有獻(xiàn)給對(duì)世間實(shí)在的再現(xiàn),而是獻(xiàn)給了心靈與想象。
金鈴子說,詩歌是她尋求醫(yī)治心靈的良藥。我們與世界的關(guān)系常常是空洞的,但是,隱藏其間的驕傲與卑微、繁華與孤絕,卻也十分真實(shí)。警覺這樣的物化與沉淪是困難的吧?所以,又一個(gè)不惜揮霍生命的人,把自己化為了祭品:“我在我的孤獨(dú)中狩獵/ 這茂密的森林哦/ 我必須費(fèi)盡全身的力量,才能獵殺自己……”意識(shí)到我們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認(rèn)識(shí)存在著悖謬與混亂,也許是自我治療的基本動(dòng)機(jī)。馬格瑞特把藍(lán)天白云和黑色屋子里的燈光畫在同一張畫布上,這似乎是違反造型藝術(shù)的取材規(guī)律的,但畫家看著自己的杰作說:“我將這令人喜出望外的力量稱為詩。”而金鈴子說的是:“我想用另外一種語言表現(xiàn)詩歌。”那么,油畫大體是她的輔藥了。
世界總是把自己的癲狂最先傳染給這樣一些人,仿佛這樣才能使他們的表達(dá)充滿魔力。我看著這不可理喻的色塊和線條,亦如看見十字架,看見代罪人。一瞬間,看的人也仿佛走在了通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心中充滿了痛苦。
作者簡(jiǎn)介:魚禾,女,畢業(yè)于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現(xiàn)為鄭州市文聯(lián)副主席。2008年從事寫作。主要作品:散文集《摧眉》、《相對(duì)》;長篇小說《情意很輕,身體很重》(原名《中度悲觀》);中短篇小說《你怎么哭了》、《有病》等;系列讀書隨筆《非常在》;長篇隨筆《逃離》、《迫在眉睫的俗世》等,專欄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