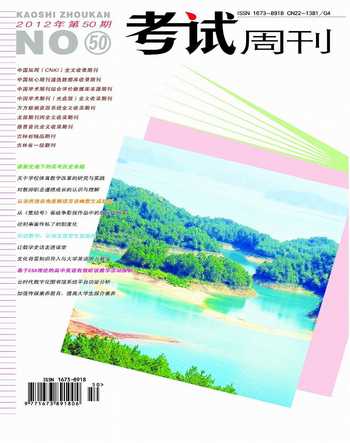小議龐德意象詩歌之“意象”
韓海燕
摘要: 西方意象派是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觀念的影響下產生的,由于文化差異等影響,龐德的意象詩歌中的“意象”與中國詩歌的“意象”不盡相同。
關鍵詞: 龐德詩歌意象局限性
20世紀初葉,后浪漫主義主義和后象征主義氛圍中的英美詩歌過分張揚個性,無病呻吟,語言拖沓見長。為扭轉這種困境,以龐德為代表的一批詩人積極吸收外來營養(yǎng),從古典詩歌傳統(tǒng)中借鑒簡雋明晰、表現(xiàn)力強的意象,建立了意象詩派。表達簡約、句法單純,實力強勁的中國詩歌為英美詩壇注入了一縷清風,極大地改變了英美詩歌的生態(tài)。
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借鑒,主要是在中國詩歌的“意象”上。本文從以下幾方面研究龐德詩歌的“意象”。
一、中國詩歌的“意象”
在談到龐德意象詩歌之意象時,我們先看中國詩歌對“意象”一詞的理解。中國的古代文學批評是一種感性的批評,并沒有把“意象”一詞用專業(yè)的詞語解釋出來。嚴格來說,中國“意象主義詩歌”并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也沒有一個意象主義的流派,更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意象”這個概念卻早已融入我國的古典文學之中。
關于意象理論,在中國,最早的說法從《易經(jīng)》說起,書中有“觀物取象”、“立意以盡象”的說法。根據(jù)歷史推斷,這里的“象”指的是卦象,是抽象的事物。而詩歌中的“象”則是物象,是具體可感的事物。“意”與“象”的關系莫過于“情”與“景”、“心”與“物”的關系,對于想象力極為豐富的詩人而言,最好的詩歌作品無非是情與景的完美交融。關于這樣的論述還有,如劉勰指出詩歌構思應“神與物游”,謝榛認為“景乃詩之媒”,王夫之提出“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王國維提出“一切景語皆情語也”。由此推及,古人作詩是將內心的意借助與外在的景物表達出來的,象只是一種假托,寄意于象。詩歌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一個由觀察、感受、揣摩再到表達的過程。選定一個物象,便將自身的所思所感寄托于它,把她融進感情世界面,形成一個藝術天地,將這樣的感受傳給讀者,增加其想象的空間。
可以這樣理解,意象通常是指“意中之象”,主觀情感與客觀的物象融合而成的心象,意象的組合則是為了構建一個意境,從而達到情與景的交融,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再如“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這其中的意象雖是自然景物,但無不帶著作者的思想感情。除此以外,還有很多社會事物也可作為意象,如人物形象、生活畫面、歷史事實等,都可以寄托個人情思。在眾多的意象結合在同一個作品當中,呈現(xiàn)出一個完整的畫面時,就形成了一個意境,以馬致遠《天凈沙·秋思》為例:“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通篇由互不關涉的十二個意象組成,但它們集中起來,卻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空間,時值傍晚時分,面對西沉的太陽,孑然一身的旅客顯得如此孤獨與渺小,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肝腸寸斷?
二、 西方(龐德)詩歌的意象
意象派,是歐美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個詩歌流派,其主要創(chuàng)始人是龐德,后期領導人為洛厄爾,均為美國詩人。還有英國詩人代表人物弗林特、阿爾丁頓等,西方文學批評是一種理性的文學批評,當中國的意象傳入西方之后,他們立即對意象開始做出了理性探索性的定義。“意象主義”一詞的提出在龐德任特刊編輯時,將杜利特爾、阿爾丁頓的詩作以“意象主義者”的名義發(fā)表于該刊物上,龐德是意象主義理論的核心人物。對于“意象”的定義,他曾經(jīng)有三次論述,1913年3月,他第一次對意象的概念作出了論述:An Image is which presents an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complex in an instant of time.(意象呈現(xiàn)瞬間當中產生的智力和情緒上的集合體。)[2]但并未說清楚“意象”究竟是什么,只是說詩歌中的意象會刺激讀者產生某種心理反應,反之,不能刺激讀者產生心理反應的意象就不能算作是詩歌意象。年輕的龐德對意象的認識也是不清楚的,但他也在一步步尋求著科學的答案,1914年9月,他對意象作出了第二次論述:意象并非一個意念。它是一個能量輻射的中心或者集束——我只能稱之為漩渦。意念不斷地涌進、涌過、涌出這個漩渦[3]。這一次強調了意象的一個新特點:處于一種劇烈活動的狀態(tài)。這只是一種表象,依然沒有回答意象是什么的問題。在1915年的1月,龐德第三次對意象進行論述:意象不僅僅是一個意念。意象是一個融合在一起的意念的漩渦或者集合,充滿著能量[4]。“充滿著能量”意在說明意象擁有能量,這樣說來,就算是靜態(tài)的意象也同樣是具有能量特征的。這些是“意象派”所做出的理論闡釋,但依然沒有一個清楚、準確的定論,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探討,但意象派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對于物象的觀察,要求精確,表達上簡潔、凝練、清新,無需華麗的辭藻,這就決定了意象并非是簡單的一般形象,而是主觀與客觀的相互交融,追求詩歌的具象性、簡練性、音樂性是意象派的終極目標。同時提倡“堅實”的詩歌風格,強調用客觀精煉的意象發(fā)泄主觀的情感,采用短小精悍的詩歌體式,如龐德的《巴黎地鐵車站》: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人群中這些幽靈般的面孔,
濕漉漉的、黑枝條上的花瓣
最后,在作品《意象主義者的幾個“不”》中龐德下了定義:“意象是在一剎那間里呈現(xiàn)出來的理智與情感的復合體。”[6]強調了主觀情感與客觀物象的結合。龐德對于“意”的解釋受到表現(xiàn)主義的影響,把詩看作對思想感情的表現(xiàn),他曾經(jīng)說:“詩歌是極大感情價值的表述。”詩歌的韻律、節(jié)奏由感情來組織。“象”是情感的一種呈現(xiàn),由描寫外物來表達內心。在龐德的意象理論中意象包含“意”、“象”兩個方面,“象”是自然物象,他幫助詩人完成理智對內心經(jīng)驗的呈現(xiàn),詩歌借助意象表現(xiàn)出來就會發(fā)生質的飛躍,成為意象。
龐德對意象在詩歌中的作用是這樣說的:“正是這樣一個‘復合物的呈現(xiàn)同時給予一種突然解放的感覺:那種從時間局限和空間局限中擺脫出來的自由感覺”。他還認為意象可以直接表現(xiàn)事物,這是意象主義的基本思想,他們的詩歌群體的創(chuàng)作趨向與詩歌不以描繪、敘述取勝。
三、 龐德詩歌意象的局限性
龐德對對“意象”一詞的理解應該說和中國的意象基本呈現(xiàn)出了一致性,但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中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希臘三面臨海,懸崖峭壁,石多土少,常年遭受風浪的襲擊,糧食大部分靠海外進口。險惡的自然環(huán)境,對希臘人提出挑戰(zhàn),但沒有惡劣到把人完全壓倒,不能發(fā)展。要在這種環(huán)境中生存,就要善于運用理性思考,采用不同的生存策略應付外在環(huán)境的變化,險惡的自然環(huán)境調動了古希臘人的積極性,刺激他們通過開動腦筋,應用知識智慧,掌握技術戰(zhàn)勝自然,求得民族的生存發(fā)展。崇拜知識的好奇心,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民族精神傾向,對未知世界和新領域無止境的征服欲,不斷向外擴張。古希臘的文明是一種開放式商業(yè)文明,人充滿了好奇心,一路探索、追逐大自然的神奇奧秘,人是自然的征服者,人是主體,以功利的態(tài)度參與并改造自然,不能參與大自然當中,與自然融為一體。
中華文明則以儒道文化為主導,封閉式的農耕文明,是一種參與到大自然當中,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精神文明。在情感方面的追求,中華民族無疑是偏于感性而又純樸的,以遵循自然規(guī)律、順應自然的態(tài)度和自然界對話,展現(xiàn)出天然的樂生傾向。中國的詩歌自然呈現(xiàn)出意象中的“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交融,而西方的意象則存在著一定的“意”和“象”的分裂,從而沒有了中國詩歌含蓄雋永的美感。中西語言文字的不同使龐德的意象產生了局限性,中國的漢字既可以表音,又可以表意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只是表音文字,因此,中國古典詩歌的內在意蘊就很豐富了,這是拼音文字無法超越的。龐德的詩歌因為兩個方面的影響,使“意象”大多只是外在的模仿,外在的形似而無內在的神似,西方因為文字的影響,所以必須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發(fā)表議論補充表達,而龐德的意象詩歌造成在詩歌中發(fā)表議論、抒發(fā)主觀感情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對詩人想象力產生一種束縛,致使詩歌思想感情一度貧乏,不利于這一流派的長遠發(fā)展。
參考文獻:
[1]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三聯(lián)書店,1999.
[2]彼德瓊斯.裘小龍譯.意象派詩選.漓江出版社出版,1986.
[3]張鐵夫,季水河.比較文學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4]陳斌.淺談龐德與意象派詩歌.科技信息,20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