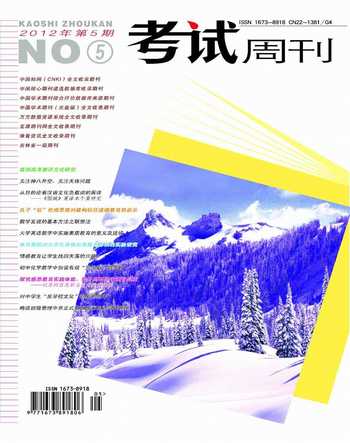淺析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
鄭偉華
當代宋詞專家夏承燾先生曾說:“在婉約派這一詞派中,她的詞應該說是成就最高的,她是整個北宋婉約派中最恰當的代表人。”能得到這么高評價的,唯有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李清照是一位曠世才女,她的詞作委婉含蓄、情意綿綿,可謂“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她才調絕倫,詩詞創作及書畫藝術作品皆斐然可觀。李清照以自成一格的詞作,異軍突起,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她既是宋詞的大家,又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之一。本文就李清照詞中的情感內容和女性形象描寫進行探析。
一、李清照詞中的情感內容前后期有著明顯的不同
李清照的詞被稱為“易安體”,被推崇為“無一首不工”(清·李調元)。從優裕走向苦難的現實生活,釀就了李清照一顆千回百轉的詞心。她的詞以“靖康之變”為界,前后期有著明顯的不同。隨著她生活的發展與變化,其詞作水平也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南渡以前,其作品主要是對大自然的描繪,對真摯愛情的抒發,對離愁別緒的抒寫,風格清新明麗,意境優美。南渡以后,詞風有了改變,以抒發亡國之痛為基調,既寫個人的悲苦,又表現時代的悲劇;既悲傷于自己的身世和失去的幸福,又憂傷民族災難的深重。故而后期詞作傷時感世,悼亡思鄉,無論是思想的深度,還是藝術概括的強度,都比前期詞作有很大的提高。
(一)前期詞中的情感表達偏重于哀愁、感傷。
前期,李清照過著優裕的生活,作品主要是對大自然的描繪,對真摯愛情的抒發,對離愁別緒的抒寫。李清照的前期詞,大部分反映的是她少女、少婦時期的閨閣家園生活,表達出她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愛情生的追求,洋溢著青春生命的活力。詞人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滲透到一切客觀事物,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從而更深層次地表達出詞人對美好事物的熱愛,給人以美感的細致經驗。例如《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昨夜雨疏風驟”)這兩首熱情歌頌自然的小令,用明白曉暢的語言,輕松的筆調真實地現出一位活潑率真、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的女主人公形象。后一首(“昨夜雨疏風驟”)尤為傳神地表達出寂寞深閨中少婦惜春憐花的無比惆悵的細膩感情。
李清照前期詞中還有不少是抒寫離愁別緒的。在李清照生命的前期,曾有二十六年美滿的夫婦生活。趙明誠曾經兩次異地為官,李清照未隨同赴任,小別輕分促使李清照寫了不少傳誦千古的佳作,因而李清照前期詞更多的是表達閨閣之情的相思閑愁,這種前期“愁”是以幸福美滿為前提的,是充滿著憧憬的“愁”,生動地體現出他們夫妻之間真摯、深厚、纏綿的伉儷之情。例如她的名篇《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這首詞,便以花、以水作比,吐露了思念離人的相思之苦,體現出詞人對丈夫的真摯感情。即使是眼前的一點點歡樂使愁眉稍解,也不能頌臾忘情:“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將愁思具體化,讓人理解到了詞人內心難以排解的別離苦悶,這是對內心情感和變化的靈動、巧妙、細膩的瞬間捕捉,可見她的一往情深和對愛情的真摯、執著。又如《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生動地寫出了詞人在親人遠離時寂寞愁苦的心境。“人比黃花瘦”這一創造性的形象比喻,將人與黃花相比,寫出了一個愁損離腸的女子瘦弱不堪的形象,把詞人在重陽佳節銷魂蕩魄的相思之苦非常貼切地表達出來。由此可見詞人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多深啊。后來的陳廷烽《白雨齋詞話》評此詞:“深情苦調,元人詞曲往往宗之。”又如《鳳凰臺上憶吹簫》塑造了一個終日凝眸獨對樓前流水等歸舟的思好形象。詞人不直說沒有人了解自己的思念深情,而說:“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把無意識的流水擬人化,成了詞人的知音,通過寫流水的多情來反襯詞人的多情與孤獨。相思閑愁本是詞史上的傳統題材,李清照的獨特就在于寫來不同凡響,耐人尋味,與浮淺庸俗的相思之作不同,它不僅表現了詞人超群的藝術才能,而且表達出她對愛情真摯執著的態度和情感。
李清照的這些詞,以女性的身份來大膽地表達對愛情的追求,這比“男子作閨音”的詞作要更為真切自然。李清照作為一個敏感的女詞人,最為可貴的特點或許就是她敢愛敢恨,敢抒女性的深摯情懷,敢寫內心世界,始終沒有使自己豐富的情感衰退,始終保持著女性極為深摯強烈的情感感受。而且在宋代程朱理學流行的年代里,嶄露鋒芒,情感泉涌,在詞中唱出了自己的內心,細膩地表現出詞人性格的溫柔、深摯、內在的一面。她在《一剪梅》中大膽地傾吐內心的苦悶、強烈的情感和撲不滅的欲望:“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種強烈的愛情思念,委婉動人的情感呼欲望的火焰,一般說來都是密不告人的,尤其是對封建社會的女性而言。可是在李清照的詞中卻對時常含蓄地燃燒:“暖日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齊。“(《蝶戀花·春懷》)這里的入、月、花、夢,都娟娟含情,道盡了女性思念愛人的九回情腸,頗有典雅、凝重的閨秀風度。然而王灼在他的《碧雞漫志》里卻對李清照前期詞的這種纏綿、真實、復雜的相思閑愁作出了批評:“聞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夸張筆墨,無所羞畏。”不過這些批評倒也在一定程度上說出李清照前期詞對封建禮教挑戰的積極意義。
(二)后期詞中的情感表達偏重于悲愴、沉郁。
如果說李清照前期詞作偏重于從女性的角度來表達對人生、對個性、對愛情的強烈欲求,表現出敏感女性既具有的精神苦悶和愛情心理的話,那么她后期詞作則偏重于愛國主義思想情緒的歌唱,以民族情緒和愛國情為主題,在前期詞哀愁感傷的基調上更趨悲愴、沉郁,情感的憂郁也更加深刻化,乃至變前期的“終日凝眸”為后期的“欲語淚先流”,由前期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和對狹窄小園的厭膩轉到后期對“中州盛月”的故國之情和對國破家亡夫死的創巨痛恨。這種心理的轉折是深刻的,因而在情感的表達上便具有很大的不同。
“靖康之亂”導致北宋王朝迅速崩潰,在這次戰亂中,李清照親身經歷了顛沛流離的亂世生活,親眼目睹了哀鴻遍野的慘痛現實。殘酷的社會現實、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詞人的思想開始震蕩。她這時已離開深閨,置身流亡路上,生活發生了急邃的變化。詞人此時也不再只唱前期那種個性苦悶和相思閑愁的歌了,而是轉到比這個思想要求更為動心、更為牽魂的愛國主義情緒上來。這在后期的作品《永遇樂》、《菩薩蠻》(風柔月薄春猶早)中表現突出。《永遇樂·元宵》一詞十分悲愴、沉郁,讀之令人鼻酸。這首詞通過個人今昔的變化及今日臨安(杭州)與昔日汴京(開封)的元宵盛況的對比,把深切的故國之思與強烈的個人身世之悲融合在一起,既表現出她個人的不幸,又體現出當時的時代特點。元宵佳節,人們都在詩酒慶賀,女詞人此時心中卻有著愈發難言的痛苦。友伴來相召,一一被詞人委婉謝絕。詞人此時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及時行樂,不是醉生夢死地尋求解脫,而是國破家亡、身世飄零,不能不思念“中州盛月”、金甌無缺的舊時盛況。詞中寫的臨安慶賞元宵的盛況,則是對在萬方多難、大敵當前的形勢下,“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統治集團的諷刺。詞中“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等句,是對南宋統治者發出的警告,表現出她對偏安江南的不滿,對政治風雨中的南方的憂心。李清照絕不是《套中人》中的別里科夫,晴天憂下雨。這首詞曾深深地感動了南宋末年的許多愛國詞人,劉展翁讀此詞時就“為之涕下”,“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須溪詞》)。可見李清照后期詞作愛國主義情感之深沉動人。
李清照后期還有許多懷念故國舊家的詞作,這些詞作雖然還是抒寫個人生活的感覺,但和前期寫的離愁別緒相比,無論是思想深度還是內容和情感的表達都有了明顯的進展。在這些作品中,既有流離飄零之愁,又有國破家亡之痛;既有個身世之悲,又有慘遭兵荒馬亂之苦,感嘆淪蕩,悼亡懷鄉,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時代的真實,詞作社會意義較強,詞中的主人公形象也不再是昔日因離愁而“人比黃花瘦”的深閨少婦,而是國破家亡、飽經憂患的暮年寡婦了,流露出較多的哀愁、怨嘆及苦恨。這些都非她前期的閨閣閑愁所能比,故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清照這時期的“愁”正是她作為社會的一個清醒者的可貴標志。深刻的思想痛苦遠比淺薄的歡樂更有人生價值,更有思想意義。李清照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最缺乏英雄氣質,最無所作為,奴性十足的悲劇性時代,南宋統治集團在那“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林升)的醉生夢死之中花天酒地,而李清照則痛心國破家亡,始終為此而愁思郁郁,不肯去追歡取樂。她是那個一攤爛醉的社會中憂郁、思考的靈魂。這個靈魂始終在敏銳地感受,深沉地思索,暗暗地流著她的哀國之淚。生在那樣的一個時代,別說是一個國破家亡、孤身飄零的落難敏感女性,就連辛棄疾這樣的硬漢子,都難免蕩下悲愴之淚:“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李清照本是一個有才華與身份的貴族女子,只要愿意,她完全有可能踏入達官貴人的圈子,謔浪于桂堂上,醉生夢死。但她沒有這樣做,而是持著嚴肅的人生態度,在那個燈紅酒綠的生活氛圍里獨自一人憂郁著,尋覓著……她心靈固然有些空虛,但這是探索者找不到人生道路的一種迷惘,完全不同于紙醉金迷者的靈魂空白。在人生道路和內心歷程上,李清照冷冷清清地尋覓著自己嚴肅、獨特卻顯得孤獨的道路: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這是李清照后期詞中的杰作——《聲聲慢》。在這里,詞人以精練的語言概括而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后自己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在短短九十七個字中,她運用了驚人的描寫手腕,展示了自己尋覓時曲折復雜的內心世界。雖然是“竟日愁情,滿紙嗚咽”,調子凄苦,但無一處不是她飽經憂患后的低沉的傾訴,無一處不是她歷盡折磨后的急促的憂嘆,是的,一切都消逝了:那烹茶猜書、笑聲洋溢的日子,繁花壓枝,把玩古人真跡的春晚……但是,中原故土的淪喪,丈夫的病逝,流落江湖的凄涼暮年……這些郁積在心頭的創痕和陰影,卻是難以排除的。在凄風苦雨的秋月黃昏,她若有所尋,如有所覓。……乍暖還寒的時節,晚來的寒風,雁兒南來,黃花憔悴,處處都在觸動著詞人的滿懷愁緒。她深知,她必須突破重重困難,獨自在漫長崎嶇的人生道路上繼續前進。但接著來的梧桐更兼細雨,像是灑不完的遙傷心淚,又引起她無限的愁。郁積在心頭的坎坷淪蕩的憂思,正隨著點點滴滴的雨聲翻騰著。“愁”,是李清照晚年生活的一個核心,是支配著她的思想生活的。“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里不僅集中鮮明地點出了題旨,又顯得很突兀。戛然而止,給人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全詞在情感的表達上有感人至深而又含蓄雋和的藝術效果,生動地體現出李清照詞在藝術上“善于言情”的顯著特色。可以說,李清照的詞沒有一首言情,沒有一首不言細膩動人之情。無論是寫景,詠物,抒寫離愁別緒還是悼亡懷鄉之作。皆在“短幅中藏無數曲折”發出真摯、深厚、婉曲之情,讀起使人感到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就具體作品中的表現而言,無論是“綠肥紅瘦”之類的“詞眼”,或者是“人比黃花瘦”之類的比喻,“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之類的描寫,“欲說還休”之類的內心活動的揭示,以至于“我抱路長嗟日暮”的用典,等等,無不滲透著動人之情。李清照之所以如此善于言情,和她的修養,對生活的深刻感受,以及女性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敢寫、敢愛、敢恨的性格是分不開的。此外,詞人為了表達她深切的情感,還常常調用一切獨特的藝術手段,從側面著筆,運用烘托對此手法,化抽象為具體。例如寫于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詞人流落浙江金華時的《武陵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一個“載”字,寫活了沉甸甸的哀愁,更用虛擬的手法將抽象的愁情化為有實體有重量的形象,真可與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相媲美。
李清照不但是一位言情能手,而且是一位語言大師,其詞往往能“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李清照特別善于用許多“尋常語”既用自然而和諧地表達思想,抒發情感,讀起來既樸素自然,又富于聲調美。《醉花陰》、《聲聲慢》、《武陵春》諸篇,有哪一首不易讀,哪一首不好懂,哪一首表達的意思不新鮮?《聲聲慢》口語,又有疊字、唇齒音、舌音等出奇的創意,更是詞家的空前了。
總的來說,李清照后期詞作與南渡前的詞相比,內容和情感表達上都有著顯著不同。縱觀李清照前后期詞在情感表達上的不同,我不禁想到李調元《雨村詞話》中的一句話:“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把這句話拿來形容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女作家、宋詞的大家李清照,一點也不為過。
二、李清照詞中生動、婉媚秀逸的女性形象
李清照作為女性詞人,詞中表露出的女性感情,既熱烈又恬靜,既微妙又直率,描寫的女性形象更是生動、婉媚秀逸。
(一)前期詞中描寫活潑天真的少女形象和對愛情的大膽追求、感情真摯纏綿、多情的少婦形象。
《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中游玩晚歸的少女形象活潑可愛、清新動人;《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中惜春憐花的妙齡女子形象楚楚動人;《慶清朝慢》中“容華淡佇,綽約俱見天真。待得群花過后,一番風雨晚妝新。妖嬈艷態,妒風笑月”,塑造了一位清淡高潔,沒有經歷世俗風塵的天真聰慧少女形象。《雙調憶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荷葉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這是一首秋游之作,也是較早的一首反彈,這首詞既無高情別緒,又不傷時嘆世,純真無邪的京師官宦小姐還沒有品嘗到人生的艱辛。雖說蓮老荷枯,再似往日的風姿綽約,然而藍天碧水,一望無垠,瀲滟湖水,點翠秋嵐,清廓的山秀水,讓李清照的心胸開闊得如同浩瀚的萬里晴空,一位少女不知愁滋味彈出了一首輕松爽朗的心曲。《點絳唇》則是一首反映待字少女心態的傳神之作。“見客入來,襪劃金釵溜。”體現一位少女的害羞,無處可逃的憨態,“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一位調皮可愛,毫無大家閨秀之感的美麗少女那種好奇、大膽的神態表露無遺。
《小魚山》中獨守閨房的少婦雖然心中充滿怒氣,但“舊來也,著意過今春”體現了對丈夫的諒解,也體現了對愛情渴望而又真摯的內心情感。《滿庭芳》更借典故,以“何遜”所寫詩篇的人物“陳皇后、卓文”自喻,來體現與古人同病相憐,無法言表的難言之隱,以殘梅自喻“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夫妻深情。《醉花陰》的離恨別愁,更讓讀者看到一位重陽獨守空閨,深感寂寞的女子,在佳節之時,不能與親人團聚,只能在夢中寄情相托,半夜中睡夢驚醒,深秋寒夜更突出女子寂寞凄涼的心情。結拍以花擬人,含思婉轉,傾訴了自己對丈夫深深的思念之情。《一剪梅》是體現主人公真情流露的佳作,是初遇政治風波的閨人內心的憂慮之感,讓我們感受到一位真情女子對純潔、正常的愛情生活的渴望,以及內心相思之情,無法排除的痛苦無奈愁悶。這些戀情詞表達的是一種極為細膩的兒女柔情,那就是愛情至上。
(二)后期詞中描寫了在亂世中飽受顛簸流浪之苦,又不失個人情懷抱負的才女形象。
李清照后期詞中既有凄婉悲傷的哀調,又有風流倜儻的大夫之氣,表現出在亂世中飽受顛簸流浪之苦,又不失個人情懷抱負的才女形象。
面對南宋王朝的偏安一隅,李清照揮筆怒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巾幗不讓須眉之氣浩然生起,此時若詞人是男子,必是執鞭上馬、縱橫沙場,絕不做貪生怕死、誤國殃民之奸佞,而在亡夫、被騙的雙重打擊下,流傳千古的名篇《武陵春》中一位遭受黨爭株連、兵燹戰亂、喪偶流寓、“頒金”之誣、再嫁離異、訴訟系獄等人生憂患的悲苦女子站在讀者面前。一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讓人不堪人生重負,不禁淚流滿面。《聲聲慢》敘述作者晚年時期一天從早到晚的所見所聞、親身感受,讓我們看到詞人佇立在蕭瑟的秋風之中,面對憔悴的黃花,飄零的梧桐,在“滴滴答答”的雨聲中孤守的衰敗凄清情景,滿紙嗚咽,字字含淚,如泣如訴地傾吐了淚人內心深處難以言狀的愁苦悲傷之情,從而形象地反映出詞人遭到時代風雨無情摧殘的凄慘處境。
婉約詞派創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婉約風格最大的特色就是抒發女性的個人情感,以別致精巧的言語譜寫多愁善感的內心和細膩微妙的感情世界。但三大家對此有不同的方式,柳永善用直率明白的語言來表達對追求和理解,秦觀善用情景相融、含蓄蘊藉的言語來表露內心世界,而李清照則善用女性身份直接抒寫愛情生活。雖較為直接,但不同于柳永的直淺從俗、坦陳胸臆,表現得極為真摯纏綿。含蓄歌詠愛情的閨情詩與秦觀的裊裊婷婷、幽約曼妙也有不同,表現了女性特有的既熱烈又恬靜,既微妙又真率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少女時期的作品綽約輕倩、自然嫵媚,表現了年輕女性的活潑天真,這非男作家可以流淌的心跡,形成了李清照獨特的抒情方式。李清照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以我筆畫我形,更深刻、逼真地活現女性形象,這一點男性詞人無法比及。
參考文獻:
[1]劉偉明主編.李清照詞選.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6,第一版.
[2]李清照集校·注后記.中華書局出版,1986.2,第一版.
[3]李清照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出版,1984.5,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