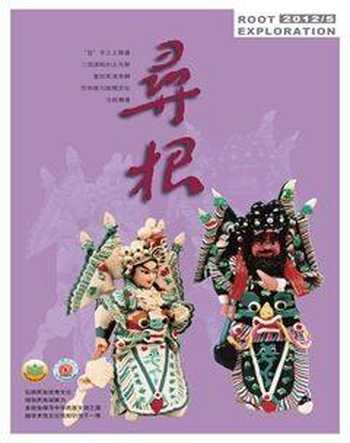尋訪土木村遺址
運濤
在旅游業已經定位為戰略性支柱產業的時代,各地開發爭搶旅游資源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程度,但偏偏真正擁有歷史重大事件遺址的地方對旅游不“感冒”,不開發不宣傳,甚至連本地人都不知曉此地發生過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
我上初中時就知道了懷來縣的土木堡是明朝“土木之變”的發生地。“土木堡”,通志本名“統幕鎮”,唐初,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后訛為“土木”。明永樂初置堡。這次從北京前去游覽,幾經曲折,才找到土木村遺址所在地。
古祠堂
到了土木村后,我先找了家“土木賓館”住下來。可能是土木村距離縣城和鎮里都非常近,所以賓館里沒有客人,房門連鎖都沒有,服務員告訴我不會丟東西的。問起廟,說有一個,就在村部,不過能否進去就不一定了,因為平時廟門都是鎖著的,得找到看門人才能參觀。
我向一個從村委會走出來的人打聽廟的位置,他一指墻邊的老人,說“找他”。老人就是看門人,帶我進入了村委會院內。院內正中,立有一座“為人民服務”的紅色石碑。在偏廂,有一個月亮門,上有紅筆寫著“顯忠祠”,旁邊墻上掛著張家口市“全民國防教育基地”的牌子。
月亮門內迎面是兩塊新立的石碑,一通是“重修顯忠祠記”的“功德碑”,一通是“念奴嬌·憑吊顯忠祠”的“詞碑”。
顯忠祠的院墻為青磚,大門是紅漆木制的,似很普通的農家小院。老人打開銹跡斑斑的門鎖,里面是一個四合院。一座正殿,兩廂配房,院內幾通青色的石碑。
正殿為硬山頂柱廊式建筑,青色琉璃瓦屋頂,木格窗戶的油漆斑駁脫落。正殿高7.5米,朱紅色的大門,掛著顯忠祠的牌匾,抱柱上有一副楹聯:“故老尚余哀兵潰不堪論往事,諸公應自慰君存何必問微軀。”
殿內基本是空的,室內長8米,寬6米。正面供桌,香火并不旺,墻上有“土木顯忠祠原貌圖”,顯示當年的規模比現在要大許多,并列的是當地書畫家張玉生所書祁萬德(當地作家)的“念奴嬌·憑吊顯忠祠”。
四面墻上有墨寫的牌位,應是古跡,如“都督王公貴之位”“都督吳公克勤之位”等,但不知是何時修建所立。
左邊有一個“土木之變中殉難諸臣牌位”,詳細列出了文臣四十六人、武臣十七人、內官一人,共六十四人的名字和官職,后又續增黃綬和樊忠,為六十六人。領銜的文官有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野、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等;領銜的武官有太師張輔(英國公)、朱勇(成國公)、恭順侯吳克忠、泰順侯陳瀛、西寧侯宋瑛等。
右邊有關于顯忠祠的簡介: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師也先率軍大舉入侵,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明英宗朱祁鎮不顧百官勸阻,偕王振并官軍御駕親征。由于倉促上陣,當八月十四日戰敗退至土木城時,追兵趕到,四面圍攻并切斷水源。十五日,也先用假議和之計誘使明軍移營后撤,趁混亂之機,也先率兵將明軍擊潰。致使英宗皇帝被俘,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數百名官宦殉難,五十余萬大軍全軍覆沒。九月,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以翌年為景泰元年(1450年)。祭宣府、土木陣亡將士,葬其遺骸。景泰初,建顯忠祠,于祠內豎神位,祀殉難諸臣,計六十六尊牌位。景泰八年(1457年),南宮奪門,英宗復位,景泰帝代宗被削去皇位,兵部尚書于謙蒙冤。天順元年(1465年),憲宗朱見深即位,平反冤案,恢復了代宗皇帝尊號,為于謙昭雪。憲宗命懷來重修顯忠祠,立碑紀事。祠成之日,憲宗親自撰寫碑文,題寫祠匾。后顯忠祠年久倒塌,遭火災燒殘將盡。明萬歷年間,懷隆兵備道胡思伸主持重修顯忠祠,祠堂高大而壯觀。清初,祠堂被戰火燒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口北道徐炯重建,撰寫碑文,說明牌位失散原因。民國初年,當地百姓又捐資修建。馮玉祥將軍任張家口督辦時,曾瞻仰了顯忠祠。
院內現存最早的碑是明朝萬歷九年(1581年)萬世德的《出塞曲四首·感土木己巳之變卒之乘輿無驚宗社奠安蓋往古所無并及之》:
塞門春去草芊芊,青蹕何由駐九天。一自真人歸大統,至今龍虎護燕然。
雪里穹廬擁至尊,名王歌哭向黃昏。莫言冒頓無情者,猶自嵩呼德漢恩。
胡姬徙倚拂新妝,待得君王一笑將。多少娉婷看北極,一時翹首在昭陽。
胡笳四合夕陽殘,無數貂裘擁漢官。不信六龍親出塞,家家猶記唱回鑾。
令人疑惑的是,其中不知為何兩個“胡”字被摳掉了,難道是犯了清朝滿族的忌諱,屬于敏感字眼?
清朝以后的石碑上的字不太容易辨認,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重修顯忠祠序》碑一塊,嘉慶九年的碑一塊,還有如下碑等。
乾隆時期禮部尚書吉林德保立有一碑《乾隆丙戌初夏謁土木謁顯忠祠有作》:軍行當日出倉皇,遺恨千秋此戰場。碧血至今沈朔漠,丹心終古護君王。垂堂誤入奸閹計,勒鼎遙留詞客傷,昭代春秋隆祀典,滿庭生氣溢馨香。
道光時期立有一碑《土木堡謁顯忠祠》:萬乘當年統六師,匆匆退保力難支。徽欽覆局堪同恨,潘沈英名此并垂。身后猶經焦土劫,魂歸應笑奪門時。專祠翻為中官建,悔禍君心總未知。此碑是道光時期督學使者南川彭邦疇所題。詩中“潘沈”兩字下有注:“二君皆明季安置保安衛者,各有祠宇。”并注:潘謚“忠愍”,沈謚“文肅”。有人認為他們可能是指明代主張抗擊瓦刺和清兵的官員潘宗顏和沈煉,但潘宗顏謚節愍,沈煉謚忠愍,又與之不完全吻合,在清朝時,連《出塞曲》中的“胡”字都抹掉,彭邦疇居然公開在詞中為抗擊清兵的潘宗顏歌功,膽量不小啊,也許是碑上哪里刻錯了字吧。
關了門,上了鎖,給了老人幾元錢,發現在門外還躺有一通古代石碑,上前一看,為清咸豐九年(1859年)《重修隍神廟碑記》,因它與顯忠祠并無關系,所以沒有放到里面鎖起來。據說堡中原有泰山廟、三清宮、馬神廟、七神廟、城隍廟、玉皇閣、花園寺、龍王廟、老爺廟和顯忠祠。這塊碑應該屬于十字街的城隍廟。
有城隍就表示土木堡曾是城池,規模與今天的小村子不可同日而語。明代,土木堡、榆林堡和雞鳴堡是京北三大堡,是長城軍事工程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時也沒有懷來縣,僅僅設置了一個千戶所,無非負責管轄當地的人口、耕地和日常軍政事務。當地居民也主要是來自守軍及其家屬,純粹的農戶并不太多。據《懷來縣志》載:土木堡城,明景泰五年(1454年)復修,筑土木堡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修筑。隆慶三年(1569年)磚甃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周三百五十七丈,池深七尺,闊一丈八尺。環眼看來,曾經橫亙在村中的黃土城垣,如今卻被當成農家的籬笆墻,只有一些農家的黃土房還透著久遠的歷史信息。我一路向南走出村子,一路尋思這些殘破的夯土堆是古堡的遺跡嗎?正在打量中,只見細細的矮小灌木枯枝上迎風掛著沾滿灰塵的塑料袋和地膜,猶如當年大明軍隊凌亂的旌旗。
古城垣
走回村子,很多農戶的院墻上砌著“泰山石敢當”“蓋即石可當沖也”,可惜當時它們卻沒能擋住瓦刺的鐵蹄。很想走近黃土城垣,去觸摸那段歷史的遺物,感受來自祖先的氣息,可幾乎每一段城垣都在人家的院內,成為自家院落高高的后墻頭,我不會貿然進入私人領地,只有一邊遠觀一邊走著。
很快就不再遺憾了,在村東有寫著村名的照壁,照壁背面題有“為人民服務”,建于二〇〇二年九月,旁邊有一左一右兩個巨大的夯土堆,這應當是城門了:一側是裸露而遭風蝕的黃土堆,上面已經長起了荒草;一側是仿長城墩臺的形狀維修過的,上面有“土木堡古城遺址”的字樣。
土木堡古城正是我此行想來尋覓的,居然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幾百年歲月的侵蝕,風變了,云換了,人變了,朝代換了,只有它保留于原地,成為一個見證明代歷史盛極而衰的拐點坐標。
土木之敗,與其說敗給瓦刺敗給也先,不如說敗給了明王朝自己的腐敗,敗給了對開國君王正確治國思想的背叛。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鑒于歷朝歷代因宦官而亡國滅家的經驗教訓,對宦官限制極嚴,立下規章制度,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不許宦官兼任外臣文武銜,不許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級不得超過四品,等等。他還在宮門上掛了一塊高三尺的鐵牌,上面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幾個大字,結果王振把這些都顛覆了。王振原來是個讀書人,但書讀得并不好,中舉人、考進士根本沒有希望,于是他便自閹入宮。入宮后他即服侍太子。宣宗皇帝駕崩,太子繼承皇位。新皇剛剛九歲,還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于是對王振很倚重,讓他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監太監。起初,太皇太后張氏和內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對宦官很警覺,沒有讓王振參政,然而隨著張氏和“三楊”的相繼去世或退隱,在小皇帝的放縱下,王振開始大權獨攬,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然后壓制真正有才能的人,以重典治御大臣。結果,誰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就會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時間一久,向王振送禮成了官場中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如果有人不送禮,也要受到懲罰。王振擅權,根本不懂也不在意加強北方邊防,反而接受瓦刺賄賂,與瓦刺貴族進行走私交易。他每年私造大量箭鏃,送給瓦刺,瓦刺則以良馬還贈王振作為報答。正統十四年,因沒有滿足瓦刺對賞賜的需要,瓦刺首領也先兵分四路,大舉攻明,并親率一支大軍進攻大同。皇帝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聽信王振讓他親征的話,不與大臣們商議,做出親征的決定,并宣布兩天后立即出發。王振只會拍皇帝的馬屁,自入宮以來,在朝廷上下,只要祭起皇帝的法寶,從來都是立馬奏效的,所以他或許是真的認為皇帝是無所不能的,連打皇帝的旗號都能整倒任何政敵,天底下他還怕什么呢?對也先,他應該也打過皇帝的旗號,或許沒有奏效,他才搬請皇帝親自出馬。可能恰恰是王振這樣不學無術的小人對皇帝的盲目崇拜,才最終害了皇帝,害了明朝。
戰爭的起因,可能就是王振造成的,皇帝又片面聽從肇事者王振的話去解決戰爭,才導致戰爭的一發不可收拾。
古戰場
我重新走到公路,前面是老營洼村,一個“營”字就說明這里也與軍隊有著關系。
110國道另一側為煤場,風把黑色的煤塵吹上了天,天也黑乎乎的一團,煤塵落到地上,地上也成了黑色的。
在曠野之上,忽然看到一座紅色的仿古牌坊,五間六柱,中間兩根纏繞金龍,正中字是“明代土木之變遺址”。
牌坊之后,只有一片荒野,一片幾百年前擁擠過數十萬明軍將士的荒野。在這數十萬人中,有屢征沙場、征服安南的蓋世名將,有從容調劑、節縮有方的理財能手,有未雨綢繆、抱傷上言的忠義之士。然而,至高無上的大明天子,卻把指揮權交給了一個無半點陽剛之氣的身邊太監。擁有世界上最先進武器裝備的軍隊,在人數絕對占優的情況下,被無才無德的太監胡亂調遣,如一團無頭蒼蠅般亂跑亂撞,最后,被區區幾萬人的瓦刺擊潰,數十萬明軍將士身葬草野,死于溝壑。
雖然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高喊著“吾為天下誅此賊”錘斃,但當英宗復辟之后,不但不認為自己被俘是拜王振所賜,反而繼續維護“王先生”的聲名,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立了一個彩色泥像,還樹了一塊碑為他立了傳,以致明代太監的禍患越來越重,如憲宗時出現汪直,武宗時出現劉瑾,甚至熹宗時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明朝,終于成為中國歷史上太監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斥為“最大的太監帝國”。
仿古牌坊的背面,寫著“記史訓強國洗辱”,雖然當地沒有對土木之變遺址進行旅游宣傳和商業開發,但我認為三處古跡的布置很有意義:古祠堂和古城垣處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的手書“為人民服務”,古戰場沒有寫“為人民服務”,但強調了“記史訓強國洗辱”。
20世紀初,隨著清帝國的滅亡,太監也隨著帝制一起消逝在歷史的深處。作為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拒絕搞家族制的世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國體,他的治國方略只有五個字“為人民服務”。歷史一再說明,一旦執政者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那么難保類似“土木之變”這樣的歷史悲劇不會一次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