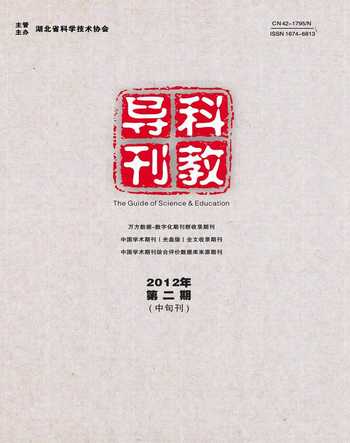“田園”與“反田園”
彭苗
摘 要 一直以來,師陀都被歸入到京派作家的行列,但二者事實上貌合而神離,在師陀“田園詩”的表面下,實則是“反田園詩”的鄉土敘事。
關鍵詞 師陀 京派 田園詩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Pastoral" and "Anti-pastoral"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 Tuo and the Beijing
PENG Mi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Shi Tuo 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the ranks of Beijing writers,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y look the same but actually different, in the appearance of Shi Tuo's "pastoral", in reality it is "anti-pastoral poetry" of native narrative.
Key words Shi Tuo; the Beijing; pastoral
在多數文學史、小說流派史著作的敘述中,作為小說家的師陀都被定位為京派作家,然而,師陀本人生前一直強烈反對自己被劃歸京派。他自己說“在文學上我反對遵從任何流派,我認為一個人如果從事文學工作,他的任務不在能否增長完成一種流派或方法,一種極平常的我相信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而是利用各種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說達成寫作目的。”①這說明師陀本身志在于追求自己的創作風格,而非在主觀意愿上親近京派的田園抒情風格。拋開作家自己的意見不談,研究者們就師陀是否京派問題上各執一詞,分歧始終也未曾斷過,成為師陀研究領域一個奇特的現象,若我們細細考證,這種分歧甚至在師陀的創作初期就有了體現。
師陀頭兩部小說集的出版引出的最早的五篇評論文章,便來自于京派的劉西渭、朱光潛,與左翼的楊剛、汪金丁、王任叔,兩方的評論家均同時看出了師陀作品與己方合與不合之處,并都提出了希望師陀創作向己方靠攏的期待。朱光潛把師陀與沈從文并列,說他們“從事于地方色彩的渲染……這些人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歷史上會留下痕跡的”。②劉西渭贊揚師陀“小說的文章,有一種奇特的風格”③可以看出,京派從藝術風格和創作態度上都表示了對師陀的認同與贊揚。左翼一方則更看重師陀作品中表現的“現實給予不幸者的蹂瞞”及類似“社會問題”④的內容和主題,并提出希望作者能“從素樸的原野,回返到人生的鬧市,將自然的哲學,深入到現實的實踐”,“作個更落實的扛起鋤頭,邁入荒蕪的開辟者”。雙方論者都看出了師陀與本方的同,同時也看到了與本方的異,當然這些評論是僅就師陀前期兩部短篇小說集《谷》和《里門拾記》而言的。抗戰爆發后,師陀進入其創作的高峰期,蟄居上海期間貢獻了短篇小說集《果園城記》,中篇《無望村的館主》,長篇《結婚》、《馬蘭》、《荒原》(未完)等作品,其中鄉土小說占到半數以上,《果園城記》更被認為是“足以使蘆焚自立于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之林”⑤的杰出作品,師陀在這一部短篇集中以哀婉、溫情而又不乏嚴峻的批判的筆觸描繪了一個被美麗的果園包圍著的小城——一個動蕩的大世界中的封閉又逐漸凋落的小世界。也正是因為這部作品散文詩化的風格,鄉土田園的情調,師陀更多的被作為京派作家提起。
但是《果園城記》可以說是師陀鄉土小說中的一個異類,它無論在藝術上或形式上都異于師陀早期的鄉土小說《谷》、《里門拾記》、《落日光》,風格和情調也迥然不同。如果說“里門”世界中的師陀身上滿是諷喻人事丑陋的尖利的刺,那“果園城”中的師陀相對來說則要內斂、沉靜的多。
“百順街”無疑是古老宗法制度下落后、貧困、愚昧的中國封建農村的代表,人們的生活幾乎無一例外地趨于病態和變態:地主大戶主婦畢四奶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千方百計地折磨小妾直至其懷著孩子死去;人們“喜氣洋洋”的“穿起將來的冥衣”去圍觀夜晚死在河里的尸首,做出種種財與色的猜想,冷漠地將這陌生的過客的死當做可聊的話資;本身是封建迷信代表的女巫,不惜“大碗喝酒,整塊吞肉”損耗自己的身體來維持自己在村民們心中神秘和信任,只因為丈夫酗酒兒子病重而不得不以此維持生活,“這樣一來自己先瘋了,然后再把別人弄瘋”;荒涼的小城外,瘋狗追逐啃咬著被當成匪徒殺害的農民們的尸首,而執刀的槍斃手日日殺人以致麻木,砍死了自己“扎丫角時的朋友”⑥……整個“里門”世界灰暗而散發著潰爛的氣息,著力揭示鄉里村落社會種種“生活樣式”的病態和整個鄉土中國“社會生態”的惡化,以致作者絕望地宣告:“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著那廣大的原野”。⑦這確實是師陀內心深處最真誠的吶喊,對故鄉的依戀是每個在外的游子內心深處最深切的渴望,中國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就無時無刻不在尋找“精神返鄉”的旅途上,“離去——歸來——再離去”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經典的情節模式之一。然而不同于沈從文的沉迷于建設“人性的希臘小廟”,師陀清醒的認識到故鄉的落后和丑陋,他并無意去構建一個虛無飄渺的“桃花源”,因此“眷戀”與“批判”糾纏在作者的心中,劉西渭說師陀“把情感給了景色,卻把憎恨給了人物”,這句話用來評判師陀早期的鄉土小說是一點不錯的,師陀早期的小說中充滿了“田園詩”的浪漫風光和“反田園詩”的丑陋人事的對比。
深秋清晨,霧濃重得像煙,一縷一縷從樹梢,從半空中撲下來,成了煙的團,云的團,緩緩在地面上溜,然后再卷上去。逢著這樣天氣是不會有風的,所以便成立了霧的世界。它比牛奶看去還要新鮮,綿綿卷舒著,繞住茅舍的檐角,繞住樹干,滾過村道。《霧的晨》
夕陽落向山崗后面去了,丘陵間已盡入黃昏,荒寂的田莊還浴著殘輝,構成這田莊的是幾座古屋,一帶老柳掩映的殘缺的圍墻,屋后野草叢雜的廢園。莊門前密植著洋槐的林子。林外溶溶流著一條小河;水面反映著云光,油似的微起渦渾。從田莊通過樹林,又跨上河上的小橋,有一條路。這路年來車馬絕跡,很少行人,因之漸為野草侵領,其間開著無人聞問的花朵,并散布著羊糞。晚鴉冶游了一天,悄悄飛過天空,一只兩只歸林來了;那歇腳枝頭拍著翅的懶倦景況,使人聯想到是在打寂寞的呵欠。《落日光》
這種優美的景色描寫經常出現在師陀的早期文本中,然而置于其中的卻并不是“翠翠”與“儺送”們充滿了人性美、人情美的故事,而是真正的人間慘劇。霧的晨光里,一條人性化的狗在計算著如何吃那個意外摔死的人的肉,而村人們在圍觀著“九七”的尸首,卻不是為他的死而傷心,而是在心里暗暗埋怨九七借米借的不是時候,倘若遲一天借,自己的米也吃完了,這樣也就不會再為沒有借給他半瓢米而抱憾了。詩意的落日光里,遠離故鄉三十年的“吃閑飯的”回到家中,希望能找回昔日的回憶,卻被害怕他來分家財的侄子趕出家門,最后死在了斜谷的亂石間。
這種景物與人事的強烈的對比在“果園城”中似乎趨向于緩和,這個封閉、停滯的小城被美麗的果園包圍著:
這城里最多的還是果園,假如你恰恰在秋天來到這座城里,你很遠很遠就聞到那種香氣。累累的果實映了肥厚的綠油油的葉子,耀眼的像無數小小的粉臉,向陽的一部分看起來比擦了胭脂還要嬌艷。《果園城》
在這個小城里,有可愛、充滿生氣的水鬼“阿嚏”,有既尊貴又從容的郵差先生,有給家家戶戶送去燈火的賣油郎。回到果園城的馬叔敖悠悠地走過這小城的每個角落,緩緩講述著這個小城古老的過去和當前的現實。這么看來,這部系列小說確實沾染了京派的風格,“果園城”仿佛是另一個山美、水美、人美的“邊城”。然而,“京派作家喜好古樸的農村,童年的天真甚而至于對原始生命力的贊頌”,“京派作家以表現人性美、人情美為創作極致”。⑧也就是說,京派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對美好人性的贊揚,對完美人格的謳歌,在現代文明將人的原始生命力和鄉村的純凈毀壞之前,人性本是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健康狀態。可是在果園城中,時間似乎是停滯的,“在任何一條街岸上”都看見“狗正臥著打務,它們是決不會叫喚的,即使用腳去踢也不”,“在每家人家門口坐著女人,頭發用刨花水抿得光光亮亮,梳成圓髻。她們正親密的同自己的鄰人談話。現代文明似乎不曾給小城帶來任何改變,“屋子里的陳設仍舊跟好幾年前一樣,迎面仍然供著熏黑了的觀音神象,兩邊掛著的仍舊是當初徐大爺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所有的東西幾乎全不曾變動,全在老地方。”不知幾百年或幾千年前就矗立在那里的塔,“似乎永遠不會倒”,⑨這種停滯和不變似乎是果園城的常態,人們也似乎漸漸安于這種狀態,盡管有短暫的反抗,最終卻歸于沉寂。面對這令人窒息的生命的循環往復的怪圈,作者感嘆“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則,一種散漫的單調生活使人慢慢變成懶散,人也漸漸習慣于成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曾經做過如下描述:“人民生活在同一的小天地里,在時間上,每一代的人在同一的周期中生老病死……”這種“小國寡民”式的安寧固然美麗,但是在對民族存亡和時代的進步有著強烈的關注的知識分子面前,這樣的安寧同樣也代表著一種永墮輪回的不思進取和坐以待斃的盲目的生存狀態。作者非但沒有對這種無意義的消磨生命的人性進行贊美和謳歌,反而進行了沉痛的批判。這種對國民懶散常態的痛恨和批判與師陀前期小說中對故鄉鄉民們人性常態的揭露是多么的相似:“在那里,永遠計算著小錢度日,被一條無形的鎖鏈糾纏住,人是苦惱的。要發泄化不開的積郁,于是互相毆打,父與子,夫與妻,同兄弟,同鄰舍,同不相干的人;腦袋流了血,掩創口上一把煙絲:這是我的家鄉。”⑩盡管前期小說中更尖銳,但《果園城記》這種將國民人性的墮落與生命的麻木化入到千年如一日的日常化的生活中,而非前期小說中用略帶傳奇色彩的故事來表現的手法,更有一種歷史的沉重感和對國人這種生存狀態的沉痛的悲哀。
因此,盡管《果園城記》與師陀前期小說藝術上和風格上差異甚大,卻并非完全的改弦更張,其深層意義上對國民人性的墮落和麻木的沉痛批判是一樣的。而正是這種對日常人性中的黑暗與墮落的批判將師陀與京派作家區別開來,他無意于建構一個天人合一的桃花源,亦不認為有完美的“人性的希臘小廟”可以用來供奉,在他的文本世界中,人性從來就是丑陋而非充滿了原始生命力的健康狀態。陰慘,痛苦,而且是永無止境的痛苦,絕望,荒涼,而且是永沒有人住居過的荒涼,孤獨、不安、驚懼,根本沒有獲得“從容”的可能性,也根本沒有“美”的可能性。他與“京派”遠不是在同一個表現層面上,二者就算在表層上有某種程度的相似,其內里卻是截然不同的。
注釋
① 師陀.《馬蘭》成書后錄.文藝雜志,1943-03-15.
② 朱光潛.現代中國文學.朱光潛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③ 李健吾.讀《里門抬記》.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④ 金丁.光明.1937.3(5).
⑤ 錢理群.試論蘆焚的“果園城”世界.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1).
⑥ 師陀.里門拾記.師陀全集.劉增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⑦ 師陀.巨人.師陀全集.劉增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⑧ 許道明.京派文學的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
⑨ 師陀.果園城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⑩ 師陀.巨人.師陀全集.劉增杰,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