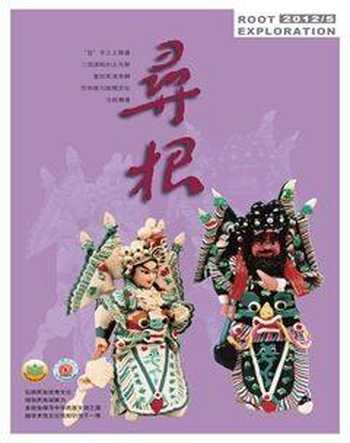子夏傳授《春秋》考
高培華
孔子據(jù)魯國史記編纂《春秋》,不僅是編修了中國第一部編年史,簡(jiǎn)略記述了春秋時(shí)期242年的歷史,還常常以一字寓褒貶,借以表達(dá)其王道政治觀點(diǎn),以謹(jǐn)嚴(yán)的措詞懲惡揚(yáng)善,所謂“微言大義”。故《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有文獻(xiàn)明確記載,“《春秋》三傳”之《公羊傳》《谷梁傳》都傳自子夏;至于《左傳》,近現(xiàn)代學(xué)界有謂“子夏作”,有謂成書于“子夏門下一再傳弟子”,可見子夏是《春秋》最主要的傳人。
子夏深厚的歷史文獻(xiàn)修養(yǎng)
子夏在孔門求學(xué)的后期,被孔子列為“四科十哲”中的“文學(xué)”高徒。(《論語·先進(jìn)》)先秦所謂“文學(xué)”,大致相當(dāng)于今之古文獻(xiàn)學(xué)。作為“文學(xué)”高徒,子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孔子的助教。一是協(xié)助孔子為其他弟子解疑釋惑。如《論語·顏淵》:司馬牛“問君子”,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但是司馬牛想到“人皆有兄弟,我獨(dú)亡”,又不免憂從中來。子夏先用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話安慰他,接著勸導(dǎo)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意謂君子加強(qiáng)修養(yǎng),則足以改變“無兄弟”的不幸,從而否定了人在命運(yùn)劣勢(shì)下無可奈何的消極心態(tài)。這無疑是對(duì)孔子“存天命而盡人事”之積極天命觀的靈活運(yùn)用。又如《論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dá)。子曰:“舉直錯(cuò)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xiāng)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cuò)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yuǎn)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yuǎn)矣。”
孔子所謂“舉直錯(cuò)諸枉”,是其“舉賢才”思想的一種表述;但由于說得深?yuàn)W簡(jiǎn)潔,樊遲不理解,又來問子夏。子夏一聽,便深刻領(lǐng)會(huì)了孔子的話,并運(yùn)用自己的古文獻(xiàn)學(xué)之長(zhǎng),舉出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的歷史故事加以說明,在補(bǔ)充說明孔子言論之際提出“選于眾”,即在眾多待舉對(duì)象中慎重選擇,只有選中了真正的賢才,才會(huì)有“舉直錯(cuò)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這就在闡發(fā)孔子思想時(shí)有所發(fā)揮,為孔子“舉賢才”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質(zhì)。
二是在孔子晚年整理《詩》《書》《禮》《樂》等文獻(xiàn)和依據(jù)魯史作《春秋》時(shí),發(fā)揮其“文學(xué)”之長(zhǎng),做了不少協(xié)助工作。《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作《春秋》在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之后,又記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于此單單提到子夏,可見他是做輔助性工作最多的弟子,至少說明他當(dāng)時(shí)在孔子身邊。不然的話,能否“贊一辭”就無從談起。徐彥《春秋公羊傳疏》引閔因《序》日:“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jīng)立。”《春秋說題辭》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漢代緯書雖有神化儒家經(jīng)典的缺點(diǎn),但也保存了一些有參考價(jià)值的史料。將此與《史記》的記述相參,可知子夏于哀公十四年確實(shí)在協(xié)助孔子作《春秋》:先是受孔子所使赴洛邑“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爾后定居曲阜協(xié)助孔子并領(lǐng)受其《春秋》真?zhèn)鳌?/p>
子夏等人求周《史記》,應(yīng)當(dāng)是從魯國出發(fā),途經(jīng)衛(wèi)、晉到達(dá)成周。《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之晉,過衛(wèi)”遇“讀史記者”,糾正“亥豕之訛”,就是此行途中發(fā)生的事:
子夏之晉,過衛(wèi)。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因?yàn)樽酉牡却诵心康氖恰扒笾堋妒酚洝贰币詡淇鬃幼鳌洞呵铩返氖妨希诵薪Y(jié)果是“得百二十國寶書”,一路上下功夫廣為搜求亦可想而知。既然要搜求各國史料,途中所接觸的人、所留心的事,自然也都在“史記”方面。知此,就很容易理解子夏“過衛(wèi)”為什么會(huì)對(duì)“讀史記者”特別關(guān)注,聽到其讀“晉師三豕涉河”感到不通之后,就憑借自己的歷史和古文字功底推斷“三豕”為“己亥”之訛,并在晉國得到了證實(shí),于是留下了子夏糾正“亥豕之訛”的千古佳話。
子夏傳授《春秋》的巨大成就
關(guān)于子夏傳《春秋》,先秦文獻(xiàn)即有記述。如《韓非子·外儲(chǔ)說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夏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xì)⒕⒆託⒏刚撸允當(dāng)?shù)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子夏日:“善持勢(shì)者,蚤絕奸之萌。”
這在西漢人著作中也有反映。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衛(wèi)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xué)《春秋》。不學(xué)《春秋》,則無以見前后旁側(cè)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于位,一朝至爾。茍能行《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又如劉向《說苑·復(fù)恩》: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據(jù)上引材料可知,子夏傳授《春秋》,特別重視從春秋史事中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側(cè)重于弟子政治才干增長(zhǎng)提高以及提醒“有國有家者”學(xué)習(xí)和借鑒歷史經(jīng)驗(yàn),以養(yǎng)成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治國、齊家本領(lǐng)。故子夏門下能夠培養(yǎng)出魏文侯、李悝等杰出的政事之儒。
子夏門下著名的傳經(jīng)之儒,有公羊高、谷梁赤、曾申等人。
公羊高,復(fù)姓公羊,名高,受《春秋》于子夏,又傳于后人,著重講授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到西漢,形成了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重要典籍《春秋公羊傳》,設(shè)博士,立于學(xué)官。《漢書·藝文志》著錄“《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疏引戴宏《公羊傳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shí),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谷梁赤,復(fù)姓谷梁,名赤,受子夏《春秋》,又傳授于后人。其后世子孫、弟子根據(jù)其口述內(nèi)容,在戰(zhàn)國后期著于竹帛,成《春秋谷梁傳》,也是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重要經(jīng)典。《漢書·藝文志》著錄“《谷梁傳》十一卷”,班固自注:“谷梁子,魯人。”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谷梁氏,谷梁赤,子夏門人。”桓譚《新論》、蔡邕《正交》也說受經(jīng)于子夏的谷梁子“名赤”;唐楊士勛《春秋谷梁傳注疏》卻說:“谷梁子名淑,字元始,受經(jīng)于子夏,為經(jīng)作傳,以授茍卿。”《七錄》亦云“名俶”;《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谷梁子,名喜”。清經(jīng)學(xué)史家皮錫瑞推測(cè):谷梁子的多個(gè)名字,可能并非一人,而是指不同時(shí)代的傳經(jīng)者。
子夏為《春秋》的主要傳人,自漢代以來沒有爭(zhēng)議;有懷疑的只是一些文獻(xiàn)所記述子夏以后的傳經(jīng)線索。故本文還需要就漢儒所記子夏傳經(jīng)的線索,做一點(diǎn)考證祛疑的工作。
前引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疏引之戴宏《公羊傳序》將傳承已講得非常清晰。戴宏為漢安帝、順帝時(shí)人,與公羊壽及其弟子胡毋子都雖不同時(shí),但畢竟是漢代人追述漢代的著述,可信度應(yīng)當(dāng)比后代所記高一些。古今學(xué)者提出懷疑,是因?yàn)榻倌曛挥形宕鷤魅耍来疵膺^于稀少。這懷疑不能說沒有道理,卻不足以否定漢代成說。徐復(fù)觀先生講:“戴宏所說的,由子夏(卜商)下來的五代傳承,只是出于因《公羊》《左傳》在東漢初的互相爭(zhēng)勝,《公羊》家為提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來的,以見其直接出于孔門的嫡系單傳。”(徐復(fù)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這未免低估了漢儒的學(xué)術(shù)品德,也有后世對(duì)漢人追述之詞的誤解。追述各家淵源,自然需要一代代溯上去、一代代說下來,不必是“嫡系單傳”之意。《公羊傳》中就記述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等外姓經(jīng)師,顯示出并非自家一線單傳。至于“世代過稀”之成因,應(yīng)當(dāng)在于年代久遠(yuǎn)且系師師口傳,難免有所遺漏。但也正因?yàn)橛写嗣黠@破綻,得知其并非刻意編造,不然的話是不難“私造”得比較完善一些的。
唐代楊士勛《春秋谷梁傳注疏》謂谷梁子“受經(jīng)于子夏,為經(jīng)作傳以授茍卿”。以人物時(shí)代考論:戰(zhàn)國初期“受經(jīng)于子夏”的“谷梁子”,是絕不可能“為經(jīng)作傳以授茍卿”的;“授茍卿”的“谷梁子”,只能是戰(zhàn)國后期略早于荀子的谷梁氏后人。這樣更為粗略的經(jīng)師傳授記錄,顯然不能作過于拘泥的理解,只能遵照應(yīng)劭之說:認(rèn)定作為“子夏門人”的谷梁子名赤;而“為經(jīng)作傳,以授茍卿”的谷梁子,則是谷梁赤的后人。
另外,《春秋左氏傳》淵源于子夏,也是一個(gè)可能性比較大的推測(cè)。因?yàn)椤蹲髠鳌酚洉x國歷史之詳,對(duì)于魏氏先祖的不無過分的贊譽(yù),都讓人不能不想到子夏的國籍及其與魏文侯的實(shí)際關(guān)系。因此,近代劉師培參照汪中考證,列出《孔子傳經(jīng)表》,認(rèn)為《春秋》三傳的傳授,均出自子夏一派。現(xiàn)代學(xué)者徐中舒則進(jìn)一步推論曰:《左傳》“可能就是在子夏門下編寫成書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的一再傳弟子”。(徐中舒:《(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歷史教學(xué)》,1962年第11期)孔祥驊先生認(rèn)為:“《左傳》中‘君子曰的贊語,很可能是子夏搞的。”進(jìn)而提出:“子夏氏一派不但積極參與了魏文侯改革,也進(jìn)行了一次相當(dāng)大規(guī)模的文化整理,在重新撰寫《左傳》的過程中,作為子夏氏的魏派儒家們難免不流露出該派對(duì)于魏國的贊頌,這也正好揭示《左傳》一書成書的時(shí)代。大概可以這么說,《春秋》三傳正是在這個(gè)時(shí)期先后由子夏一派的弟子們分別搞出來的。”(孔祥驊:《子夏與(春秋>的傳授》,《管子學(xué)刊》,1997年第2期)應(yīng)該承認(rèn),這些說法是頗有道理的。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規(guī)劃項(xiàng)目《卜子夏考論》階段成果,編號(hào):2011BLS002)
作者單位:河南省教育科學(xu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