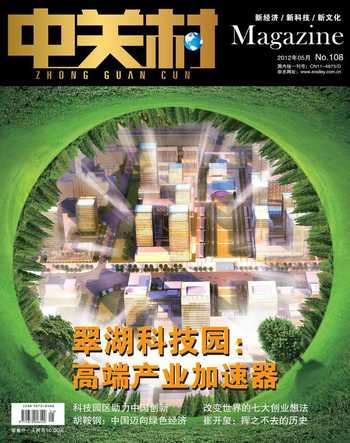“天真者”的啟示
張越


天真者的藝術(shù)以一種共鳴的和聲向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以及備受爭議的中國教育提出了質(zhì)問。
2012年4月2日,北京中間美術(shù)館的中庭廣場中坐滿了孩子、家長和老師們。這一天是第五個世界自閉癥日,同時也迎來了第五屆“愛在藍天下”繪畫作品展。
雖然從醫(yī)學上來講,自閉癥患者存在社會交往障礙和交流障礙,或有些怪異的習慣,但表現(xiàn)在藝術(shù)作品上,他們又都是“正常的”。在這些天真者的畫筆下,你看到的是一個沒有被腐蝕過的世界,你會被那種純粹的力量所打動,仿佛剎那間被拉回到污濁的彼岸,這正源于他們不諳世故、不染塵煙的心靈。這種心靈的洗滌,早已超越了慈善的范疇,而是以一種共鳴的和聲向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以及備受爭議的中國教育提出了質(zhì)問。
畫展發(fā)起人之一、清華大學美術(shù)學院教授李木說,面對當今藝術(shù)以及藝術(shù)教育所出現(xiàn)的尷尬局面,我們幾乎沒有可能自省和自救,而自閉癥孩子及其作品的出現(xiàn)卻給予了教育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和切入點,讓大家在這些孩子們的身上和作品上看到一種奇跡——他們沒有接受過教育,他們不遵循固有的和相同的價值觀,他們沒有統(tǒng)一的審美判斷,卻能創(chuàng)作出這樣的作品。而他們所擁有的恰恰是健康人漸漸丟失的,這近乎是一種對中國教育缺口的折射,對家長、老師甚至整個中國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質(zhì)問。
更值得人們反思的是,原本自閉癥兒童及其作品是被人“評價”的,而今天,他們的作品反而成了一個是非評價的參照:能夠被這樣的作品觸動,則可能離一個真誠的藝術(shù)狀態(tài)很近;如果連這些藝術(shù)都無法打動你的心靈,你也將不太可能有新的東西被呼喚出來。
在過去的四年中,“天真者的藝術(shù)”吸引了社會各界人士關(guān)注。今天,在中間美術(shù)館里,記者依舊尋找到了眾多響亮的名字:鄭淵潔、陳丹青、李木、張進……
鄭淵潔:朽木可雕
在畫展的開幕式中,“童話大王”鄭淵潔講了這樣一段故事。
“在現(xiàn)實生活中,眼鏡能夠矯正視力,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任何醫(yī)生能夠通過任何方法治療看走眼。令我們沮喪的是,我們的眼睛經(jīng)常看走眼,給我們制造許多遺憾,甚至錯失良機,貽誤他人終生。”
“‘朽木不可雕這句貌似千古經(jīng)典的名言不知導致多少人看走眼,特別是成年人看走眼未成年人。”
“我的弟弟鄭毅潔有‘信鴿大王之稱。他有一只瘸腿信鴿,這只鴿子除了血統(tǒng)欠佳外,還有一只腿殘疾。它不能將瘸腿收回,因此它在飛行時無法保持身體平衡,只能側(cè)身飛行。朋友對鄭毅潔說,你的閃電鴿舍如此宏偉,卻有這樣一只瘸鴿,影響形象,放棄它吧。鄭毅潔認為朋友言之有理,決定淘汰瘸鴿。但養(yǎng)鴿子的人是不忍心殺鴿吃肉的,于是他想到了一個拋棄瘸鴿的方式,就是送它去參加遠程信鴿競翔比賽。那次比賽他一共送了20只信鴿參賽,除了瘸鴿,其余19只都是血統(tǒng)精良身強力壯的精英。令鄭毅潔大吃一驚的是,瘸鴿最后贏得了這次比賽的冠軍。現(xiàn)在,這只‘影響形象的瘸鴿成了‘鎮(zhèn)店之寶,還出現(xiàn)在央視的屏幕上,聲名大振。”
“這個世界上壓根就沒有朽木,朽的是我們的眼睛。到了糾正‘朽木不可雕的時候了,我且將其改成‘朽眼不可雕。最可悲的‘朽眼就是父母在看自己的親人,特別是看自己孩子時走眼,還有老師在看自己的學生時走眼,拱手把諾貝爾獎得主讓給外國的孩子。”
“今天,我要恭喜這些天才小畫家們的父母,因為能生出天才的父母特別少,希望所有的父母和老師都能呵護自己的孩子(學生),支持他們、理解他們,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助力孩子的成功。”
陳丹青:“另類”是最珍貴的
“自閉癥孩子和自閉癥孩子的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這些孩子們的畫,卻突出地反映出了中國在教育中出現(xiàn)的問題。”
“我回國已經(jīng)12年了,我回想自己剛回來的時候,似乎還沒有這么糟糕。今天的學校,一大堆的規(guī)范和教條,讓原本正常的孩子都產(chǎn)生‘障礙了。他們不敢說真話,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表達的對不對。我每一次到大學講演,面對的那些年輕人像是復制品一樣,一張張相似的青春的臉,他們的個性的棱角幾乎被磨圓了。”
“現(xiàn)在中國的教育像是進入了一個殘酷的管理狀態(tài)。孩子們從進幼兒園開始,直到大學,像是進入了一個障礙過程,而且是越來越系統(tǒng)的障礙過程。而自閉癥孩子恰好因為自己生病而逃離了這個障礙過程。教育原本是一件無限復雜的事情,而我們現(xiàn)在教育的頑疾恰恰是把復雜的事情變得很簡單(應將因材施教落到實處)。”
“所以,如今‘個性和‘另類是中國最珍貴的東西,老師和家長生怕自己的孩子和別人不一樣,中國的絕望就在這兒。縱觀世界藝術(shù)發(fā)展史,創(chuàng)造奇跡的恰恰都是些‘瘋子。比如,打開現(xiàn)代藝術(shù)突破口的是三個有問題的人:塞尚、梵高和高更。雖然這三個人的問題不一樣,但這三個人中卻有兩個人都有嚴重的‘神經(jīng)病傾向。在文學界也出現(xiàn)過類似的例子。在現(xiàn)代文學中四個最重要的現(xiàn)代詩人全都是同性戀者,‘同性戀雖然不是病,但也區(qū)別于大眾。同樣,在音樂界里,世界聞名的莫扎特也是一個在生活上問題百出的人,他不會規(guī)范時間、不會理財、不會顧家,甚至管理不好自己的語言,可是他在藝術(shù)上卻神奇透頂,沒有他做不到的事……這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但這個話題有時候在藝術(shù)內(nèi),有時候也可以在社會層面。”
“這些自閉癥的孩子正因為沒有被任何人改變才創(chuàng)作出了今天這樣的作品,這是否會給當今的教育一個有力的反擊呢?”
李木:追溯真正的藝術(shù)
“前不久,我剛剛結(jié)束今年的招生工作。讓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藝考時兩萬個學生畫的是一樣的,那才叫真正的‘不正常。我們的招生制度,因為要用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去選拔人,與其說是選拔人,不如說是淘汰。現(xiàn)在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了,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里才能看到不正常人畫的正常的畫。而這些‘天真的藝術(shù)家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非常有幸地躲開了中國的藝考制度。”
“當然,在教育中把握共性與個性的平衡是非常難的,但依然要堅持。而現(xiàn)在教育卻是非常極端的,講究共性、統(tǒng)一,強求一律,這讓教育,尤其是藝術(shù)教育出現(xiàn)了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
“今天的藝術(shù)教育,鼓勵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功力傾向,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要有目的。比如說一定要獲獎,一定要被認可,甚至一定要讓人們看懂。多數(shù)人不愿意冒風險,不愿意承受壓力。本來藝術(shù)教育應該有的東西,卻因為一些功利性的因素而漸漸失去,變成一味地迎合大眾。我們看不到鋌而走險的真正藝術(shù)家,也看不到探索實驗和嘗試,更看不到藝術(shù)的個性。”
“藝術(shù)教育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兩回事兒,甚至他們的做法和訴求都是矛盾的。但我們國家由于歷史上的很多原因造成兩者混為一談。所以很多藝術(shù)教育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出現(xiàn)的問題,都是源于這個地方,即教育和藝術(shù)、教師和藝術(shù)家的職責身份不分,導致在市場上賣的,在課堂上畫的和教學上倡導的相一致,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
“但是今天突然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情形,一幫孩子由于他們的疾病,導致了他們真的需要去畫畫,或者只能去畫畫。這些孩子提醒了一下那些還有感受和良知的藝術(shù)家,讓他們重新去反思藝術(shù)最開始的狀態(tài),讓他們回想其繪畫中最可貴的因素是什么。”
“最開始籌辦這個畫展的時候,我并沒有指望自閉癥的孩子中能出現(xiàn)幾個偉大的藝術(shù)家,我只是希望這樣的展覽能夠給人一些觸動,讓藝術(shù)家,尤其是年輕的藝術(shù)家能夠通過這次展覽獲得一些心靈上的啟示,幫助他們最終走向成功。”
張進:尋找“陽光教育”
“來到這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現(xiàn)在中國教育部在提倡的陽光教育。但是作為一線教師,我深知孩子們沒有體會到陽光。而今天,我卻看到這里面充滿了陽光。”
“我在中學里教了30多年書,一直教學生畫畫。我曾編了一本書,叫《中學生的現(xiàn)實主義》,這本書源于一次主題為‘我與面具,表現(xiàn)真實與虛偽的課堂作業(yè),主要讓學生通過繪畫表現(xiàn)他們內(nèi)心的一種心聲。因為現(xiàn)在許多學生在家長和老師面前變得很虛偽,不說真話,所以我就讓學生們通過畫畫表現(xiàn)一個真實的自己。有一個男生畫完畫之后問我:‘老師,我覺得光畫畫表現(xiàn)得不夠充分,能不能再寫點文字?我說可以,他又說:‘老師,可以罵人嗎?我說,筆出心意,詞發(fā)心聲,這是你的事兒。于是他就寫了一段話,最后一句寫了‘中國教育XXXX,這一句話寫完了以后,我看了非常震驚,我說我要給你們印一本書。然后我就把這些畫稿拿給校長看,校長一看也說好,但是校長翻到這篇作業(yè)的時候,就突然不同意出了。我說,你可以對不起240個學生,但我不能對不起我的學生,于是我就拿出自己的工資出了這本書。當書印刷完畢,發(fā)給同學們的時候,這個學生特敏感,馬上就翻到那頁,看后說:‘老師,你太偉大了!因為他發(fā)現(xiàn)那句最要緊的話沒刪。后來,這句話被年級評為最經(jīng)典的語言。”
“從這些孩子的內(nèi)心活動和行為中,我就看出了當前中國的教育所出現(xiàn)的問題。這些正常的孩子的內(nèi)心在經(jīng)受一種煎熬,而相比之下,這些自閉癥的孩子反而在家長的呵護下,在更多人的關(guān)愛下顯得更加幸福。”
手記:
持續(xù)五年,“愛在藍天下”繪畫作品展讓自閉癥兒童受到社會各界關(guān)注的同時,也讓自閉癥從一個簡單的醫(yī)學范疇逐漸向社會范疇擴散。
今天,這個直到70年前才被世界醫(yī)學界認定的群體,正在不斷增多。據(jù)最新統(tǒng)計,每一萬人中,就有六十至一百二十人患有自閉癥,目前地球上的自閉癥患者已超過6700萬,甚至超過了艾滋病、癌癥和糖尿病患者人數(shù)的總和。
當我們從這些自閉癥兒童身上收獲思考的時候,卻看到這些天真者們的家長的臉上莫展的愁云。因為這些孩子在社會人際互動方面存在“質(zhì)”的缺陷,并且極度孤僻,給他們未來的獨立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李木教授說,目前能夠想到的,相對比較現(xiàn)實地解決自閉癥患者生存問題的方式,就是自閉癥孩子的家長能夠盡可能地健康長壽。倘若父母能夠活到八九十歲,那么孩子也就五六十歲了,他的一生也基本是完整的。
未來,通過全社會的努力,自閉癥患者一定會有個完滿的人生軌跡。
在這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所幸,有天真者和天真者的藝術(shù)。“孤獨”從來都是偉大藝術(shù)家的重要特質(zhì),他們在前往自己人生彼岸的路途中,也提醒我們還可以回到原點,找回創(chuàng)造力的能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