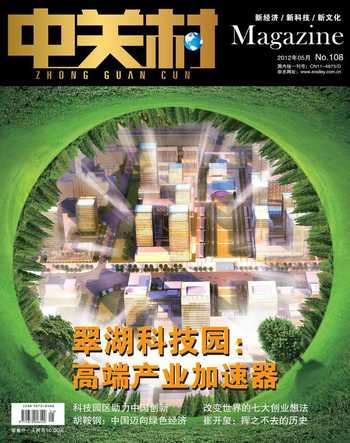用法律來(lái)遏制學(xué)術(shù)腐敗如何?
田方
調(diào)查、處理學(xué)術(shù)腐敗,不能只靠科學(xué)界和科學(xué)家本身的自律,必須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瑞典、美國(guó)、德國(guó)等都對(duì)學(xué)術(shù)腐敗行為實(shí)行刑罰的處罰。如德國(guó)處理學(xué)術(shù)腐敗就主要依靠的是法治。
近日,廣東省紀(jì)委召開(kāi)新聞發(fā)布會(huì),通報(bào)省紀(jì)檢監(jiān)察機(jī)關(guān)近兩年查處的一批典型案件。中國(guó)青年報(bào)記者赫然發(fā)現(xiàn),此前曾因涉嫌抄襲被廣泛關(guān)注的廣州體育學(xué)院原院長(zhǎng)許永剛,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銷(xiāo)黨內(nèi)職務(wù)、行政撤職處分,調(diào)離廣州體育學(xué)院。(4月18日《中國(guó)青年報(bào)》)
教育家梅貽琦說(shuō):“大學(xué)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實(shí)踐證明,“大師之大”是大學(xué)興盛的根本。而學(xué)術(shù)自由又是大師們發(fā)揮能力的基本保障,大學(xué)自治則是實(shí)現(xiàn)學(xué)術(shù)自由的關(guān)鍵。誠(chéng)如牛津大學(xué)第一副校長(zhǎng)麥克米倫所言:“學(xué)術(shù)自由是大學(xué)的靈魂,是大學(xué)得以生存的基礎(chǔ)”。但近年來(lái),我國(guó)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發(fā)生了頗多的“逸聞趣事”:從上海交大“漢芯”造假,到院士、博(碩)導(dǎo)抄襲論文,甚至有人進(jìn)入國(guó)外學(xué)術(shù)刊物的“黑名單”。其實(shí),進(jìn)入“黑名單”也無(wú)妨。正如《左傳》所言:“人非圣賢,孰能無(wú)過(guò)?過(guò)而能改,善莫大焉!”但有些人被人揪住了“小辮子”,還死不悔改。說(shuō)什么既“沒(méi)有一稿多投”,“也不存在因?yàn)槌u而被禁發(fā)論文的事實(shí),是有人在惡意污蔑”。
其實(shí),回溯中國(guó)傳統(tǒng),為學(xué)術(shù)而學(xué)術(shù)的求真精神并不多見(jiàn)。讀書(shū)是為了致仕,治學(xué)是為了治國(guó)。很多“學(xué)術(shù)名人”年輕的時(shí)候才華橫溢,但因身份的“嬗變”使其與學(xué)問(wèn)漸行漸遠(yuǎn),雖各種論文、專(zhuān)著和課題越來(lái)越多,卻背上“剽竊”的標(biāo)簽。用云南大學(xué)教授金子強(qiáng)的話說(shuō),“名師講課是一流的,有實(shí)才也有口才,表達(dá)有感染力,而科研成果是工匠式的。脫離教學(xué)的科研場(chǎng)所不是學(xué)校而是研究所,脫離教學(xué)的科研人員不是大學(xué)教授而是研究員……教授‘一大撥,‘名師有多少。很多人有資格當(dāng)教授,卻因‘科研成果不夠‘評(píng)不上。有人雖是教授,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兒。”
俗話說(shuō):“透過(guò)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學(xué)術(shù)腐敗滋生了學(xué)術(shù)泡沫,像毒瘤一樣將學(xué)術(shù)研究引入歧途,阻礙了整個(gè)科學(xué)和社會(huì)的進(jìn)步。筆者以為,危害社會(huì)的許多行為都被認(rèn)定為是犯罪,學(xué)術(shù)腐敗豈能例外。多年前,韓國(guó)首爾地方檢察廳就以欺詐罪、挪用公款罪、違反《生命倫理法》的罪名起訴肝細(xì)胞科學(xué)家、首爾大學(xué)教授黃禹錫以及其幾名重要助手干細(xì)胞造假。韓國(guó)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審理認(rèn)為黃禹錫在美國(guó)《科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的有關(guān)人體干細(xì)胞的研究論文部分造假事實(shí)成立。但考慮到黃禹錫本人在科研領(lǐng)域的貢獻(xiàn)等幾方面因素,遂以侵吞政府研究經(jīng)費(fèi)和非法買(mǎi)賣(mài)卵子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期3年執(zhí)行。其科研小組的數(shù)名成員也被判處緩刑或者處以罰金。
溫家寶總理說(shuō):“一些大學(xué)功利化,什么都和錢(qián)掛鉤。這是個(gè)要命的問(wèn)題。”筆者以為,學(xué)術(shù)腐敗最終都糾結(jié)于利益,或騙取經(jīng)費(fèi)、或謀求職務(wù)職稱(chēng)、或謀求學(xué)術(shù)頭銜……所以,在刑法立法中設(shè)立“學(xué)術(shù)欺詐罪”很有必要。調(diào)查、處理學(xué)術(shù)腐敗,不能只靠科學(xué)界和科學(xué)家本身的自律,必須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瑞典、美國(guó)、德國(guó)等都對(duì)學(xué)術(shù)腐敗行為實(shí)行刑罰的處罰。如德國(guó)處理學(xué)術(shù)腐敗就主要依靠的是法治。如果學(xué)術(shù)腐敗被“查實(shí)”,不但會(huì)受到各學(xué)術(shù)部門(mén)的紀(jì)律處分,還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處理“科研中的錯(cuò)誤行為(學(xué)術(shù)腐敗)”的相關(guān)司法條文不僅涉及到民法,情節(jié)嚴(yán)重的還要?jiǎng)佑眯谭āT诘聡?guó)人的眼里,“學(xué)術(shù)腐敗不僅屬于道德范疇,因其發(fā)生領(lǐng)域的特殊性,可能與許多人、甚至整個(gè)社會(huì)的利益相關(guān),必須以法律手段嚴(yán)加懲處”。即使在許多國(guó)家只被認(rèn)為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一稿多投現(xiàn)象,在德國(guó)也被認(rèn)為是學(xué)術(shù)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