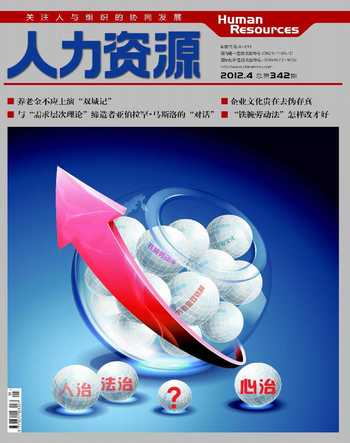出色的領導者是一位“船長”



管理理論之林中,唯獨“需求層次理論”讓我激動,至今迷戀不止。它那人本主義的關懷,溫暖如春,激勵前行。因此,選擇在這樣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里,與仰慕已久的大師進行“對話”,在享受的同時,獲得的是信仰:人類是美好的,前程似錦。
人們必須對自己的命運、
對自己的前途做出回應
康瞧:你的智商高達195,其他測試也取得了在當時是有史以來的第二個高分。你為此也很自豪。可是,你是猶太人,受到反猶太人傾向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時間郁郁不得志。你的家人、朋友都勸你改個名字,不要叫亞伯拉罕·馬斯洛了,但是,你最后沒有改。
馬斯洛:我當時讀了路德維格·劉易遜的《內(nèi)在之島》一書,他讓我改變了主意,我不再夢想改變自己是猶太人的事實。既然我生來就是一個猶太人,我就做一個猶太人。如果他們不再喜歡它,我就把它塞進他們的喉嚨里去……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康瞧:那個時候,你的“安全需求”還是一個問題。你在35歲的時候,提出了“人類動機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在于人類的需求層次,而需求層次的核心在于,已經(jīng)滿足的需要不再驅動我們的行為。形象一點的說法,一個饑餓的人為了活命也許不顧自尊,但是,一旦他吃飽穿暖,他就可能會追求更高級的目標,而最高的目標就是自我實現(xiàn)——你能形象一點談談自我實現(xiàn)嗎?
馬斯洛:一個音樂家必須作曲,一個畫家必須畫畫,詩人要寫作,否則,他就無法與自我保持最后的統(tǒng)一。一個人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他就一定會變成什么樣的人……這個需要,我們可以稱之為自我實現(xiàn)……它是指人希望自我發(fā)揮和自我完善的需要,也就是他想成為他有可能成為的一種人:成為一個人有能力成為的任何一種人的內(nèi)在傾向。
康瞧:這話前面易于理解,后面可就需要慢慢咀嚼體味了。
馬斯洛:這種傾向可以說是一個人越來越成為獨特的那個人,滿足他所能滿足的一切欲望。自我實現(xiàn)的特質(zhì)簡單來說,具有平靜、知足、鎮(zhèn)定、潛力……得到充分發(fā)揮,具有很強的創(chuàng)造力,以及在人際關系方面的成功,等等。
康瞧:你說過“自我實現(xiàn)是艱苦的工作”,不錯,大多數(shù)的人是不怕艱苦的,可是,如何在工作中找到快樂?
馬斯洛:找到快樂并不難。不過,我喜歡自己這樣的一個措辭: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會做得好。
康瞧:值得做的才是至關重要的,快樂也源于此吧!
馬斯洛:尋求各種拯救總是個人拯救的錯誤方向。唯一真正的道路就是艱苦的勞動之路,就是對做好一件值得去做的工作的全心關注,也是命運召喚你去做的那件工作,或者是召喚任何人去完成的重要工作。這種通過對一項重要工作和有價值的工作形成的自我實現(xiàn),也可以稱作通往人類幸福的道路。
康瞧:那么,可不可以說:要賦予工作以使命感?
馬斯洛:如果你把這個世界上重要的某種東西放到你自己身上,那么,你本人就成為重要的人物了。你因此而使自己變得很重要了。每一項任務都會“召喚”世界上的那一個最適合干那件事情的人,就像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一樣。而且,一個人會感覺到那種召喚是最強烈的,因此對它的召喚也會產(chǎn)生反應,彼此都有一種雙向影響,有雙向的合適性,就像好的婚姻,就像好的友誼——彼此是為對方而設計的一樣。
康瞧:學習、創(chuàng)造力、公平、責任心,還有公正感,都自然地來到人們身上——有人說,這就是馬斯洛的理論。可以這樣說嗎?
馬斯洛:我不好肯定。但每一個人都存在內(nèi)在的需求——需要美、真和公正等等的最高價值。當我們自己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當我們開始實現(xiàn)自己最深層次的潛力時,我們就會越來越獻身于其他人的幸福。因而,自我實現(xiàn)和集體實現(xiàn)似乎并不矛盾。
康瞧:這一內(nèi)在需求是人的天性。可惜,正如你說的,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的天性一直都被低估了。這又是為什么?
馬斯洛:如果說真正的自我實現(xiàn)很少有人能達到,那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成年后仍然在為滿足那些低級需求而努力。人們必須對自己的命運、對自己的前途做出回應。否則,他就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康瞧:你一直倡導 “進步管理”,又稱“理想管理”,在中國還有一種翻譯叫“優(yōu)心態(tài)管理”——那是一種非常迷人的管理模式。
馬斯洛:是這樣……我必須強調(diào),這是通往經(jīng)濟和財務成功的道路。比如,把一些工作當作就好像他們是高層次的“Y理論”人類來對待是有益的,不僅僅因為《獨立宣言》,不僅僅因為《圣經(jīng)》或者宗教信條,或者任何此類的東西,而是因為這就是通往任何意義上成功的道路,包括財務成功在內(nèi)。
康瞧:教皇J·保羅二世在《百年散論》中說過一句話:利潤是商業(yè)的生命調(diào)節(jié)器,可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因素等別的原因也應該考慮在內(nèi),這在長期看來至少與一門商業(yè)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我想,他的觀點,與你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致的。
馬斯洛:……
人類的創(chuàng)造潛力丟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康瞧:彼德·德魯克在一次講演時,對那些高層經(jīng)理人說,如果大家的公司里面有一些“死木頭”,就請你們舉手告訴我。很多人舉手之后,他又發(fā)問:那些人是在你面試他們并決定聘用的時候就是“死木頭”呢,還是后來才變成了“死木頭”的?這話很有震撼力和反思性。如果你在場,你如何回答?
馬斯洛:這個問題不難回答。當我看到德魯克的《管理的實踐》一書,就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管理著作……說回答嘛,當然我可以這樣反問:是啊,在當前的環(huán)境下,員工為什么不創(chuàng)造、不革新了?其實,我們更應該反思:人類的創(chuàng)造潛力丟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每一種新發(fā)明,每一種新發(fā)現(xiàn),都會引起某種混論。非常舒適地安于現(xiàn)狀的那些人,他們會受到震動,并感覺到不自在。很明顯,任何偉大的發(fā)現(xiàn),任何偉大的發(fā)明,任何需要對已經(jīng)被征服的領域進行重新承認的東西,都不太容易被人們輕易地接受。
康瞧:你的意思是,創(chuàng)新常常被不創(chuàng)新扼殺了。可是,作為人,也有懶惰的一面,難道不是這樣嗎?
馬斯洛:人確實是有惰性的。我經(jīng)常對學生提出一些問題:“你們當中有誰認為自己會有非凡成就?你們當中有誰會改變世界?”當他們的臉上露出迷惑的神情時,我就繼續(xù)說:“如果不是你們,那又是誰呢?”激勵人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尋找意義,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必須學會并正確看待抱怨
康瞧:現(xiàn)在,令企業(yè)管理者頭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抱怨——員工總是不滿意。這到底是為什么?
馬斯洛:人類總是會抱怨。沒有什么伊甸園可言,沒有什么天堂可言,沒有什么上蒼,而只有偶爾的天示。不管人類得到什么樣的滿足,他們總是不會滿意,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人類總能夠把一些滿足的事情扎在褲帶底下,不管是福也好,是好運氣也
罷。人類絕對會暫時追求于這些東西。接著,一旦滿足以后,他們就會忘記這些東西,并開始把手伸向未來,以便得到更高的祝福,因為人類要無止境地追求好的東西,這在我看來是一個永恒的過程,使人類永遠地向未來發(fā)展下去。
康瞧:按照你的動機理論,我們永遠也不應該指望抱怨會停止下來,我們只能期盼抱怨層次越來越高了。
馬斯洛:沒錯。抱怨玫瑰園的意思就是說,你的肚皮飽了,你的頭上已經(jīng)有了一個屋頂,你的爐子還在燒著,你不怕淋巴結鼠疫,你不怕被謀殺……許多其他的條件也是好的,已經(jīng)得到滿足。這就是關鍵所在:高水平的抱怨不能簡單地當作其他的任何抱怨,它還必須用來指明所有的預先條件,這些條件都必須得到滿足,以便使這種抱怨上升到一個從理論上來講是可行的高度……我們必須學會并正確看待抱怨,讓這種抱怨在動機水平上上升。
康瞧:你的意思是,這種上升層次的抱怨,反而是一種進步。
馬斯洛:難道不是嗎。我們必須記住:不管父母、婚姻、中學或者大學有多么的好,總還有可以感覺到的辦法來改善狀況。就是說,總應該有抱怨和牢騷。這里,就有一個區(qū)分的必要:積極的抱怨和消極的抱怨。
康瞧:作為一個經(jīng)理人,也應該將抱怨看作是一種批評,這樣才可以找到問題的所在:抱怨者希望的東西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問題在前面等著?
馬斯洛:我認為,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了:一個組織的健康水平或者是發(fā)展的水平,從理論上是可以通過抱怨或者牢騷來定級的。但是,盡管抱怨不斷,我始終認為,利他主義、同情心、愛和友誼是最基本的人的傾向,盡管它們可能在早期被有害的經(jīng)驗所掩蓋甚至毀掉。
康瞧:現(xiàn)在,員工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jīng)引起了企業(yè)管理者的重視,你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有哪些建議?
馬斯洛:最好的管理者應該懂得如何促進被管理者的健康。辦法有兩個:一是滿足被管理者的基本需求,包括對安全感、歸屬感、情感關系、友誼關系的需求,以及對聲望與自尊的需求;二是滿足他們高層次的動機或需求,例如對真、善、美、正義、完善以及規(guī)律的需求。
個人的目標必須與組織的目標結合起來
康瞧:現(xiàn)在,很多企業(yè)片面、甚至偏激地理解“執(zhí)行力”,將員工管理得服服帖帖,以為這樣就可以讓制度、決定、流程等暢通無阻。對此,你怎么看?
馬斯洛:我堅信的一個觀點就是:權力下放式的管理方法,就是過著積極的生活的人與那些僅僅作為無望的人而生活著的人之間的差別。我毫不懷疑,在大型組織里一直起作用的那種順從性的行為準則絕對需要修正和改動。我們必須得找到一個辦法,讓人們在一個公司里保持自己的個性。
康瞧:我們總會聽到有的企業(yè)“出事了”:員工情緒抵觸,集體沉默抗議,最后演變成罷工。你認為問題出在哪里?
馬斯洛:這一定是多方面因素的結果。但是,我們好像都在某種意識水平上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權威型或者強制型管理對員工的尊嚴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那么,他就反抗,為的是要恢復他的尊嚴和自我價值,他會非常主動地帶著敵意和故意破壞情緒來干活,或者消極地干,就像奴隸一樣……甚至用各種卑鄙的、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陰毒的辦法來回擊。
康瞧:一旦人的自尊受到傷
害,上述的現(xiàn)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嗎?
馬斯洛:很難避免……當這些被動的、偷偷摸摸的、陰毒的、暗地里的報復到來時,他們是出于憤怒,出于被利用,或者被控制,或者被人以不恭敬的態(tài)度對待而產(chǎn)生的憤怒。員工對控制和因之而來的尊嚴的缺失而產(chǎn)生的反應,可被看作是正常的、根植于生理上的自我保護,因此其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人類尊嚴的表征……奴隸如果不能公開叛亂,他們就會在私下里產(chǎn)生破壞力。
康瞧:這樣隱形的破壞力會更大。如何讓員工擁有自尊感?
馬斯洛:自尊的必要基礎之一來自別人的尊敬和鼓勵。人,在于擁有一種尊嚴的感覺,在于當自己的老板。他們值得鼓勵,值得獲得地位、獎牌、名聲,否則,在非常深層的無意識水平上,無法獲得的需求常常會變成容易傷害人的東西。
康瞧: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提醒那些組織的領導者:學會尊重每個員工的缺陷,也容忍每個員工的局限,而且還要一路祝福他們的成功。因為我們大家都需要受到表揚。沒有一個人不關心自己到底做出了多大貢獻。
馬斯洛:不錯。人們成長得越多,那種權威型管理的效果就越差;人在高壓情形下發(fā)揮作用的水平就越低,他們就越會憎恨它。企業(yè)經(jīng)營者不可能靠命令來激發(fā)員工更大的創(chuàng)造力。只有當員工能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感覺時,創(chuàng)造性才會出現(xiàn)。循規(guī)蹈矩和馴服的員工是很少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
康瞧:不過,很多企業(yè)經(jīng)營者沒有意識到這些。吉姆·柯林斯在《基業(yè)常青》一書中說:“X理論仍然主宰著大部分組織。許多經(jīng)理和企業(yè)家仍然持有隱藏的假定,認為人不能夠完全相信,‘需要不時地檢查,需要‘促進,否則人們就不努力工作。權威主義的生命力仍然很強大。它不僅僅局限于一些老式的大公司,許多企業(yè)家也都用X理論的鐵掌來統(tǒng)治其王國。”
馬斯洛:可惜,我沒有看到過這部書。但我可以說,對Y理論管理哲學確切和終極的信任,雖然目前還沒找到足夠多的理由。可是我認為,對于X理論來說,目前確切的證據(jù)要更少一些。
康瞧:那你還是贊成Y理論的。
馬斯洛:Y理論管理,或者叫理想管理,一定會產(chǎn)生更好的人類,更健康的人,產(chǎn)生比X理論管理或者權威型管理更可愛的,更值得人崇敬、尊重的,更有吸引力的,更友好、更仁慈、更有利他主義精神的那一種人。
康瞧:從需要層次理論來分析,人們一旦有了安全感,一旦他們不再饑餓,不管他們所做的是什么工作,或者處于什么水平,他們想要的一切就是學習和發(fā)展。這個時候,“共享前途”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馬斯洛:任何組織的管理問題,都可以用一種新方法來加以解決:建立起某種環(huán)境條件,使人的目標與該組織的目標結合起來。
康瞧:也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工作是一種幫助別人將他們自己的目標與組織的目標對接的方式。
馬斯洛:沒有別的方式。
康瞧:可是,在這種“對接”的過程當中,我們的一些領導者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用足夠的注意力去傾聽團隊成員的意見,沒有關心他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他們不去發(fā)現(xiàn)員工真正感到激動的事情,哪些工作是他們愿意去做的,哪些是他們不喜歡做的……結果,不是遺憾,就是很慘。
馬斯洛:把一些人放到適當?shù)奈恢蒙希屗麄円贿呑鲎约合矚g的事情,常常會令他們感到超越感,從而更加富有責任心。這是實踐證明過了的,但是,確如你說的,非常遺憾,不知道很多經(jīng)理人為什么視而不見。
康瞧:難怪有些人說,他們離開那個地方,不是因為看不到工資條了,而是不再清楚自己往哪里走,公司往哪里去。
馬斯洛:這是領導者的無能。
領導者要成為一個滋養(yǎng)信心的人
康瞧:那么,我們就來說說領導者和領導力。你是如何看待領導者的?
馬斯洛:事實上,領導者是由這個集體請出來充當集體的臂膀的人,或者是集體的仆人……讓他在正確的時間發(fā)出正確的信號。身為一個領導者,他肯定只感覺到他是在承擔一份責任,或者,他是在為這個團隊服務,而不是反過來的情況。
康瞧:現(xiàn)在,很多的領導者都喜歡下屬順從。我認為,這很要命。
馬斯洛:其實,大多數(shù)領導者都必須能夠經(jīng)得住別人的敵意,也就是說,都可以忍受不受人歡迎的苦
處,同時還不會感到不安。那種必須受到所有人愛戴的人,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都不太可能成為好的領導人。
康瞧:領導者應該學會忍受孤獨。
馬斯洛:這種品質(zhì)就是一種財產(chǎn)而不是一種責任了。
康瞧:很多領導者愛唱紅臉,偏“柔”,你認為可取嗎?
馬斯洛:領導者必須能夠說“不”。如果那是客觀所需的話,他要強硬,要開槍,要傷害一些人,要使人感到痛苦,等等。或者,換一種說法,這個老板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都不能表現(xiàn)出軟弱。他不能害怕而左右旁顧。他必須足夠勇敢,以適應情況。他說“不”,為的是維持紀律,為的是要否決,而且要在一些情形下當“惡人”。
康瞧:可以說說你心目中的合格的領導者嗎?
馬斯洛:從理想的角度來說,最堅強的老板,就是那種將他最基本的所有愿望都予以滿足的人,也就是說,對于安全的需要,對于渴望的需要,對于愛的需要和對于被愛的需要,對于地位的需要和對于尊敬的需要,最后還有對于自信和自尊的需要。這一點,與說一個人越接近自我實現(xiàn)、他就越有可能成為領導者或者老板是一樣的,他在大多數(shù)的情形下,在普遍意義上講,都有可能成為出色的領導者。
康瞧:我想,你對有關領導者的這個話題,一定還有很多想法的。因為你做過大學的系主任,后來又成為美國心理學學會主席,你有切實的體會。
馬斯洛:好的老板或者好的領導者,在大多數(shù)情形之下都必須有一種在其他人的成長和自我實現(xiàn)中得到快樂的能力,這是心理上的先決條件。他還要能夠規(guī)定必需的紀律,既嚴厲,又有愛心。出色的領導者是一位船長或者將軍。一個好的領導者,也必須能夠充當演奏第二提琴手的角色,讓更好的第一提琴手去表演他的角色,而且還必須能夠像他自己在演奏第一提琴手時一樣喜歡別人的表演。
康瞧:領導者必須善于欣賞和鼓掌。
馬斯洛:但我還是要強調(diào)領導者要說“不”。當事實說“好”、而公眾說“不”的時候,好的領導者應該能夠堅持己見,尊重事實,而不要管公眾的敵意。
康瞧:你方才說,好的領導者是一位“船長”,這讓我想起惠特曼的著名詩歌《啊,船長,我的船長》。
馬斯洛:船長是能夠把擔心的事情壓抑在內(nèi)心的人。我知道,如果我在一條遠洋輪船上,船長把他所有的擔心和焦慮以及滿腹疑云和不確定的擔心都告訴我,我下次就再也不坐那條船了。我不想體會他的那些焦慮。領導者的作用的一部分是要成為一個滋養(yǎng)信心的人。要成為這種意義上的領導者,即他能夠承擔全部的責任,而不是讓大家感到擔心,或者恐怖。
康瞧:領導者應該善于掩飾自己的內(nèi)心,該沉默時,要閉嘴。
馬斯洛:對。尤其當他承擔著重要責任的時候,最好應該把一些麻煩留給自己,讓煩心的事情爛在自己的肚子里,而不要通過公開放任地釋放這些焦慮的
方式來減輕自己的壓力……他必須把這些東西留在自己的身邊,至少應該在公司外面,而不是在公司內(nèi)部表達這些東西。
康瞧:這也是一種承擔吧,需要強大的定力,時髦的說法就是淡定。
馬斯洛:如果領導者動不動就把手腕絞起來,露出焦急之態(tài),就會使部分的員工士氣大落。所以,他得學會把一切隱憂自己一個人擔著。
康瞧:領導應該是強有力的人。
馬斯洛:我們有可能不喜歡強有力的人,比如戴高樂、肯尼迪、拿破侖、羅斯福等,可是,我們禁不住會尊敬他們,而且還有可能傾向于贊同他們的意見,信任他們。當然,這是一種萬有的明證,是在戰(zhàn)爭的生死較量里得出的結論。強硬但有能力的領袖有可能會遭人嫉恨,可是,比起軟弱無力的領袖來說,他還是更受人歡迎一些。那些軟弱的領袖有可能看上去很可愛,但他們可能給人們以死亡。
協(xié)同原則:
給予的越多,保留下來的也越多
康瞧:你一直倡導協(xié)同管理、團隊合作、利他精神……這是基于對人的自身品質(zhì)的認識,還是一種希望?
馬斯洛:兩者都有吧。任何一個人心靈里的協(xié)同越是高,同時也就是朝另外一個人更大的協(xié)同效果前進,也是在朝著增大的社會協(xié)調(diào)、組織協(xié)調(diào)和團隊協(xié)調(diào)前進。更好的人和更好的團隊是彼此的因果,更好的團隊和更好的社會也是彼此的因果。也就是說,更好的個人,傾向于在他所在的團體里面形成更好的團體。而且,一個團體越是好,它就越是傾向于改善這個團隊里的人。
康瞧:人們會彼此影響。如果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能自掃門前雪,那么,世界就會非常清潔。
馬斯洛:……
康瞧:如果我沒有記錯,社會協(xié)同效果學說,是著名的心理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最先闡述的,她也是你尊崇的老師。她的基本意思是:協(xié)同制度如果組織得好,一個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同時也就自動幫助了別人;一個千方百計充當利他主義者,一個幫助別人,一個一心要無私奉獻的人,也自動和不管愿意不愿意地得到了自我所需要的好處。顯然,這個觀點應該引起企業(yè)管理者的思考,并在企業(yè)里形成合作、協(xié)同的氛圍。
馬斯洛:露絲·本尼迪克特的觀點也就是說,在合作的情況下,你給某人的權利和影響越大,你自己得到的也就越多。同時,他給予的越多,他保留下來的也越多。
康瞧:協(xié)同、合作……在體育項目中非常容易體現(xiàn)出意義來。
馬斯洛:對的。例如籃球比賽,球隊的利益超越了任何一個具體球員的利益,而球隊的益處也已經(jīng)成為這個人的益處,他無法分辨其中的差別。因此,到底是誰得了分都不太重要了。球隊上場的五名隊員將會同樣為該球隊感到自豪,也為每個人和彼此感到自豪。進一步說,任何帶有籃球意識的人,同樣都會注意到這一點,相對于一個好的“投籃手”來說是一個好的“傳球手”的人,跟實際上把籃球投入籃中的那個人感到同樣多的榮譽感。但是,當這種協(xié)同被打破時,你最后得到的就是一個極差勁的球隊。
康瞧:這也正如你說的,越是有團隊精神,他們就越是延緩彼此榮辱與共的依賴,他們對彼此的信任也就越多。作為一個經(jīng)營者和經(jīng)理人,就要想方設法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的協(xié)同氛圍。
馬斯洛:再換一種方法說,制造好的伏特加的最佳條件,就是擁有一個完美的世界。或者,反過來說,這個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不完美,最終都有可能對其伏特加的質(zhì)量和自動水筆以及汽車的質(zhì)量產(chǎn)生影響。
康瞧:協(xié)同是要創(chuàng)造一種大的聯(lián)動或者整合,彼此分享。
馬斯洛: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與別的事情聯(lián)系在一起,每一個人也都與別的人關聯(lián)著,現(xiàn)在生活的每一個人,也都與未來即將生活著的人發(fā)生關聯(lián),這樣一來,完美就會有彼此的影響。
康瞧:非常感謝……我的問題到此結束了,但你一定還有話要說吧。
馬斯洛:如果你有意逃避你本來可以發(fā)揮的潛力,那你的余生將必定是不幸福的。——這句話我說過多次了,但我非常愿意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