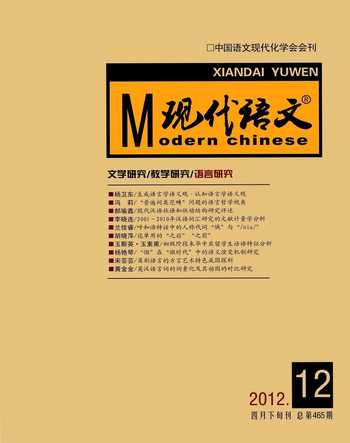從控制動詞角度談PRO分布
龔鵬程 楊成虎
摘 要:與Chomsky提出的原則及參數(shù)理論中其他的次原則系統(tǒng)研究相比,控制理論的研究還尚須發(fā)展,且控制理論中空代詞PRO的分布規(guī)則有待商榷。PRO的分布特點是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在句中呈互補分布。本文從詞匯角度出發(fā)對PRO的分布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當PRO所在的分句作主句動詞補語時,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動詞影響PRO的分布,致使PRO和顯性名詞短語互補分布可出現(xiàn)例外情況。但詞匯特征對PRO分布的影響還存在局限性。
一、引言
Chomsky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空語類,與之相關(guān)的是空語類所屬的控制理論,與Chomsky提出原則與參數(shù)理論中其他的次原則系統(tǒng)研究相比,控制理論還需發(fā)展。其中相關(guān)學(xué)者對控制理論中空代詞PRO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少努力,而PRO的分布特點已經(jīng)明晰,這一特點在相關(guān)文獻中被稱為“PRO定理”(PRO Theorem),即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在句中呈互補分布。這一定理是根據(jù)格理論而得來,顯性名詞短語在句中出現(xiàn)必須具備格,而PRO沒有格,不受格限制,所以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在句中呈現(xiàn)互補分布。關(guān)于PRO分布特點,相關(guān)學(xué)者多從格理論出發(fā)對其進行研究,而本文擬從詞匯角度對PRO的分布進行探究,因控制動詞可分為主語控制語動詞和賓語控制語動詞,本文嘗試從這兩類動詞對PRO分布的例外情況進行闡釋。
二、關(guān)于控制理論的研究
關(guān)于控制理論,溫賓利(2002)給出較為簡單的定義:“在生成語法中,關(guān)于PRO的理論稱為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徐烈炯(2009)則說,“研究控制的理論稱為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國內(nèi)外不少學(xué)者對控制動詞進行了研究,南潮(2009)認為,“提升和控制動詞屬于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動詞。語義上,提升主語不是該動詞的題元,控制語則為動詞的題元,受控語與分句謂詞有論旨關(guān)系”;許洪巧(2008)認為,“提升動詞與控制動詞的區(qū)別是:1.題元角色指派差;2.非限定性不定式補語分句的被動語態(tài)的差;3.主語的語義選擇的差;4.虛義主語使用差”。Culicover和Jackendoff(2006)認為,“1.控制動詞可分為多種,一些可以表示處所性,另外一些則不能;2.不管處所性是否存在以及什么是控制語,都可從語義角度解釋,特別是可從題元角色解釋;3.控制動詞的句法實現(xiàn)取決于滿足題元條件的概念結(jié)構(gòu)和約束理論之間的關(guān)系;4.控制動詞應(yīng)該從語義角度出發(fā)進行研究,而非從句法角度”。Polinsky和Potsdam(2006)向我們展示了不同類型的控制動詞和提升動詞,并從句法角度論證這些動詞存在的合理性。他們認為“從實證角度講,控制復(fù)寫動詞這一類型在多種語言中存在,并且超出任何人的想象”。Aldgidge(2010)利用控制移位分析的理論為我們解釋了古漢語中“莫”的黏著爬升現(xiàn)象;Dubinsky和Hamano(2010)認為日語中句法的強制控制是由TP出現(xiàn)而形成的阻礙造成。
關(guān)于“控制”的概念,吳剛(2006)認為,“所謂控制,指的是PRO與某些名詞詞組之間存在共指關(guān)系,這些名詞詞組是PRO的先行語,被稱為控制語(controller)”。我們先看一個例子,“John i has not described whether [IP PRO i to study Mandarin]。這個例子中,PRO需要依賴句子中的名詞短語‘John確定指稱意義。這種依賴關(guān)系被稱為控制(control);‘John控制PRO,PRO受‘John的控制;‘John是PRO的先行語,也叫控制語(controller)”(溫賓利,2002:168)。此外,徐烈炯也對控制理論做出了定義:“先行語與PRO之間的關(guān)系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約束理論。這種關(guān)系稱為控制(control)關(guān)系,PRO的先行語稱為控制語或控制成分(controller)”。根據(jù)以上我國學(xué)者對控制理論給出的定義,本文可以歸納出:PRO與先行語或某些名詞詞組存在的關(guān)系并非依賴關(guān)系或約束關(guān)系,而是控制關(guān)系或共指關(guān)系。那么,PRO與名詞詞組之間就存在控制關(guān)系,研究PRO的相關(guān)理論就是控制理論。
從以上關(guān)于控制理論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控制理論主要是研究關(guān)于PRO的理論。什么是PRO呢?Chomsky根據(jù)[+/- Anaphor](照應(yīng)性)和[+/- Pronominal](代名性)兩套特征來進行分類,據(jù)此空語類分為了四類:NP語跡[+A,-P]、pro[-A,+P]、變項[-A,-P]、PRO[+A,+P]。其中我們可以得知PRO具有照應(yīng)性和代名性。“具有[+A,+P]特征的名詞短語在管轄范圍內(nèi)必須既受約束又不受約束;而這是不可想象的”(溫賓利,2002:166)。空語類是在句法、語義表達式中存在,而在音系表達式中沒有音系矩陣的成分(徐烈炯,1988)。也就是說,空語類是具有句法和語義作用,但沒有語音形式的語言成分。雖然在語音形式上沒有體現(xiàn),但它也是一種語言符號,具有相應(yīng)的語法和語義功能。
三、關(guān)于PRO的研究
(一)PRO的控制語
到目前為止,PRO的控制語還不容易確定,這里有詞匯、語義和語用等因素錯綜復(fù)雜地交織在一起,很難梳理清楚。近年來,這一難題引起了不少語言學(xué)家的注意。本文將從詞匯因素角度對PRO的控制語進行闡釋。
PRO有時有任指的意義,有時則依賴控制語才能得到解釋。我們先來看幾個例子:
(1)John i was asked [PRO i to leave].
(2)John i was asked [how PRO to leave].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包含PRO的句子S(sentence)中C(complementizer)位置空著的時候,PRO受句中特定成分的控制,例(1)的PRO就受到先行語“John”控制;當C位置由“wh”詞語占據(jù)著的時候,PRO不受特定成分控制,這時PRO為泛指(arbitrary reference)的代詞,例(2)中PRO不占據(jù)C位置,而是由“wh”詞語“how”占據(jù),這樣,PRO就不受控制,從而成為泛指的代詞。例(1)中的PRO受先行語“John”的控制,并且必須受到“John”的控制,這種情況被稱為強制控制(obligatory control)。例(2)中,PRO不受先行語“John”的控制,成為泛指的代詞,PRO在例(2)中的情況受到的控制就是非強制控制。
在不斷地深入研究后,Chomsky發(fā)現(xiàn)對確定PRO控制語的方法還有另外兩種:
第一,用[+/-CONTROL](控制)特征給動詞分類。Chomsky根據(jù)[+/-CONTROL](控制)特征對動詞進行了劃分,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動詞要求其賓語從句中的主語用PRO,而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動詞的賓語從句中主語不能用PRO。例如:
(3)John tried [PRO to leave]
(4)*John said [PRO to leave]
“try”是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動詞,“say”是不具有[- CONTROL](控制)特征的動詞,因此,例(4)中的從句主語不能用PRO。這種分類就是詞匯分類,不是句法分類。Chomsky認為某個動詞屬于哪一類都是由詞庫規(guī)定的,并無句法規(guī)律可循(徐烈炯,2009:279)。
第二,對具有[+CONTROL]特征的動詞進行更進一步得劃分,而劃分的標準或依據(jù)是動詞是否具有[+/-SUBJECT CONTROL]特征:具有[+SUBJECT CONTROL]([+SC])的控制動詞稱為主語控制動詞(subject control verb);具有[-SUBJECT CONTROL]([-SC])的控制動詞稱為賓語控制動詞(object control verb)。例如英語中的“promise、try、decide”等動詞是典型的主語控制動詞;而“persuade、tell、force”等是典型的賓語控制動詞。例如:
(5)John i promised Mary [PRO i to go early].
(6)John forced Mary i [PRO i to go early].
(二)控制動詞對PRO分布的影響
根據(jù)以上對控制理論、空語類、控制動詞的介紹和說明,本文認為對PRO的分布應(yīng)從詞匯角度出發(fā),并可根據(jù)動詞的控制特性進行論證。
溫賓利(2002)用例子向我們論證了PRO的分布規(guī)律為: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PRO的分布只局限于非時態(tài)分句的主語位置。之后向我們介紹了PRO定理:PRO不得受到管轄。并且介紹了“PRO定理說明了PRO在句中的允準條件:即PRO只能在不受管轄的位置上出現(xiàn)”。此后,為了說明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性分布有例外情況,采用了下面的例子:
(7)John wants Mary to win.
(8)John wants PRO to win.
例(7)是個例外授格結(jié)構(gòu),不定式“to win”的主語“Mary”受主句動詞“wants”的管轄,并得到例外授格。在例(8)中,PRO同樣是不定式分句“to win”的主語,也應(yīng)該受到“wants”的管轄并得到授格。這是否意味著PRO與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性分布這一結(jié)論站不住腳?我們無法推翻“PRO與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這一結(jié)論。我們要做的是看能否對例句提出合理的解釋。一種觀點是,動詞“want”在例(7)~(8)中選擇不同的成分作補語,也就是說,兩個句子中動詞后的成分具有不同的結(jié)構(gòu)。在例(7)中,“want”選擇IP作補語,其結(jié)構(gòu)如例(9)所示。由于IP2的中心語I2不能給其主語授格,IP2構(gòu)不成管轄障礙,主句動詞“want”便“越界”給[Spec,IP2]位置上的名詞短語“Mary”授格。
在例(8)中,“want”選擇的不是IP,而是CP;其結(jié)構(gòu)如例(10)。例(10)中,“want”不能隨心所欲地管轄IP2的標志語。這是因為中間的CP形成了管轄障礙:按照管轄的定義,管轄語和被管轄的節(jié)點之間不能有最大投射。所以,縱使IP2不能構(gòu)成障礙,其標志語位置上的成分也不能從主句動詞處得到授格。
因此,在例(7)~(8)中,名詞短語“Mary”和PRO仍然呈互補分布:在例(7)中的[Spec,IP2]位置上只能使用顯性名詞短語,在例(8)的[Spec,IP2]位置上只能使用PRO。例如:
(9)John wants [IP Mary to win].
(10)John wants [CP PRO to win].
對于具有相同結(jié)構(gòu)的兩個例子為何有不同的結(jié)構(gòu)圖,并說明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是有例外情況的。但從例(9)~(10)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結(jié)構(gòu)圖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為例(10)中加入了一個CP,進而導(dǎo)致“want”不能對PRO授格,從而使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這種解釋存在漏洞,為什么例(10)中可以加入CP,而在(9)中的同樣位置不能加入CP呢?如果例(9)中也加入CP,就會導(dǎo)致“want”不能對“Mary”授格,從而使PRO可以出現(xiàn)在這個位置,而“Mary”不能出現(xiàn)在這個位置。這樣,PRO還是不能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
對于這種情況,我們認為可以從控制動詞的角度對此例進行解釋,從而說明PRO和顯性名詞短語互補分布也有例外情況。從上文可以得知,Chomsky把控制類動詞分為了主語控制動詞和賓語控制動詞。其中主語控制動詞是具有[+SC]特征的動詞,諸如“promise、try、decide”等;賓語控制動詞是具有[-SC]特征的動詞,諸如“persuade、tell、force、want”等。讓我們再回顧下面兩個例子:
(7)John wants Mary to win.
(8)John wants PRO to win.
兩個句子的結(jié)構(gòu)基本上一致,例(7)中使用了“Mary”,而例(8)中使用了PRO。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能使用顯性名詞短語的位置,就不能使用PRO。溫賓利(2002)是從格理論的角度對此進行了闡釋,但增加CP這一方法的說服力不足以證明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存在例外情況。句子中使用的動詞為“want”,是具有[-SC]特征的動詞,因此“want”在句中是對賓語進行控制的動詞。句中“want”對賓語進行控制,所以例(8)的結(jié)構(gòu)圖可以為“John i wants [PRO i to win]”,這里的PRO可以指“John”,也可以指任何人。同理,例(7)的結(jié)構(gòu)圖也為“John i wants [Mary to win]”,這里是指“Mary”要去贏。這里的“want”是賓語控制語動詞,那么主語控制語動詞可否這樣使用呢?先看下面的例子:
(11)John i promised Mary [PRO i to win]
(12)John i promised [PRO i to win]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在作為主語控制語動詞的“promise”作謂語的句中,顯性名詞短語和PRO也是不可互補出現(xiàn)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動詞都可以證明PRO和顯性名詞短語不是互補出現(xiàn)的呢?上文我們已經(jīng)提到過了,有些動詞是不具備[+CONTROL]特征的。例如動詞“say、arrive、leave”等:
(13)*John said [ PRO to leave]
這樣的動詞后是不能用PRO的,所以是不存在和顯性名詞呈互補性分布的。
主語控制動詞和賓語控制動詞都屬于控制動詞,而像“say”此類[-CONTROL]特征的動詞為非控制動詞。根據(jù)以上對例句的分析,我們從控制類動詞的角度對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存在例外情況進行了論證,同時從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具備[+CONTROL]特征的動詞對“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這一結(jié)論有所挑戰(zhàn)。
溫賓利(2002)從格理論角度對PRO分布進行了解釋說明,此舉還有待商榷,本文從詞匯特征對PRO的分布進行了闡釋。但是,詞匯特征對PRO的分布還存在局限性:只適用于PRO所在的分句作動詞補語時的情況。帶PRO的分句在句中作附加語時PRO也受到強制控制,這種情況顯然與主句動詞的特征無關(guān)。如下列例子為“arrive、leave”不具備[+C]特征,然而句中的PRO必須以主句主語為先行語。帶PRO的分句在主句中作主語時PRO的控制就更不能用動詞的特征進行解釋了。
(14)John arrived [PRO pleased with himself/ * oneself].
(15)John left the band [ PRO to start working on his/ * one's own].
四、結(jié)語
本文運用控制理論相關(guān)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控制理論就是PRO與先行語或某些名詞詞組的存在并非依賴關(guān)系或約束關(guān)系,而是控制關(guān)系或共指關(guān)系。PRO與名詞詞組之間存在控制關(guān)系,研究PRO的相關(guān)理論就是控制理論。而本文認為,PRO的分布除了可以從格理論的角度出發(fā),亦可從詞匯角度對PRO的分布特點進行探究,認為控制動詞是必須具有[+CONTROL]特征的動詞,并根據(jù)[+/-SUBJECT CONTROL]特征對控制動詞進行細分。基于此,本文從控制動詞的角度對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性分布存在例外的情況進行了闡釋,認為具備[+CONTROL]特征的動詞對“PRO和顯性名詞短語呈互補分布”這一結(jié)論提出挑戰(zhàn)。但只當PRO所在的分句作動詞補語時,詞匯特征才適用此情況。由此可見,詞匯特征對PRO的分布還存在局限性。通過探究,本文發(fā)現(xiàn)PRO的分布還受到詞匯特征的影響,希望這一發(fā)現(xiàn)能夠豐富空語類PRO的研究,促進空語類和控制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
參考文獻:
[1]溫賓利.當代句法學(xué)導(dǎo)論[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
2002.
[2]徐烈炯.生成語法理論:標準理論到最簡方案[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9.
[3]南潮.生成語法中提升與控制動詞研究[J].湖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
(社會科學(xué)版),2009,(6).
[4]許洪巧.論英語提升動詞[D].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8.
[5]Culicover,P.and R.Jackendoff.Turn over the control to
the semantic[J].Syntax,2006,(9).
[6]Polinsky.M.and E.Potsdam.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ntrol
and binding[J].Syntax,2006,(9).
[7]Aldgidge.E.Clitic.climbing in the archaic Chinese[A].
Hornstein.N and Polinsky.M.Movement Theory of Control[C].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149~182.
[8]Dubinsky.S and Hamano.S.Framing the syntax of control
in Janpanese(and English)[A].Hornstein.NandPolinsky.M.Movement Theory of Contro[C].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183~210.
[9]吳剛.生成語法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10]徐烈炯.生成語法理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8.
[11]Chomsky,N.On binding[J].Linguisitic Inquiry,1980,(11).
[12]Huang.J.PRO-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theory[A].
Jaeggli.O and Safir.K.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C].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