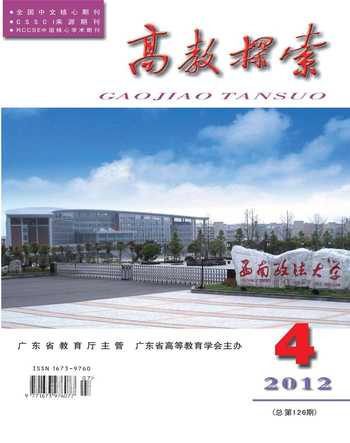“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內涵、要求與政策構想
饒燕婷
摘 要:協同創新是胡錦濤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講話中針對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提出的新要求。作為一種新的產學研合作理念,產學研協同創新是通過多個主體的協同作用和資源共享,產生整體大于部分的協同效應,實現創新價值的最大化。它不僅要求創新主體的協同合作,也要求創新目標、組織、制度和環境等的協調與整合。為了鼓勵和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政府應制定和完善與產學研合作有關的法律、政策,為各方主體的緊密協作提供制度保障;積極創建產學研合作的戰略聯盟、中介機構和各種公共服務平臺,為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組織保障;出臺促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的財稅、金融、人才流動、儀器設備共享等相關配套政策,為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人財物保障。
關鍵詞:產學研;協同創新;內涵;政策構想
2011年4月2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提出,要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戰略選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高等學校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大力增強科學研究能力,在“提升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的同時,“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1]。這一重要講話“第一次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對產學研協同創新提出新的要求”[2],為我國產學研合作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作為一個新的政策議題,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內涵、本質都還不夠清晰,政策走向也不甚明朗。因此,本文擬對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概念、內涵和基本要求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幾點政策建議和構想。
一、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內涵
“協同”一詞自古有之。根據《漢語大詞典》的釋義,“協”字有“和睦、合作、協調、匯集、匯合、聯合、協助”等意思,“協同”則表示“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行動”。“協同”與“合作”是兩個意義相近但內涵不同的概念。在英文語匯中,與“協同”相對應的詞是“collaboration”,與“合作”相對應的是“cooperation”。美國學者Miles等人指出,“協同”在哲學意義上是一個與“合作”不同的過程,協同的預期結果是相對明確的,未來回報的分配可以事先協商,而合作各方則是以自身利益為基礎開展活動。[3]此外,Von Krogh也指出,協作往往涉及不可預知的結果,并嚴重依賴信任以及對誠實與公平價值觀的共同承諾。與合作不同,協同方要盡可能顧及對方的利益,就像對自己利益的考慮一樣。[4]可見,與“合作”相比,“協同”更加強調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基礎上為實現同一個目標而通力協作,以及公平誠信的合作環境。
“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是把協同的思想引入創新過程,指創新過程中各創新要素在發揮各自作用,提升自身效率的基礎上,通過機制性互動產生效率的質的變化,帶來價值增加和價值創造。國外有學者指出:“直到20世紀90年代,學術和商業文獻都試圖把創新和創業描繪成是由單個實體所開展的活動,新的創意和產品創新被認為是由單個企業家、一個小型企業、公司內部的一個單位創造的。然而,今天競爭環境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復雜性水平和變化,使得單元化的創新方式變得越來越困難,并為跨企業、行業和國家的新創意的產生與知識的共享創造了機會。”[5]“協同創新是通過思想、知識、專門技術和機會的共享創造跨越組織邊界的創新,是保持個體組織(企業)的持續創新,增補其創新力量的一種手段,能夠使企業彌合已有創新水平和所需創新水平之間的差距。”[6]因此,Freeman等人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已指出,“出現各種形式的跨組織創新協作企業的熱潮也就不足為奇了”[7]。
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依靠單個主體的散兵作戰或淺層互動很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而創新主體間的協同作用和資源共享則有可能帶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聚合效果,加速創新的進程。有專家指出:“產學研協同創新是指企業、大學、科研院所三個基本主體投入各自的優勢資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務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協同支持下,共同進行技術開發的協同創新活動。”[8]與產學研合作相比,產學研協同創新更加強調多個主體間的協作關系,以及知識和專業技術的共享。其本質是打破人、財、物、信息、組織之間的各種壁壘和邊界,使各主體為一個共同的目標進行協調的運作,以產生“1+1>2”的協同效應。
我國產學研合作存在的諸多問題,就其癥結而言,都可以歸咎于合作組織間未能達成協同配合,產學研脫節現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從而致使大量的創新資源處于游離分散狀態,創新效能不高。與以往的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不同,協同創新不再是簡單的線性創新,而是由多個組織或部門參與的非線性創新,通過各組織間的彼此滲透、相互融合,使創新活動在更加廣闊的組織空間內進行,促進資源的整合與流動,實現創新價值的最大化。因此,產學研協同創新可以有效解決我國當前產學研合作中的瓶頸問題,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的緊密結合,提升產學研合作的效能。
二、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基本要求
現代協同論認為,協同應當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協作與融合。因此,與以往“產學研合作”的提法不同,產學研協同創新更加強調多個組織和要素的一體化深度協作,不僅要求創新主體的協同合作,也要求創新目標、組織、制度和環境等的協調與整合。
主體協同是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核心。以往人們在談及產學研合作時,通常是指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之間的技術商業化活動,僅局限于產、學、研三方的合作。然而,協同創新卻認為創新活動除了創新要素內部的互動合作之外,也離不開內部要素與外部要素的協同作用,技術創新活動不應止于產、學、研三方的簡單結合,而是要有多方主體的介入,形成新型戰略聯盟來促進合作績效的提升。因此,產學研協同創新除了要求企業、大學、科研機構這三大基本主體投入各自的優勢資源和能力之外,還要求政府、科技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協同支持。其中,企業、大學、科研機構這三方進行技術開發,政府通過法規、政策進行引導和鼓勵,科技服務中介機構提供相關信息服務,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支持,通過多方協作共同完成技術開發和技術商業化活動。
目標協同是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在產學研合作過程中存在著多個利益主體,不同的主體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對產學研合作有不同的價值訴求。例如,企業希望通過產學研合作充分利用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技與人才資源,促進產品開發、成果轉化,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益。大學期望通過產學研合作更多地走向社會,提升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而政府則從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希望通過產學研合作來實現科技、教育與經濟的無縫對接,增強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因而,如何協調各方利益主體的需求,找到一個利益結合點,用共同目標來驅動各方主體的創新動力,消除合作中可能存在的種種障礙,是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前提。
組織協同是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支撐平臺。我國目前的產學研合作還主要停留在技術轉讓、合作開發和委托開發等較低層次的合作上,共建研發機構和技術聯盟等高層次的深度合作還比較少。據有關調查顯示,我國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的合作創新有37%是常規技術咨詢,33%是合同委托開發。[9]而發達國家產學研合作的歷史和現實卻表明,產學研合作經歷了一個由技術轉讓—委托研究—聯合開發—共建實體的演化歷程,從合作初期的以技術轉讓為主到今日主要謀求共建實體全程介入,共建實體正在逐漸取代技術轉讓、委托研究和聯合開發而成為產學研合作的主導模式。例如,美國在大學內部建立的“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在企業集群之間建立的研發同盟以及在大學與企業之間建立的“科技園”等,都是建立產學研實體組織開展合作創新的成功案例。產學研協同創新離不開組織協同,通過共建合作實體和技術聯盟搭建創新平臺,使無序態的創新要素和資源進行擴散、組織、融合、轉化,從而形成有序態的知識與技術創新。
體制機制協同是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制度保障。產學研協同創新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管理體制的創新。產學研協作過程中各方的利益范圍、責任邊界、合作動力、協作關系、融資手段等都需要有明確界定,只有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才能保護合作各方的利益,激發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等組織協同創新的動力。Link和Siegel在總結美國產學研合作的經驗時指出,美國商業領域的跨組織協作在過去二十年穩步上升,主要得益于以下制度變革的推動:(1)對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的投資,包括孵化器、科學園和小企業項目;(2)放松反壟斷執法,以促進合作研究;(3)制定旨在促進從大學和聯邦實驗室更迅速地向企業擴散技術的法規,如1980年頒布的《拜杜法》(Bayh-Dole Act)和《斯蒂文森法》(Stevenson-Wydler Act)。[10]產學研協同創新是一種新的合作范式,要有新的體制和機制來將疏散的組織和資源聚合起來,并在創新主體之間建立一種適當的平衡,以制度來引導和規范合作各方的行為,確立合作的長效機制。
環境協同是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堅強后盾。除了主體、目標、組織和制度的協同之外,產學研協同創新還需要有與其密切相關的法律、稅制、政策、市場、文化、信息平臺、金融和中介服務等外部環境的支持。我國的產學研合作普遍存在著各方創新意識不強、動力不足的問題。此外,體制性障礙與法規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因素也阻礙了產學研的協同創新。因此,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環境建設,營造有利于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政策環境和氛圍,調動產學研各方的創新熱情,無疑對產學研合作的加速發展和效能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協同創新是創新要素的全面協同,作為一種新的創新理念和模式,它給產學研合作帶來了新的發展際遇,為提升產學研合作績效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路徑。在堅持“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資源互補、功能互動、平臺互通”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導地位,高校與科研機構的支撐作用,以及政府、科技中介機構和金融機構的協調功能,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或實體組織,構建多方位的合作保障體系,以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激發各方創新潛能,營造有利于協同創新的制度和文化環境,可以大大降低產學研合作的成本和風險,實現創新資源的最優配置,提升產學研合作的效能。
三、我國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政策構想
在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時代,產學研結合作為一種重要的技術創新模式,以及推動科技、教育與經濟緊密結合的有效途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為許多國家的廣泛共識。我國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積極開展與產業界的合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產學研結合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各種形式的合作已在全國普遍展開。然而,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依然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科技經濟“兩張皮”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還沒有形成全面有效的支撐;二是體制機制不健全,產學研結合松散,圍繞產業技術創新鏈持續穩定的合作不夠;三是科技創新資源分散,資源利用和投入產出效率不高,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缺乏全面有效的支撐服務。胡錦濤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提出“協同創新”的新思路,對于打破我國長期以來產學研合作效能欠佳的現狀是一個契機。然而,協同創新作為一種產學研合作的新理念要真正發揮效用,不能僅停滯在理論探討,還需要付諸于政策實踐。
第一,從制度設計上破解科技經濟“兩張皮”的難題,制定和完善與產學研合作有關的法律、政策,營造有利于協同創新的政策法制環境,為各方主體的緊密協作提供制度保障。首先,要加強產學研合作的法制建設,對合作各方的權責、知識產權的歸屬、專利許可等以立法的形式做清晰明確的界定,解決好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問題,形成產學研主體協同創新的內在動力機制。其次,應出臺相應的資助與優惠政策,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與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合作以及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的研發提供經費資助、稅收減免、融資優惠、人才支持,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激勵引導機制。最后,成立專門的產學研協調工作辦公室,實施產學研合作協調員制度,負責協調合作各方的利益和矛盾、企業與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技術的匹配,合作方案的制定,以及知識產權的轉移,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溝通協調機制。
第二,打破組織壁壘,積極創建產學研合作的戰略聯盟、中介機構和各種公共服務平臺,促進長期穩定戰略合作關系的建立、科技信息的流通和科技成果的轉移,為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組織保障。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政府科技資金的引導作用,要求大學、科研機構必須與企業合作才能共同申請一些項目資助,或者設立各種獎勵基金、匹配基金、種子基金、風險基金來促進產學研合作聯盟的建立。另一方面鼓勵在研究型大學尤其是著名研究型大學中建立聯合研究中心和科技中介機構,例如目前一些大學正在運作的產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為產學研的協同創新積極搭建橋梁和紐帶。此外,各級政府、專業學會應積極構建和完善產學研一體化的科技創新公共服務平臺,為產學研的協同創新提供人才、信息、設備、技術支持,以及各種專業服務。
第三,突破資源瓶頸,出臺促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的財稅、金融、人才流動、儀器設備共享等相關配套政策,加大資金支持和各項政策優惠,優化創新資源的配置,為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人財物保障。為此政府主要應致力于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相應的財政資助、稅收減免和投融資優惠政策,通過加大先期引導基金的投入,促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的開展和企業資金的進入。二是制定靈活的人事政策,打破人事管理條框束縛,允許、鼓勵科技人員的流動與交流,并保障科技人員在流動期間的職務晉升、職稱評定及相應福利待遇不受影響。三是建立大學、科研機構的實驗室和大型儀器設備向社會開放的制度,通過網絡平臺向社會開放儀器設備信息,實行專管公用,資源共享,降低創新成本,鼓勵中小企業積極參與協同創新。
參考文獻:
[1]胡錦濤.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1-04-25.
[2][8]張力.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戰略意義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7):18.
[3]Miles, R.E., Snow, C.C., Miles, G.. Collaborative entrepreneurship: how communities of networked firm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economic weal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Von Krogh. Care in knowledge cre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133-153.
[5]Ireland, R.D., Hitt, M..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strategic leadership[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9(13):43-57.
[6]Ketchen, D., Ireland, R., Snow ,C..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wealth creat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7(1):371-385.
[7]Johnsen,T., Ford, D.. Manag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omplex networks: finding from exploratory interviews[R]. 16th IMP Conference. Bath: University of Bath, 2000.
[9]中國產學研協同創新存在的五大問題[EB/OL].http://www.gzc.sdu.edu.cn/html/news/280.html. 2011-06-10.
[10]Link AN, Siegel DS.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責任編輯 劉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