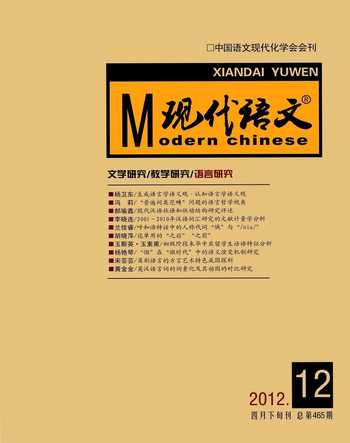英文電影片名漢譯的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周旺 徐賽穎
摘 要: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主體性日漸成為翻譯界人士普遍關注和討論的對象。本文從電影片名入手,分析了譯者主體性在英文電影片名漢譯中的體現。譯者主體性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原電影名理解階段,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選擇,譯名表達階段。
一、引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主體性的問題,這說明了翻譯研究的重點正在轉向譯者的作用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譯學思潮和文化學的興起與繁榮使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譯者不再被認為比原文作者次要,而認為譯者是具有創造性的主體,譯作是原作在后世的延續。譯者的主體性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
作為一種藝術上的再創作,電影名翻譯絕對不能夠脫離譯者的主體性。譯者作為翻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應再被僅僅看作是掌握了兩門語言的人,而應該被看作是具有能力才干的、主體性的、可以被描繪出來的、可以被探討的活生生的人。譯者的這些特點也使本文作者獲得了更多的興趣和動力對其進行研究。本文嘗試通過結合電影名,探討譯者主體性在英語電影名漢譯中的體現。
二、譯者主體性
目前,國內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譯者主體性問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并對譯者的主體性有著不同的理解。查明建和田雨(2003:19~24)在論述譯者主體性內涵時說,“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具體地說,譯者主體性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也體現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和在譯本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等方面”。譯者作為翻譯主體貫穿于整個翻譯活動過程之中,是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個體。在從事翻譯活動時,譯者以自身文化為參照對源語文本進行吸收、消化和藝術再創造,能動地“操縱”源語文本,以實現其翻譯目的。
在國外,貝爾曼也認為譯者是翻譯的主體,他曾指出,譯者的翻譯動機、翻譯目的、所采取的翻譯立場、所制訂的翻譯方案,以及所使用的翻譯方法,使譯者成為翻譯中最積極的因素。譯者的態度、方法和立場一旦選擇和確立,他就為自己定了位置,他譯出的“每一個字都成為了一種誓言”(Berman,1995:75)。貝爾曼認為,譯者的主體性是譯者的一種主觀能動性,翻譯過程也就是譯者從本身所具有的主觀意識出發,積極調動自身內在意識對原文本進行再創造的過程。譯者一旦確定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態度、立場,就要對自己的譯文負責,無法輕易更改。當然,這種主體性不是任意的,而應建立在原文本和原作者意圖的客觀性的基礎上。譯者的主觀理解和翻譯輸出要以源語的內容為客觀依據并使譯者的主觀理解盡量接近原作者的意圖和要表達的思想。Gadmar認為,翻譯是“在譯者理解的指導下文本的再創造”(Gadmar,1975:34)。因此,譯者的主觀因素對原文的理解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譯者的個人經歷——情感,動機,態度,聯想——不僅體現在譯語文本中,而且它們是必不可少的”(Robinson,1991:259~260)。此外,譯者的語言轉換水平、認知水平、跨文化知識、主觀審美意識、語言表達功能等等,都會交叉地作用于原語文本和譯本中。“沒有譯者可以避免在個人作品中一定程度的個人參與”(Nida,1964:154),在翻譯時譯者不可避免地會留下自己的印記。
三、英語電影名漢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翻譯工作者是原作和譯作,原語和目標語之間的媒介。在傳統的翻譯觀中,譯者在中國被看作是機械模仿原作的人,而在西方,譯者被看作是原作的“仆人”。這些稱謂都不符合譯者主體性的地位。作為藝術創作的主角,譯者是與原作者有真正關聯的人。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因此,考慮譯者的主體性就是分析譯者的主體意識。
在上文的分析中,盡管我們已經對譯者的主體性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但對于其在翻譯活動中的真正的體現,我們還不大清楚。本文嘗試結合具體實例來分析在英語電影名漢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一)譯者對原電影名的理解
在翻譯電影名之前,譯者需要對原電影情節有充分的理解,對電影傳達的思想內容有充分的把握,這樣,他所翻譯的電影名才能切合主題。就電影片名翻譯來說,譯者絕不能僅限于對原片名的閱讀,而要從影片的內容,把握片名的內涵。導演和編劇在確定片名時都有一定用意。對電影的完全理解,包括內容、主題、文化背景、影片主角等方面。因此,譯者所進行的閱讀并不同于普通觀眾的一般性閱讀,他不僅要讀懂片名中簡短的幾行文字,更要讀透文字背后的寓意,必須對片名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很多英文電影以人名為片名,但在翻譯時譯者不應當對其采用字對字的翻譯,而應從影片的整體內容來把握,對影片深層意義和真正意義進行解讀。例如“Erin Brockovich”,按字面很容易翻譯成《埃琳·布羅克維奇》。影片展示了一個頑強的女性以她的精神力量征服人們的故事。她的熱情、頑強和堅貞不渝的追求,使她在一次并不平等的斗爭中獲得了勝利。因此,根據影片情節翻譯為《永不妥協》,真實再現了女主人公不妥協的精神,使觀眾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又如電影“Network”,如果譯者沒有觀看電影,而直接將“Network”翻譯成《網絡》,會對觀眾造成誤解。因為影片講述的是發生在電視臺的故事,而與網絡沒有多大聯系。如果譯為《電視臺風云》,既透露了電影故事發生的地點,也會使影片更具吸引力。
因此,譯者在觀看電影時需要充分發揮其主體性。一方面,當譯者在觀看電影時,他也是基于自己的個人經歷、文化背景、認知系統慢慢地接近原電影。另一方面,任何電影作品都有文化代溝,理解好原電影,意味著要跨越這些障礙。只有這樣,譯者才能真正理解并準確傳達原電影的真諦。
(二)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
何躍敏(1997:41~43)認為,好的譯名“既要有藝術性,又要有實用性”。包惠南(2001)指出,影視片名的翻譯“既要符合語言規范,又要富有藝術魅力,既要忠實于原片名的內容,又要體現原名的語言特色,力求達到藝術的再創造”,要講求“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和藝術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導視和促銷作用”。為了達到上述境界,使譯名成為佳譯,并獲得最大的價值,翻譯方法的選擇就顯得至關重要。
原作不同,所選的翻譯方法也將不一樣,常用的翻譯方法有:直譯、意譯、音譯等。選擇任何一種翻譯策略都不是容易的事。選擇何種翻譯策略完全由譯者決定,這就是說,譯者在此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請看下例:
Pearl Harbor——《珍珠港》
Brave Heart——《勇敢的心》
Blood Diamond——《血鉆》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速度與激情》
King's Speech——《國王的演講》
The Expendables——《敢死隊》
以上這些電影名,譯者采用了直譯法,因為原電影名很容易點名電影主題,采用直譯法既保存了原電影名形式,又達到了通俗易懂的目的。
由于中英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如果片面強調保留片名的形式,就會導致以形害意。為使譯語觀眾能真正領會原片名的內蘊,實現原片名與譯語片名在信息、審美等方面的等值,就需要采用意譯法進行翻譯。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就要以影片內容為根本依據,按照漢語獨有的表達方式兼顧中國傳統文化習慣。在成千上萬的譯名中不乏譯者采用意譯法翻譯出來的優秀電影名。如2010年熱門電影“Inception”一上映便席卷了中國各大影院,產生了很大的轟動。原因之一得益于別出心裁又具有很強票房號召力的譯名——《盜夢空間》。片名“Inception”一詞取自電影,在影片中指的是通過夢境中的思想植入,改變他人原本根深蒂固的思想。如果譯者簡單地譯為《思想植入》,語言沒什么感召力,我們可能誤以為這是一部關于文化入侵的政治片,對故事情節沒什么向往。相比之下,譯為《盜夢空間》不僅展現了故事的“夢”主題,“盜”這個字又暗示了此電影是非常刺激充滿挑戰性的。看到電影名,觀眾不得不引發思考:夢怎么能被盜走呢?盜夢用來干什么呢?……譯者采用這種意譯法翻譯電影名,不僅暗含了電影主題,而且給觀眾留下懸念,使觀眾有一睹為快的沖動。
在英美影片中,對于目的語觀眾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很強的人名、地名或歷史事件為片名的電影,譯者一般選用音譯法。例如:
Titanic——《泰坦尼克號》
Jane Eyre——《簡愛》
Chicago——《芝加哥》
Romeo and Juliet——《羅密歐與朱麗葉》
Harry Potter——《哈利·波特》
Avatar——《阿凡達》
The Smurfs——《藍精靈》
(三)譯名的表達階段
在譯名表達階段,譯者會更多地考慮目的語觀眾的期待,站在目的語觀眾的角度來審視原電影名,不斷突破,選擇恰當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電影名,力求獲得最大的市場認同。將英語電影名翻譯成漢語時,譯者不僅要站在中國觀眾的角度考慮中國觀眾的需求,而且要盡可能使翻譯過來的電影名迎合中國觀眾的心理、富有藝術魅力。
例如,電影“Dancers”初譯時有兩個譯本:《一舞傾情》和《舞者》。對于前一個譯名,譯者充分利用漢語音律結構,根據漢字“傾”和“情”的元音韻律,創造了音律美,而第二個版本在這方面相對而言較差。“Outland”譯為《天外天》,既抑揚、又押韻,如果譯者簡單的譯為《邊遠地區》,則不如第一個譯名讀起來朗朗上口。“Courage Under Fire”譯為《生死豪情》(抑揚),“Singing in the Rain”譯為《雨中曲》(押韻),都充分體現了漢語的音韻美。既傳達了感情意義,又增加了審美效果,這樣的影片名就更能吸引觀眾。
四字短語也是漢語的一大特點,使用四字短語的電影名更能引起中國觀眾的情感認同。四字短語的結構和韻律優點,有助于創造音律美和結構美。很多英語電影名的翻譯,譯者都注意到了中國觀眾的這種心理特點。例如,“Shooter”《生死狙擊》,“The Spy Next Door”《鄰家特工》,“The Reader”《生死朗讀》等等,都是巧用四字格的典范。
作為譯者,不論他承認與否,在翻譯的過程中都由某些規律引導。一些譯者力求在句式結構和表達方式上接近原作,一些譯者盡力使譯作通俗易懂。譯者的人生經歷、文化背景、認知心理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對原電影會有不一樣的理解,不一樣的表達。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譯名,這是因為譯者的主體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譯過程中起作用。
比較以下的例子:
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浮生若夢》和《你無法帶走》
Chocolate——《濃情巧克力》和《巧克力》
Waterloo Bridge——《魂斷藍橋》和《滑鐵盧橋》
Blood and Sand——《碧血黃沙》和《血與沙》
New Year's Eve——《緣滿除夕夜》和《除夕夜》
Twilight——《暮光之城》和《暮色》
Taken——《颶風營救》和《劫持》
對于同一個原電影名,不同的譯者給出了不同翻譯。在以上的例子中,第一個譯名比第二個譯名更吸引觀眾,因為第一個譯名不僅留下了懸念,給觀眾無限的遐想,而且巧用漢語四字格、五字格,更符合中國觀眾的心理。
四、結語
電影片名是一部影片的“窗口”,優秀的譯名是能經得住觀眾和時間的考驗的。在翻譯中,譯者既要忠實于原片內容,又要發揮其主體性,靈活運用翻譯策略,同時充分關注觀眾的期待視野,這樣才能使電影名具有“韻味”,使譯名產生強大藝術魅力和市場號召力。本文分析了譯者在英語電影名漢譯中的體現,得出了譯者主體性在英語電影名漢譯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譯者的核心地位。本文對于譯者在其它文本翻譯中的體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Berman Antoine.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M].Paris:Gallimard,Paris,1995.
[2]Gadamer,Hans-Georg.Truth and Method[M].London:Sheed
And Ward,1975.
[3]Nida,E.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Leiden:
E.J.Brill,1964.
[4]Robinson,Douglas.The Translator's turn[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5]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
司,2001.
[6]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J].中國翻譯,2003,(1).
[7]何躍敏.當前電影片名中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翻譯,1997,(4).
[8]李建盛.理解事件與文本意義——文學詮釋學[M].上海:上海譯
文出版社,2002.
[9]譚寶全.現代英語翻譯訣竅[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7.
[10]屠國元,朱獻瓏.選擇性順應與順應性選擇——佛教中國化進
程中的譯者主體性構建透析[J].中國翻譯,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