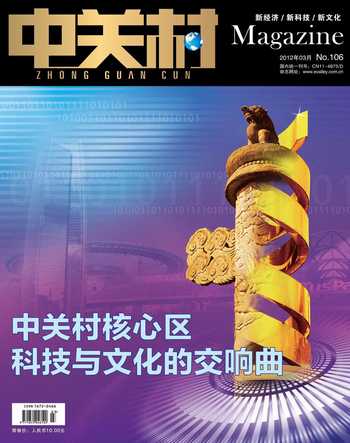江湖中國
王魯湘
中國人的“江湖情節(jié)”,源于許多人的自由之夢,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渴望自由。
連闊如,評書藝術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江湖叢談》是他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報紙上連載文章的集結,“文革”后曾以內(nèi)部資料出版,這次再版,說不上有多轟動,但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這確實是本奇人寫的奇書。連先生本是江湖中人,熟知江湖各種門道,卻又痛恨江湖上那些騙人的鬼把戲,覺得老百姓掙點錢不容易,被這些江湖騙子騙走,實在心有不忍,于是站出來揭露。今天,誰還有這個胸懷和膽識去體驗記錄這些東西?即使有,今日之江湖與一百年前那個江湖世界也已經(jīng)大相異趣了。
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分三大塊。一塊從中央政府到縣衙門,由層層統(tǒng)治者組成的上層官僚社會;一塊是縣以下,到鄉(xiāng)入村,由鄉(xiāng)紳治理的鄉(xiāng)村社會;這兩者構成了法律的陽光可以照射到的“白社會”;剩下的那塊就是所謂的“黑社會”了,也就是流動的江湖社會。江湖,是一個正統(tǒng)的法律管不著、宗法倫理夠不到的世界,鄉(xiāng)村社會的宗法倫理管束不住他們,國家機器的法律法規(guī)也難以罩住他們。江湖里的人過的是一種走街串巷、搭棚設點、跨州走府、經(jīng)商賣藝、放蕩不羈又流動不定的生活,彼此之間靠的是一種道義性、精神性的東西維系。表面上看起來游離松散、魚龍混雜,各個行業(yè)和門派的內(nèi)部卻有著自己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價值判斷系統(tǒng)。它們領地感、行業(yè)感都極強,組織結構不透明或半透明,所以在外人眼中充滿神秘。由于這個社會不透明,而且多半隱于地下和社會底層,所以謂之“黑社會”;又由于飄泊不定,來去無蹤,像水一樣,所以相對于扎根陸地上的士農(nóng)工商來說,謂之“江湖”。很多離奇、有趣、浪漫、夸張的事情發(fā)生在江湖,很多血腥、丑惡、駭人聽聞的事情也發(fā)生在江湖。江湖因此成為歷代文學作品描寫的一個重點對象,也成為許多中國人好奇、向往和憧憬的一個夢。
江湖不同于“白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自由。中國社會是按照一種超理性的儒家文化設計出來的超穩(wěn)定結構,不管是在官僚社會還是鄉(xiāng)村社會,人都被各種各樣的地緣、族緣、血緣關系所束縛、所羈絆。在朝堂,你要對皇帝盡忠;在家庭,你要對父母盡孝;你可能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死亡;你一生足不出鄉(xiāng)里,視野所及不過方圓幾十里而已。江湖社會就不一樣了,乘長風破萬里浪,來去自由。你可以逛遍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你可以擺脫先天賦予的許多義務,自主地選擇各種關系;你可以和我結拜兄弟、生死相隨,和他刎頸之交,卒相與歡;你在傳統(tǒng)社會里得不到、嘗不到、受批判、受壓抑的東西,可以在這里得到名正言順的認可、釋放與滿足。所以,江湖成了許多人的一個自由之夢,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渴望自由,哪怕它只是一種想象中的自由。
研究中國人“江湖情結”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假如我今日在大學教書,有充裕的時間,我想我會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當然,江湖的誘惑力不僅僅是自由,還有“義”。“白社會”以忠孝為先,“黑社會”的各個門派雖然也有自己的“小忠小孝”,但整個江湖道崇尚的卻是“義氣”。所謂“義者,宜也”,“義”既是江湖中人真實性情的流露,也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方式。“白社會”的忠是一種法律關系,官員忠于皇帝,忠于社稷,忠于職守,是一種后天的法律責任。“白社會”的孝是一種倫理關系,是先天的血緣義務。江湖道的維系卻只能以“義”。忠與孝不能選擇,義可以選擇,義是超法律、超倫理、超地緣、超族緣、超血緣的一種情感和責任,所以它能成為萍蹤不定、風流云散的江湖中人的心靈寄托,一種最高的生存方式,當然也是最終的生存意義。“聚義”是江湖道,“忠義”不是,江湖是自由人的集合,萍蹤俠影,聚散無定,唯有以義相感召,才能嘯聚群豪。所以,梁山水泊在晁蓋時代是江湖,山寨大廳所懸之匾大書“聚義廳”三字,宋江一心想招安,只想把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條好漢都帶出江湖,重新回到“白社會”的體系中去,但又不能太不顧忌江湖道義,所以費盡苦心改了一個字,變“聚義廳”為“忠義廳”,忠在義先,這個江湖當然就變味兒了。
江湖不同于“白社會”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它不要大一統(tǒng),厭惡大一統(tǒng),它堅決要維持維護的是一種松散的、自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組織結構。如果有一個野心家妄想一統(tǒng)江湖,一人稱霸,一定會遭到江湖豪杰的群起而攻之。許多武俠小說所寫的,無非就是這樣一種山頭林立、明爭暗斗、在統(tǒng)一和分崩之間拉鋸的江湖故事。
真正的江湖也許充滿了自由和義氣,但同時也是險惡和緊張的。江湖里的人活得都很小心,稍有不慎,就有血光之災。那些江湖老大,雖然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卻也要對手下負擔起吃喝拉撒、婚喪嫁娶、養(yǎng)老撫孤的重大責任,所以它又像一個家族。在中國,官僚、鄉(xiāng)村、江湖三個社會單元真正的組織原則只有一個,就是家族血緣式的宗法制度。從天子到臣下,從鄉(xiāng)紳到小民,從江湖老大到跟班兒嘍羅,模擬的統(tǒng)統(tǒng)都是家族式的宗法血緣關系,那個最有權威的人,同時也是所有人的大家長。
從古至今,組成江湖的是些什么人呢?一個重要部分是那些失地的農(nóng)民。人一旦被剝離了生產(chǎn)資料,就意味著他從傳統(tǒng)社會中被甩了出來,成為沒有組織沒有戶籍的“氓”,也就是流氓無產(chǎn)者。這種人有一個兩個不打緊,成千上萬的話,就成了李自成、張獻忠、朱元璋啊。所以,每個朝代最頭疼的就是這群人,碰到這種人就收編起來去充軍,去屯田。另外,為了根絕流氓無產(chǎn)者,歷朝歷代都要實行一個政策:反土地兼并。失去土地是造成農(nóng)民破產(chǎn)的最大問題,也是把農(nóng)民變成流氓無產(chǎn)者的根源。失去生產(chǎn)資料的農(nóng)民在社會的縫隙間流來蕩去,當時中國也沒有工業(yè)化,他們沒有辦法轉化為有組織的產(chǎn)業(yè)工人或城市市民,只有江湖可以容納他們,讓他們有點事干,有碗飯吃,同時有個松散的組織管著。一旦出了什么問題,有誰壞了江湖道義,還會有個老大站出來擺平。所以,歷朝歷代都會有江湖這個“黑社會”或“灰社會”存在,它與“白社會”形成一種有趣的共生關系。
在中國歷史上,江湖一直存在。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群體的動物,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不管傳統(tǒng)勢力達不達得到,不管法律管不管得到,他們出于自身生存、安全,甚至尊嚴的需要,就會自發(fā)組織。今天,在快速的城市化、工業(yè)化進程中,江湖社會又回來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nóng)民融入到城市里謀生,成千上萬的下崗工人在社會邊緣艱難地討生活,還有成千上萬因為出身、教育、健康、職業(yè)等各種因素被社會拒之門外的人,正彷徨無措、有意無意地與江湖擦身而過。于是,《江湖叢談》里所描述的那些千奇百怪、枝枝葉葉的江湖騙術似乎又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死灰復燃了,不過手段更現(xiàn)代化,形式更高級了而已。“打黑除惡”已經(jīng)成為公安部門每年的重要任務。只是,此江湖已非彼江湖,甚至也不是七十多年前連闊如筆下的那個江湖。那時江湖人公認的道義系統(tǒng)還在,現(xiàn)在這個江湖道在哪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