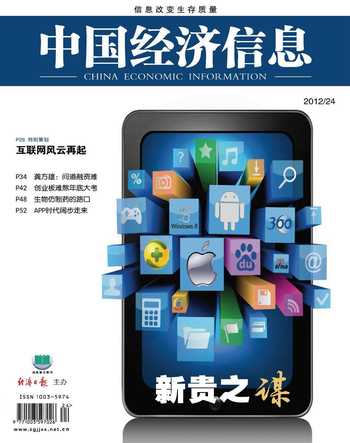消費你
靜博
粉絲多就代表絕對正確的邏輯,反襯的正是網民素質與道德水平的低下。對于網絡之群氓,能保持淡定最好。倘若認真,你必輸無疑。
普利策與赫斯特算是新聞界最牛叉的兩個先驅了。他們開創了便士報的時代,成為世界新聞史上的豐碑。但他們絕對想不到,他們所締造的“黃孩子”,經過兩個世紀的漂洋過海,已經在中國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黃孩子”原是奧特·考特所創作的著名連環畫系列,主人公為一僅有幾根頭發、沒有牙齒的小孩,穿著一件又長又大的黃色衣服,到處游蕩,發表觀感,在當時的紐約很受歡迎。
最初,“黃孩子”是普利策《世界報》的重要欄目,但赫斯特的《紐約新聞報》將奧特·考特挖走后,普利策在惱火之下聘請畫家喬治·拉克斯繼續在《世界報》續畫“黃孩子”。
一場爭奪“黃孩子”的戰爭在當時的紐約引起轟動,兩報借人們對此事的關注大肆策劃刺激性報道,爭奪受眾。彼時的《紐約客》的著名記者華德曼將兩報的煽情主義和嘩眾取寵的新聞報道風格戲稱為“黃色新聞”,并成為專門的新聞學學術用語。
敘述“黃孩子”,是源于對中國本土傳媒娛樂的耳聞目睹。從傳統的報紙、廣播和電視,到方興未艾的互聯網,各種層出不窮的媒介形式演變,讓黃色新聞的發展趨于泛濫。
制造者趨之若鶩,受眾則樂此不疲,這是娛樂泛濫的現實基礎。
一部新電影上映之前,往往會有一大撮極其吸引眼球的桃色新聞出現,類別大致可分為:
女主角和女配角爭風吃醋,一般大打出手;劇透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戲,一般離不開床;尺度越大,噱頭越足,一般情況下也是效果越好。近日,陸川執導的《王的盛宴》爆出使用水軍的新聞,讓中國電影節蒙羞。比之此前的傳統手段,電影營銷界看來也一直在與時俱進,并自欺欺人營銷手段發揮到淋漓盡致。
電視比之電影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標榜的都是服務與價值。大型生活服務類節目《非誠勿擾》上牽手一個女孩越來越難;堂堂的相聲大師郭德綱網絡上抄段子可以肆無忌憚;全中國的電視臺都在跳《江南Style》幾乎都不付錢;夢想類的選秀節目吸引眼球全靠一個字—“煽”;同一時段的電視劇從題材到情節千人一面……
的確,制造噱頭可以吸引眼球,一時的眼球經濟可以讓制造者一本萬利。然而,這卻是一條通往尼爾·波茲曼眼中的“消逝的童年”和“娛樂至死”之路。山寨者在借鑒與剽竊的搖擺中,制造著一堆一堆的文化垃圾,再強塞給沒有辨別力的受眾,結果可想而知。其實,把任何有關文化的產業做成娛樂,縱使不是中國人的原創,但絕對是中國人將其發揚光大的。把真實的東西秀得讓觀眾都以為是假的,本身就是很悲哀的事。
若干年前,所謂的營銷策劃大師找到退休教師兼網絡名人羅永浩,欲為其策劃其與芙蓉姐姐熱戀的新聞,為之拒。
時至今日,為了出名而炒作者此起彼伏。去掉所能去掉的所有遮羞布,為著名利的共同目標,消費著這個時代及身處其中的眾人。手段上,從當初的撲朔迷離到昭然若揭,從欲遮還羞到路人皆知,層出不窮的炒作伎倆,已然露骨到不要臉之境地。
苦就苦了那一小撮還有著正義感的受眾。你永遠不理解為什么被消費的大眾為何樂此不疲,更不理解娛樂大眾為何能成為一種趨勢。
粉絲多就代表絕對正確的邏輯,反襯的正是網民素質與道德水平的低下。對于網絡之群氓,能保持淡定最好。一認真,你就輸了。借用新聞界對于黃色新聞的定位,來警醒中國當前的傳媒娛樂的部分締造者與改造者:“他們投了一部分道德敗壞人的所好”。
如果要寫一部《中國娛樂之怪現狀》的編年史,相信2012年就不止幾百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