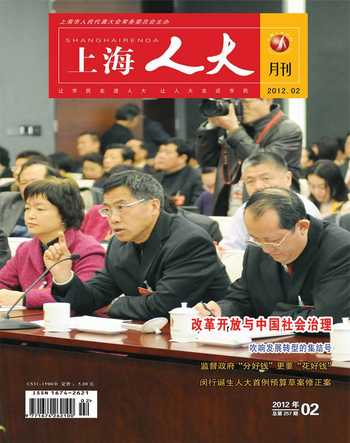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劇變之后是轉(zhuǎn)型
陳兆旺 胡德平


在風(fēng)云突變的二十世紀(jì),蘇東劇變無疑是若干沖擊巨大、影響深刻的重大歷史性事件之一。劇變發(fā)生后,即有“歷史終結(jié)”論者論及社會(huì)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zhēng)已告一段落,當(dāng)今世界已是自由民主一統(tǒng)天下之時(shí)。時(shí)過境遷,二十年后,如今的蘇東國(guó)家轉(zhuǎn)型境況如何?人們?nèi)绾握J(rèn)知和評(píng)判?蘇東劇變二十年的歷史變遷在我們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體系中地位如何,留有哪些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我們可以大致按照上述思路略作梳理:
市場(chǎng)、民主與福利需要合力推進(jìn)
我們?cè)趯?duì)蘇東劇變二十年進(jìn)行分析時(shí),可以大致區(qū)分出幾個(gè)相異的區(qū)域,但是無論是以市場(chǎng)、民主與福利中的任意一個(gè)指標(biāo)進(jìn)行測(cè)量,多會(huì)發(fā)現(xiàn)結(jié)果大致一致,也即這三者具有客觀上的相關(guān)性。當(dāng)然,其中更為深刻的理論與實(shí)踐問題在于市場(chǎng)化與私有化的推進(jìn)將無疑內(nèi)在地抵制福利性再分配,從而擴(kuò)大社會(huì)不平等,貧富差距擴(kuò)大化,如我們?cè)谄涓母镌缙谒姟6@ㄖ埔矊⒈厝辉黾迂?cái)政開支,影響勞動(dòng)者工作積極性,從而將拖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如我們?cè)谥袣W國(guó)家當(dāng)前所見的輕微的“福利病”。由此,市場(chǎng)化的階段性目標(biāo)設(shè)置與福利制度建構(gòu)等一系列矛盾,將考驗(yàn)政治家的智慧。當(dāng)前中國(guó)社會(huì)同樣面臨著這樣兩難選擇。轉(zhuǎn)型后的蘇東國(guó)家都要在民主的機(jī)制與過程中對(duì)這些問題加以辯駁與解決。而中國(guó)當(dāng)前同樣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即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發(fā)展的現(xiàn)狀使得福利建制變得日益緊迫,但是其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促動(dòng)還是阻礙倒是個(gè)深刻的理論與實(shí)踐問題。但是中國(guó)的優(yōu)勢(shì)在于,市場(chǎng)化逐步推進(jìn)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通過政府的合理調(diào)節(jié)與運(yùn)作,完全可以使得民生建設(shè)不影響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甚至推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
民主的績(jī)效與合法性的分合
民主狀況與程度在一系列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目標(biāo)設(shè)置與戰(zhàn)略選擇等關(guān)鍵性問題上影響改革進(jìn)程與制度變遷的速度與廣度。轉(zhuǎn)型前的民主與自由的許諾是誘人的,但是民主一時(shí)間仿佛并沒有帶來明顯的改觀,甚至帶來的可能是歷史性的倒退。制度變革一旦生效,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激進(jìn)式變革將不可避免地導(dǎo)致效率和福利的暫時(shí)性衰退。這些政治效應(yīng)將通過人們的感知與政治程序影響經(jīng)濟(jì)改革的具體政策甚至改革的進(jìn)程。但是,林茨等民主理論家的研究表明,民主的優(yōu)勢(shì)就在于,民主實(shí)踐使得人們可以把對(duì)民主體制的信任與民主政府或政黨的具體實(shí)踐相區(qū)分,即政治學(xué)行話“合法性與執(zhí)政績(jī)效”的區(qū)分。但是,民主體制不可能在一個(gè)經(jīng)濟(jì)衰竭、貧富差距巨大的國(guó)家中持續(xù)存活。而許多蘇東國(guó)家的民主體制的鞏固依然任重而道遠(yuǎn),而在民主過程中的低效率、腐敗、暗箱操作等多半也是難以在一時(shí)明顯改觀。當(dāng)然,民主的價(jià)值并非完全建立在執(zhí)政績(jī)效的基礎(chǔ)上,而是作為比較普遍的價(jià)值追求有其內(nèi)在的價(jià)值,這也是所謂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huì)主義,就沒有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內(nèi)在邏輯。所以,即使需要犧牲一定的經(jīng)濟(jì)績(jī)效而促進(jìn)民主體制的建立健全,那不論是人民還是共產(chǎn)黨,都會(huì)樂意為之。
當(dāng)局者與旁觀者
在蘇東問題的認(rèn)識(shí)上,我們有普遍的扭曲甚至歪曲事實(shí)的嫌疑,這也便是討論蘇東問題的難處之一。因?yàn)樘K東劇變對(duì)于社會(huì)主義實(shí)踐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挫敗,所以我們有時(shí)候不得不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其歷史的倒退性質(zhì)與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我們也大可參引蘇東國(guó)家的政客、學(xué)者和民眾的牢騷,從而佐證我們的觀點(diǎn)。其實(shí)正是劇變后的民主實(shí)踐使得人們的言論自由、現(xiàn)實(shí)披露與批判更為普遍。而作為旁觀者,我們應(yīng)當(dāng)充分尊重蘇東國(guó)家人民的選擇與歷史的選擇,他們自有自己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與身心體驗(yàn),我們多半是難以感悟的。今天看來,我們應(yīng)當(dāng)對(duì)我們自己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保有完全的信心,而無需太顧及他人,畢竟中國(guó)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jīng)漸漸走出了自己的社會(huì)主義改革與發(fā)展的康莊大道。
人民選擇、歷史責(zé)任與執(zhí)政黨
我們常常提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長(zhǎng)期執(zhí)政地位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這樣的政治邏輯在蘇東國(guó)家同樣體現(xiàn)。我們?cè)賮砜刺K東劇變二十年后的各國(guó)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境況時(shí),會(huì)不由自主地感慨萬(wàn)千。蘇東國(guó)家的共產(chǎn)黨在當(dāng)年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占有改革與發(fā)展的優(yōu)勢(shì),但是由于體制與思想的逐步禁錮,黨組織與黨員不思進(jìn)取,甚至走向腐敗墮落,以至于最終葬送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基本上都淪為在野黨,甚至在劇變?cè)缙谠S多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失去合法存在的空間。幾十年的執(zhí)政實(shí)踐頃刻間化為烏有,所謂的理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績(jī)效、人民政黨等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多多半淪為笑柄。而至今,許多蘇東共產(chǎn)黨依然難以擺脫歷史的包袱以在現(xiàn)行的政黨體制中健康成長(zhǎng),這或許已經(jīng)離當(dāng)年執(zhí)政共產(chǎn)黨的歷史抱負(fù)太遠(yuǎn)太遠(yuǎn)。如今的蘇東在野的共產(chǎn)黨是進(jìn)退維谷,如果不進(jìn)一步采取迎合民意和適應(yīng)國(guó)情的策略,很難在政壇上有所表現(xiàn)。但是,如果進(jìn)一步改革自身就意味著其將走上社會(huì)民主黨化的不歸路,從而就意味著共產(chǎn)主義的身份特征的逐漸喪失,對(duì)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而言,人民的歷史性選擇自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當(dāng)前的關(guān)鍵問題是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都應(yīng)當(dāng)時(shí)刻牢記歷史的教訓(xùn)、能夠?qū)θ嗣衽c歷史充分地負(fù)起責(zé)任,而不應(yīng)當(dāng)有任何僥幸心理,這便是共產(chǎn)黨執(zhí)政之難——人民與歷史不僅關(guān)注我們做了多少歷史性的貢獻(xiàn),同時(shí)也關(guān)注我們犯了多少歷史性的錯(cuò)誤,而我們又是如何面對(duì)并加以補(bǔ)救的。
大國(guó)崛起與國(guó)家影響力
從蘇東劇變后二十年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的歐盟為代表的歐洲經(jīng)濟(jì)、制度與文化對(duì)東歐諸國(guó)的吸引力。加入歐盟、融入歐洲是中歐國(guó)家、東南歐等蘇東國(guó)家夢(mèng)寐以求的理想與目標(biāo),并深刻地嵌入到改革的進(jìn)程與國(guó)內(nèi)政治過程當(dāng)中。中國(guó)道路的探索當(dāng)引以為戒,所謂的軟實(shí)力不在于大筆的援助和鋪天蓋地的形式化宣講,而在于制度與文明的認(rèn)同與實(shí)實(shí)在在的影響力。
蘇東劇變已過二十年,對(duì)其轉(zhuǎn)型全面客觀的認(rèn)知、反思與研究或許還將繼續(xù),而這對(duì)中國(guó)的發(fā)展也將是一筆彌足珍貴的財(cái)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