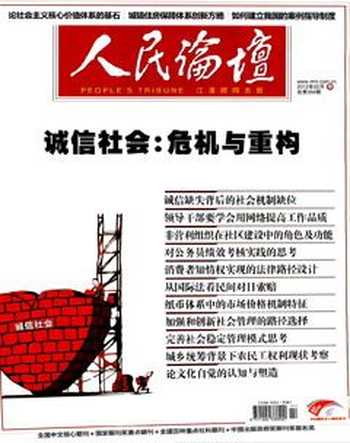試論我國居民訴求渠道的變化
馮希瑩
【摘要】隨著民生保障問題的深入研究和實踐,黨和政府對順民意、知民情、解民憂的認識日漸深刻。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居民的訴求表達渠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其表現為“單位性渠道”的核心地位明顯弱化、社區居委會組織在各訴求表達渠道中表現突出、宏觀的體制內渠道不斷拓寬、“微博”渠道異軍突起。
【關鍵詞】城市居民訴求表達渠道變化
隨著民生保障問題的深入研究和實踐,黨和政府更加重視民意表達渠道的建設,并多次公開對民意表達進行了集中闡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黨的十七大又強調“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可見,黨和政府對順民意、知民情、解民憂的認識日漸深刻,順應這種背景,我國居民的訴求表達渠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
“單位性訴求渠道”的核心地位明顯弱化
在“單位社會”背景下,社會成員生存和活動的方方面面都與單位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個“社會生活共同體”中,單位組織代表和維護其成員的利益。單位領導在解決內部成員收入分配、住房、子女就學等諸多問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單位性渠道,內部成員不僅可表達各類分散的個性化訴求,且不受時間、空間的局限。由于內部成員依賴于單位的各類資源,單位領導在解決各類矛盾、疏導其不滿情緒上具有一定的話語權,社會成員將“單位”作為訴求表達的首要渠道,“向領導反映問題”一度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語。
然而,隨著單位社會的消解,“單位性渠道”的核心地位明顯弱化。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后,對單位而言,最大的改變是將其所承擔的社會職能分離出去。加之,單位的用人制度從終身制轉向合同制,單位成員迅速從單位分離出來,成為社會人。大量的“單位人”轉為“社會人”后,國家通過單位組織對個人的社會控制、單位成員對單位的“依賴性人格”逐漸削弱,這導致“單位”在訴求表達渠道中的最重要地位開始松動。再者,“單位”中負責回應居民利益訴求問題的“工會”功能無法凸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單位性渠道”的弱化。“單位性渠道”的弱化導致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領域缺失了一種既便利又管用的訴求表達渠道。與此同時,廣大群眾了解公共決策、參與決策的需求和表達利益訴求的意識卻不斷增強,這在客觀上要求其他訴求渠道承擔起更多的功能。
社區居委會組織訴求渠道日漸凸顯
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大規模建立居委會組織的目的一是將“無組織”的居民“組織”起來,二是通過“單位”外的資源增加居民的福利。①居委會組織在生產自救解決貧困人口救濟問題上雖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相比單位性渠道,居委會組織在承擔訴求表達的功能上還相對弱化。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社會管理機制從“單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區制”,逐步走向以群眾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化道路。眾多研究表明,盡管社區公民社會的成長不是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全部,但社區自治已成為趨勢。近些年的實證調查結果顯示,社區居委會組織在“上通下達”,幫助群眾解決困難上逐漸得到了民眾的認可。2003年,陳映芳在上海市的實證調查中,②被訪者們被問及他們在遇到困難、矛盾、糾紛等問題時,居委會的利用率最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2000年以后,社區居委會逐漸成為了主要的利益表達渠道。而在2008年全國的社會支持網調查中,被訪者被問及生活中遇到困難,誰向您提供過幫助時,選擇“社區組織”的比例(17.8%)僅次于“家庭”(87.3%)、“家族宗教”(63.8%)、“私人關系網”(55.5%),明顯高于“工作單位”(15%)、“地方政府”(13.3%)、“黨組織”(12.6%)等組織和機構。③這組數據說明,社區組織已經成為民眾表達訴求的重要渠道之一。可見,“單位性渠道”弱化后,“社區組織”得到了群眾的充分認可。
宏觀的體制內訴求渠道不斷拓寬
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不斷調整,居民利益趨于多元,各類新的民生訴求不斷涌現,為了順應轉型期的形勢和要求,及時、合理地解決群眾的問題,各級政府不斷完善原有的民意表達渠道,居民對宏觀體制內渠道的應用也有所拓展,這主要表現為:
第一,城市居民通過人大代表表達意見、主張和要求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近些年,各級政府通過開展“代表接待選民日”、“選民座談會”、“人大代表進社區”等活動,將居民的意見和呼聲轉交至有關部門。有些群眾的呼聲對促進立法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例如2006年勞動合同法草案公布后,30日內征集到群眾意見191849件,成為改革開放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歷次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中收集意見最多的一次。④實踐證明,通過人大代表反映問題逐漸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常態。
第二,城市居民以各種形式參與聽證會,表達個人見解。我國政府于2004年10月26日第二次修訂通過了《國務院工作規則》,對“實行科學民主決策”進行了具體要求,規定各部門提請國務院討論決定的重大決策建議,必須以基礎性、戰略性研究或發展規劃為依據,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一般應通過社會公示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意見和建議。⑤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上,部分城市居民通過參與聽證會,將基層的聲音傳遞上去。盡管目前我國的聽證會制度還不完善,但聽證會制度仍然讓權力的運作更加開放透明,國家在出臺重大決策的過程中也更注重傾聽普通百姓的聲音,使普通居民參與決策的渠道更為順暢。
此外,各地政府增加的“人民建議征集”、“領導干部大接訪”、“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公安大接訪”、“法律援助”、“政法系統工作站”、“群眾涉法訴求工作站”等類似渠道如雨后春筍般陸續涌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很多群眾的利益訴求問題。
“微博”成為民眾訴求表達的新渠道
隨著電腦普及和現代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中國社會步入了生活網絡化時代,其明顯特征之一即是“微博”的崛起。實踐表明,“微博”已成為新聞輿論的重要源頭,由“微博”引發的社會熱點事件受到了廣泛關注,網民的聲音對推動有關社會熱點事件的解決起到了強有力的作用。
第一,單位性渠道弱化后,民眾在日常生活場域中缺少一種可隨時表達意見的渠道,而“微博”自身的技術特色和影響力,恰恰可使民眾不受時空限制,不受其他因素阻礙,隨時隨地地表達意見和情緒。布迪厄將技術和制度概括為制約公共話語權的兩個主要因素,而技術遵循的是“理性”邏輯,會在某種程度上對制度進行改寫。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微博”將互聯網和移動網絡(手機)結合,實現了互聯網與無線終端嫁接后發送信息的功能。這些變化使作為“新訴求群體”的不少網民開始漸漸擺脫對傳統網站、專業媒體提供信息的依賴,主動出擊,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可見,技術優勢為其成為新興訴求表達渠道提供了基本保證。
第二,“微博”的高使用率加速了民眾訴求信息的流通,讓更多的民生和民意訴求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在廣大的“微博”用戶中,每個民眾均可扮演“公民記者”的身份,這打破了新聞媒體的絕對領導權和話語權。無論是明星微博、意見領袖微博,還是那些因機緣而引發“圍觀”的草根微博,其對新聞事件的現場直播以及互動群體“病毒式”傳播,都改變了傳統的媒體生態,吸引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眼球。
第三,“微博”信息的公開透明形成了強大的社會監督力量,再加上其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使諸多棘手的民意訴求得到了快速解決,強化了“微博”渠道的作用。“微博”興起前,人們曾經將新聞輿論表現出來的社會監督力量視作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使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輿論監督力量進一步放大。網上網下輿論的疊加,也加大了輿論監督的影響。在網絡虛擬世界中表達的社會態度、有關民計民生等切身利益問題均需要回到真實世界中加以解決。與以往任何一種網絡表達載體相比,“微博”顯示出在最短時間內形成最大的社會關注度和輿論浪潮的能力,推動了利益矛盾的解決。
“微博”使網民隨時隨地表達意見,它的高使用率加速了信息的流通,讓更多的民生和民意訴求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改變了傳統訴求表達渠道的固有格局,但是由于缺少“把關人”,“微博”所表達的某些非理性訴求或情緒遭到了惡意擴散,引發了諸多社會負面影響,這也值得注意。(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后;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輿情疏導機制建構與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號:11CSH059)
注釋
①韓全永:“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是如何在全國建立起來的”,《社區》,2006年第6期。
②陳映芳:“貧困群體利益表達渠道調查”,《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6期。
③數據來源于李培林2011年4月在天津市委黨校所做的《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講座紀要》。
④畢宏音:《訴求表達機制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第132頁。
⑤《國務院工作規則》,www.gov.cn,2005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