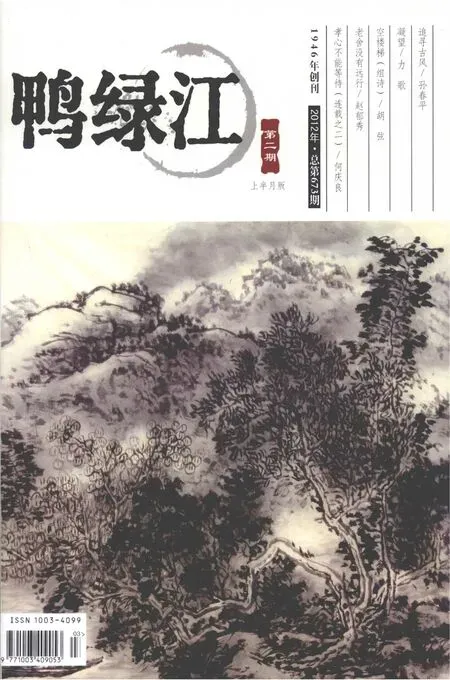老舍沒有遠行
趙郁秀,女,滿族,編審。1933年10月生于丹東。1953年入北京中央文學院研究所(現為魯迅文學院)二期學習。1955年秋,任遼寧省作協編輯。現任遼寧省作家協會顧問、亞洲兒童文學學會副會長、遼寧省兒童文學學會會長。建國前開始發表、出版文學作品,作品達百余萬字。其中,《黨的好女兒張志新》《為了明天》等獲過省及省以上多種獎勵。2006年于韓國漢城召開的世界兒童文學大會上獲“功勛獎”。1993年始享受國務院的專家特殊津貼。
獨抱寒衾忍不眠,長思死別廿九年。
愛國忠誠如烈火,舍家抗戰兩地牽。
相親相諒又生路,似血似淚斷續篇。
默視無言心寧靜,為民樂業力爭先……
這是人民藝術家老舍夫人——著名畫家胡■青的詩賦《憶老舍》。1984年春,老舍85誕辰(1899年2月3日)時,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了有彭真、習仲勛等諸多國家領導人和專家、文友出席的隆重紀念大會,會上,胡■青代表全家宣布,將老舍故居、書稿、字畫等全部捐獻給國家,后賦詩述懷。
當年,這深情的述懷,曾使我心靈震顫,久久沉思。思起上個世紀50年代我聽老舍先生講課,畢業時又送行、合影的一幕幕;思起60年代我到鞍山湯崗子溫泉療養院拜見在這里療養的老舍先生,聆聽到他的肺腑真言,看到他的全家福照片的一幕幕。那時方知他的夫人胡■青不僅是畫家,還曾是文學教授,師從錢玄同大家。今天,她同老舍“長思死別”、“似血似淚”歷經的苦難,不僅使我震撼、崇敬,更想尋機拜見這位倔強的滿族長者、偉大女性。
幾年后,我有幸因主編《五彩的園圃》一書進京領取第二屆冰心兒童圖書獎,頒獎臺上在座的有雷潔瓊、葉君健、楊沫等名家,為我頒獎的正是我曾深深同情、敬仰的胡■青老人。頒獎儀式后同她并座暢談,使我理解了老舍夫婦這一滿族家族不僅如巴金所贊“他的全部作品都貫穿著一根愛國主義的紅線”,而且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始終展現了“愛國忠誠如烈火”的風范。
老舍出生不足一歲半,其父親、一位滿族護軍,便在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戰死。聯軍挺進京城,洗劫燒殺,搶走老舍家的衣物后,還將空空的木箱扣到了正在襁褓中熟睡的老舍身上,使其幸免未像他家的黃狗一樣被鬼子一刀刺死。這尚不黯世的嬰兒心靈怎能不刻下殺父之仇,怎能不燃燒忠誠愛國保家的烈火。“五四”運動后的1922年,在南開中學的“雙十”節紀念會上,青年學子舒慶春(老舍本名)激情演講:“我愿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我們既要為破壞和鏟除舊世界的惡習、積弊和有毒的文化而犧牲,也要為創立新的社會民主和新的文化而犧牲。”在他父親負起一個十字架后,老舍發出了這樣誓言。
但是,這一正紅旗下精忠愛國的滿族父子,負起十字架獻身后的骨灰盒里都沒有留下他們的忠骨骨灰。父親舒永壽木盒里裝著的是他拋于戰場的血跡斑斑的布襪子和生辰八字。而存于北京八寶山公墓的老舍的骨灰盒里,裝的是先生筆耕用的眼鏡、鋼筆、毛筆,和他最喜愛的美麗的茉莉花。(當年“四人幫”指令“不得保留骨灰”)
這位新中國成立后最早被授予“人民藝術家”之稱、深受人民崇敬的老舍,于1966年“文革”風暴乍起的8月,因不忍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屈辱,獨自走向同他母親祖居僅一墻一水之隔的太平湖,投入了一生含辛茹苦撫養他長大成人、將寧折不彎的剛烈性格傳給他的敬愛母親懷抱。“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
人杰老舍,沒有留下骨灰和遺言,卻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愛國主義紅線足跡。三十年代初,老舍從英國任教歸國,同胡■青女士完婚,夫婦在山東任教、講學、生子,自稱“樂安居”,創作走高,《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等四五部長篇及短篇集相繼問世。抗戰炮響,揮淚擱筆,舍妻撇子投入抗戰洪流。“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1937年11月,老舍獨自徘徊抵漢口,馮玉祥將軍親接到他家下榻。當時馮將軍大力提倡高唱抗戰歌曲,曾請陶行知之子到福音堂等地教歌,老舍立馬隨之而行,同時運用快捷的鼓詞、相聲等通俗文藝形式創作并親自表演,及時向群眾宣傳抗戰。他連夜寫出的《丈夫去當兵》(張曙作曲)“抗戰洋片”等,在群眾中得到極大反響,被普遍傳唱。他曾說“在戰斗中槍炮有用,刺刀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魯迅先生說過“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佛羅培爾的。”(《論“第三種人”》)
1938年3月,周恩來在武漢組織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推舉老舍為主席。從武漢到重慶,奔波中,老舍一直全力以赴做好“文協”工作。1939年,老舍還率領一個有二三十人的作家戰地慰問團到前線慰問,團員中有東北作家羅烽、白朗等。女作家白朗曾向我講過,他們訪問團從重慶出發,經陜、甘、寧、河南等15個戰區,遭敵機三四次轟炸,險些喪命,歷經164天,槍林彈雨中長途跋涉,慰問“苦斗戰士”。是年9月到達延安,得到熱烈歡迎,毛主席設宴招待,老舍同毛主席、朱總司令并肩而坐,舉杯同飲。老舍還即興表演了京戲清唱,表達了萬眾一心、勇猛殺敵的真情。這是老舍第一次同久仰的毛澤東親切會面交談,他無比欽佩,說:“毛主席五湖四海的酒量,身后有億萬群眾哪!”事后他寫了一首歌頌延安的長詩《劍北篇》,當年《新華日報》給予高度評價,可謂是最早的延安頌。他曾被朱自清譽為“使詩民間化”的“抗戰詩壇”代表作。
新中國成立,老舍曾立誓“為創立新的社會民主和新的文化”的新時期到來,肩負這一十字架,勤奮創作,兢業工作。他操勞過度,身體不適。1962年,得周總理關懷、安排,老舍到鞍山湯崗子溫泉療養院療養。遼寧省作協得知,特派我前去看望并約稿。
那天,我下了火車徑直來到老舍的房間。他的房間同我曾看望過的鞍山市長同作家陳■寫回憶錄時住的房間一樣,一床一桌、兩木椅,不過老舍的桌上有一酒瓶,插著各色野花,發出幽幽清香。那時沒有買花、獻花風氣,但我已為自己兩手空空冒然到來有些發窘。而老舍卻熱情地直說:“我來時一再表示不要同當地打招呼、不要驚動人家,我就是一個普通療養員嘛!”
為了打破僵局,我表達了遼寧作協對他的問候后,告訴他,我在北京文學研究所學習時聽過他講課,講的是文學語言問題,關于如何從生活中提煉語言的精辟論述,至今我仍記憶猶新。畢業合影時,先生還曾大聲熱情囑告:扎根群眾,勤學苦練!我邊說還邊學著他當年手杖拄地、高高揚手的姿態。老舍哈哈大笑起來,說:“那是在鼓樓東大街,一個朱漆大門院里吧?我這人,一看見青年朋友就想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嘛!”于是我又講起抗美援朝時我在丹東,老舍先生曾隨以賀龍為團長、他任副團長的赴朝慰問團到過朝鮮前線。以后我讀到了當時很轟動的他的長篇《無名高地有了名》。記得當年有評介說,老舍堅持在朝鮮前線半年有余,同志愿軍戰士同吃同住,并要爬到被志愿軍英雄頑強攻破的,敵人稱為“最堅固的陣地”的老禿山高地去親自看看,戰士們要背他上山,他堅決不依,硬是自己拄杖一步一喘攀上山頂。后寫出了有開創性的軍事題材長篇。
老舍聽我說完嘿嘿笑著說:“你這小同志記性眼挺棒啊,那《無名高地有了名》是我第二部寫兵的長篇。”我馬上插話:“第一部是抗戰時寫的《火葬》吧?”
老舍點點頭,回憶似地說:“這第二部真勝過第一部喲,我在朝鮮前線和戰士一起蹲坑道,聽炮聲,那一平方多米的禿山頂上竟落了一千多發炮彈,那真是英雄戰士,英雄陣地,我兩手撲地爬也要爬到山頂去,若不怎么能產生《無名高地有了名》呢!那半年多的火煉,煉了身體,煉了靈魂……”
他的掏心窩的話,使我聯想到我親歷的抗美援朝的炮火,想到從他作品的炮火硝煙中展現出的“可愛戰士”、“頗有學問的”指揮員們那機智勇敢、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他是“北京味”權威,也可稱“火藥味”的“勇士”。他惟妙惟肖、活生生地寫出的北京平民和“最可愛的人”的形象,都能經得起滄海桑田歷史時光的考驗。同時,他筆下還有膾炙人口的旗人、藝人……記得當年在《龍須溝》上演之前,有一出轟動京城的話劇《方珍珠》,是寫一女藝人故事,好像還拍成了電影。此劇容易使人想到著名評劇演員新鳳霞。我突然冒然問老舍先生:“聽說新鳳霞和著名作家吳祖光結婚是您給介紹的,還是主婚人,是嗎?”
老舍微微一笑,沒點頭也沒搖頭,給我講了一個當時我感到非常新奇有趣的故事。
1950年3月,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選為理事長,老舍等為副理事長。他很重視這個職務,立馬帶人到北京天橋去視察。十四五年前他在北京時,常到這個藝人聚集的地方。現在舊地重游,一切都感到新鮮。天橋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一小客店,掛著新鳳霞的大照片,有人打著鑼鼓吆喝:
新鳳霞唱戲在萬盛軒,一毛錢就能看一天。我店離萬盛軒真不遠,看戲回來請住我店,大通鋪衛生還省錢……
老舍果然去看了新鳳霞的評劇,回來便想在這能躺十來人的大通鋪上睡一宿,第二天還看。陪同人員堅決不同意。他只好交了宿費,坐著閑聊一陣。正巧遇一人來募捐,說是有一花旦演員得了重病,“戲迷”們有人捐錢,幾毛或幾元錢。老舍打開錢包拿出20元人民幣。那人深鞠大躬,要留下他的姓名地址,老舍說自己是賣野藥的,名叫龍套。從此老舍和新鳳霞的劇團也有了些聯系。對吳祖光,老舍是在重慶時結識的。吳祖光工作的《新民晚報》首發了毛澤東的《沁園春》,國民黨要追捕他,他逃至香港,后來到北京。老舍率吳祖光看新鳳霞的評劇,他們一見鐘情。1951年他們結婚,欲在酒店辦婚禮。但當年這樣大的舉動很少,便聲稱辦“雞尾酒會”。當時可能有人不懂“雞尾酒會”,或故意幽他一默,來赴宴的侯寶林等還真的抱一大公雞、要割雞尾祝興。老舍在酒會上講了話,周恩來總理還發來了賀喜電……
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情趣。隨口說:“您可寫篇很有趣的散文。”老舍搖頭說:“咦,使不得,寫不得……”
我理解了,那個年代是不宜發表此類散文的。我鄭重問了一句:“先生,您手頭還有朝鮮的戰地隨筆或寫北京的散文嗎?”說著遞上了我帶去的我們的文學雜志。
老舍先生翻翻雜志,直率地說:“噢,派你來是向我約稿的呀!”他沉思下,慢慢說:“現在辦雜志都要反映現實生活,我現在可不能像當年那樣爬山走路嘍,出門步步離不了拐杖,在北京每天最低還要吃個雞蛋吧,能同群眾同吃同住嗎?不真正深入工農兵生活,哪能寫出您們期望的、反映工農兵現實生活的好作品呢?”
這一番話,使我有點吃驚,我覺得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家同我這無名小輩發出如此肺腑之言,在當時是難聽到的,這真是一位掏心窩、講真話的光明磊落的真實老人。我不知該如何回答。但,這番真話使我更失去了拘束感,同老人隨便閑聊起來。
當我聊到曾聽女作家白朗說過,馮玉祥將軍曾有一首打油詩“老舍先生到武漢,提只提箱赴國難,妻子兒女全不顧,赴湯蹈火為抗戰”時,老舍先生笑笑,長嘆一聲說:“那時可苦了他們母子三四口之家了。”說著,順手從一個書本里抽出了一張他們的全家福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夫人胡■青的形象,高高的身材,眉清目秀,文人氣質,滿族格格。老舍告訴我,她燒得一手好菜,還能親自給他裁制綢料衣衫和皮袍子,是賢內助。但,他們不門當戶對。老舍出身于滿族底層貧民,除他,自祖輩下數,家里沒有一個識字的。而胡■青的父親,是滿清伊姆佐領、三品大官。不過他們能結成姻緣也是因為有緣分,他們都是父母膝下的老疙瘩,老舍出生時,母親41歲,胡■青出生時,父親已64歲了(母親是父親的三房夫人)。因為都是老疙瘩,掌上明珠,都讀書上進。胡■青考取師范學院時,班里只有三個女生,她苦讀到大四,便能在邵飄萍主編的《京報》副刊上發表散文小稿了。所以,她一直任語文教師,是老舍的得力助手。因她小時隨母親描紅繪畫,解放后師從齊白石老人,成為國畫大家。
這一天,可能因為在療養院老舍獨居一室,少有談話對象,也可能因為我曾是他的忠實學生和讀者,使他熱情親切如我的家長一樣開懷暢談,也使我了解了老舍和夫人兩個滿族家庭的演變,更體味到他的作品中曾被魯迅先生稱贊“地域特色頗濃厚”的十足京味和滿族旗人的獨特性情和風格。他筆下常常現出的“淚中有笑,笑中有淚”的幽默、悲涼的場景,正是滿族衰敗、人民崛起的時代特征。清末民初滿族沒落,失去了“皇糧”、“俸祿”,生活無著,只好拾起游牧時代的歌舞特長,靠吹拉彈唱,以詼諧、幽默排解心中郁悶。老舍自幼也便得到這通俗文藝的熏陶,在幽默、詼諧、樂觀中滋生了要改變命運的堅毅、自強、抗爭奮斗精神。他的作品是他親歷、熟悉的生活的再現。正如英國學者卡萊爾對莎士比亞的評語:“它通過他高貴真誠的靈魂茁壯成長于自然的最深處,是自然的聲音……就像一棵橡樹從大地的懷抱中成長起來。”坐在我面前的這位真誠老人,就是扎根于大地、不斷發出自然的聲音的高大橡樹!
當我同老舍先生告別時,他手拄木杖起身,一定要把我送到火車站。那時療養院所在地是農村小鎮,去車站是沙石土路,火車只停一分鐘。我一再勸他停步或我扶送他回去,他堅持不依。當發現路邊有野花搖曳時,他又駐足哈腰采下幾株野花送我。我馬上想到護花之神的美譽,老舍大師乃真、善、美的化身!待將來我有機會去北京再拜見先生時,我一定買束他喜愛的鮮花贈獻先生(已為終生遺憾了)。我手持鮮花扶先生一步一步過鐵路到車站。匆忙上車、火車開動后我向他招手,隔窗望著他一手拄杖,一手向我揚手的身影漸漸遠去。我不由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他雖不是“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但確是“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顯出努力的樣子”,“慢慢”行走。那拄杖揚手的身影,正是在“晶瑩的淚光中”遠去,“我最不能忘記的”父輩的“背影”,迎風挺立的高大的橡樹。
一個月后,老舍寄來一篇題為《學生腔》的短文,談的還是文學語言問題。(刊發于《鴨綠江》1962年10月號)他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循循告誡讀者要“思路清楚,說的明白,須經過長時間的鍛煉,勤學苦練是必不可少的”。這后一句,正是當年他囑告我們的掏心窩的話,也是語言大師老舍的終生體驗和忠告。他的語言來自生活、來自民間,精彩、生動、凝練,又富有詩意,可謂爐火純青。
以后我讀到了老舍的《正紅旗下》,正是他浸透半生心血,醞釀、構思出的真正的文學,自然的聲音,滿族文學的扛鼎之作。他以濃墨重彩展現了清末民初滿族及中國社會的風雷激蕩的歷史畫卷,展現了滿族文化獨特風采和歷史表現力。遺憾,我們讀到的只是長篇開頭的11章8萬字,僅寫到小主人公的誕生和童年。我們冀希他的成長,我們等待讀下去。但是,我們再得不到這藝術的享受,領略不到這部經典歷史教科書給予我們的深邃思想了。老舍先生在正紅旗下肩負著兩個十字架,痛苦地放下了他的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巨筆。這支筆和那香氣不絕的美麗的茉莉永遠在他的骨灰盒里放香,讓我們深深記憶這支筆給我們留下的閃耀著民族光輝的文化遺產,給予我們世世代代吸取不盡的永恒力量和美的追求。老舍先生仍拄著手杖、幽默地、親切地、頻頻地向我們招手,如高大橡樹挺挺站立。大師,沒有遠行!
責任編輯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