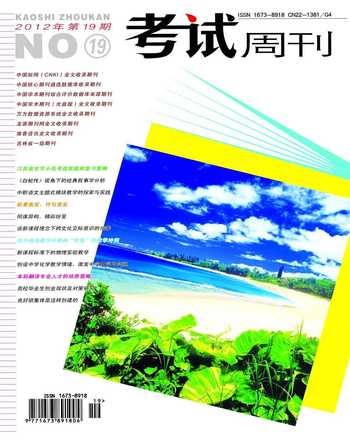老師,你OUT了嗎?
白麗
“OUT”原意“向外,在外”,當(dāng)下,這個詞被賦予了“落伍”的新意,成為時尚達(dá)人的口頭禪。有時我在想:轟轟烈烈的新課改之后,素質(zhì)教育貫穿始終的新課標(biāo)之下,我們授課時的舊理念,舊作為是否已成為學(xué)生眼中的“古董”?
片斷一:
師:政壇“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從小受到嚴(yán)格的家庭教育,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力爭一流,“即使坐公共汽車,你也要永遠(yuǎn)坐在前排”。同學(xué)們,聽過瑪格麗特的故事,你們受到怎樣的啟示?
生:“永遠(yuǎn)坐在前排”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
生:真OUT!我討厭那些永遠(yuǎn)都要坐前排的人,機(jī)會是大家的憑什么你永遠(yuǎn)坐前排。坐公共汽車也爭前排,要我才不呢,坐前面危險!
師:嗯,這個見解角度新穎,有個性。
分析:閱讀教學(xué)中允許并鼓勵學(xué)生大膽說出自己的獨(dú)特見解是新課標(biāo)中明確規(guī)定的,然而我們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偏離了這一點(diǎn),總希望學(xué)生想我們所想,說我們所說,牽著學(xué)生在我們設(shè)計好了情境里機(jī)械式地反饋信息,最后達(dá)成“共識”便萬事大吉了。
對策:現(xiàn)代社會,學(xué)生的個性越來越強(qiáng),如何針對學(xué)生的個性展開教學(xué),教師除了要有博學(xué)廣智的素養(yǎng),還要有海納百川、求同存異的氣度。教學(xué)中不妨多設(shè)置一些可以并需要拿出不同觀點(diǎn)的內(nèi)容,相信真理是愈辯愈明的。
片斷二:
生:老鼠怕貓,這是謠傳。壯起鼠膽,把貓打翻。
生:哈哈,有本事你接著喊,看“老貓”來了一口吃了你不。
師:剛才是誰在大喊大叫?挺押韻的嘛,但結(jié)構(gòu)不夠工整,充其量是首打油詩。而今天我要學(xué)白居易的《錢塘湖春行》是一首七言律詩。你們知道打油詩和律詩的區(qū)別嗎?
生:一俗一雅,嗯,打油詩通俗易懂,貼近生活。
師:大家說的沒錯。打油詩多為百姓作品,貼近生活,不太注重字?jǐn)?shù)、對仗、格式、音調(diào)的工整,文學(xué)色彩不濃。而律詩在字?jǐn)?shù)、押韻、對仗方面要求比較嚴(yán)格,具有很濃的文學(xué)色彩。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研究一下白居易的七言律詩——《錢塘湖春行》。
分析:如果對課前學(xué)生的哄笑置之不理,那么學(xué)生會把這種興奮帶入課堂,天馬行空的思緒很難回到正題上來;如果對學(xué)生的惡作劇尖酸刻薄地指責(zé),那么學(xué)生會帶著壓抑的心情去面對這節(jié)課,教學(xué)效果可想而知。
對策:接著學(xué)生意猶未盡的話題,順勢引出本節(jié)內(nèi)容,既突出了重點(diǎn),又突破了難點(diǎn)。我們常說“教師是主導(dǎo),學(xué)生是主體”,我認(rèn)為實踐中過度關(guān)注這個問題會迷失教育者自我,過于恍惚又會錯失教育的最佳時機(jī),閑庭信步的姿態(tài)才會使教育者永遠(yuǎn)立于不敗之地。
片斷三:
生:“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該生邊搖頭晃腦地讀著,邊用筆挑起前座女生的馬尾辮。)
生:你有病啊,討厭!
(前座女生回過頭來狠狠地瞥了這個男生一眼。)
生:切!你也算“窈窕淑女”?自從你坐我前面我上課都不敢睡覺了,因為你的長相很提神!
生:呸!你也算“君子”?后現(xiàn)代產(chǎn)物!
生: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
師:你說她不算“淑女”,她說你不夠“君子”,那在你們心目中怎樣才算“淑女”和“君子”呢?
生:淑女呢,要安靜但不內(nèi)向,好看還得有思想。
生:不是說“君子博學(xué)”么,沒文化、素質(zhì)低能算君子嗎?
師:要是這樣衡量起來,剛才那兩名同學(xué)的拌嘴也不無道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它不單單是用來度量別人,更多的時候是用來度量自己。雖然,我們離“淑女”和“君子”的標(biāo)準(zhǔn)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這段距離是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去縮短甚至消除的。
分析: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往往會具有狹隘、嫉妒、憂郁、自卑等負(fù)面心理,時而沉默寡言,時而張狂躁動,戲弄別人是他們常用的發(fā)泄手段。這一時期男女生是懵懵懂懂的,這種懵懂會造成兩種極端,要么互相吸引,要么互相排斥。吸引的有可能發(fā)展成早戀,排斥的見面就掐架,處處要PK。
對策:時代在飛速發(fā)展,新思想、新風(fēng)尚、新標(biāo)準(zhǔn)、新元素層出不窮,若要拉近與學(xué)生之間的距離,我們勢必要接受一些他們的“文化”。有時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看問題,會讓復(fù)雜的問題簡單化。用向下45°的俯視換來學(xué)生向上45°的仰視,這樣的崇拜無意義。
教育像湘繡,針法千變?nèi)f化,但極富表現(xiàn)力的物象不是最后的極致,刻畫內(nèi)質(zhì)才是登峰造極之作,只有用心的教育才能刻畫出學(xué)生內(nèi)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