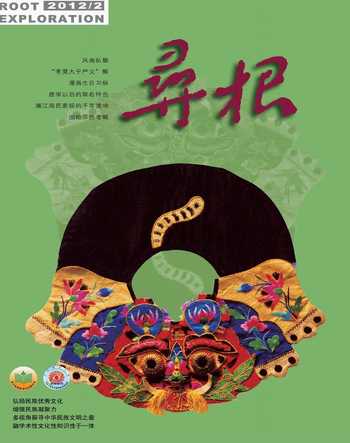從《泡沫》到《浪花》
余冰
《泡沫》是泡沫社的刊物。1935年下半年,北平出現一個由文藝青年成立的泡沫社,呂夔龍、王云和辦了個小報《泡沫》。每期為對開單頁兩版,不定期出版,后改為月刊,共出4期。1936年3月,《泡沫》被軍閥宋哲元查禁。
泡沫社的骨干力量在《泡沫》被封之后,又組織了浪花社,成員有北大、清華等校學生和部分中學生,共一二百人。他們創辦了《浪花》文藝月刊,同年6月15日出版。從“泡沫”到“浪花”,意在象征革命大潮的發展。但《浪花》出了兩期,即被當局查封。
泡沫社和浪花社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文藝團體組織。《泡沫》和《浪花》是北方左聯的刊物。1935年11月,中共決定健全北方左聯,谷景生任書記,楊彩(北師大學生,筆名“史巴克”)任宣傳委員,擔任組織委員負責聯系一些學校的進步文藝團體、主管《泡沫》《浪花》的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
當年浪花社成員、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碧野(1916~2008年),原名黃潮洋,廣東大埔人,40多年后回憶:“記得當時我以我的父親為模特兒寫了處女作《窯工》投給《泡沫》,《泡沫》編輯部約我到東城去見面。那時我住在南城,徒步十里前往,到達地點一看,原來那是一個十分破落的院子,殘磚碎瓦,平房低矮。接待我的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個年青人,但見面時他卻給我一個比較成熟的印象和一種親切感。這個人是誰,現在記不清了。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谷牧同志曾經是該社的主要負責人。”(《〈泡沫〉碎屑、〈浪花〉點滴》)
谷牧(1914~2009年),原名劉家語,山東榮成人。1934年8月從家鄉到北平。他擔任北方左聯領導的時間不到兩年,以后就到東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了。
浪花社的主要成員有:《浪花》主編魏伯(1914~1984年),原名王經川,另有筆名王韋、王路、瑋路等,河南汜水人,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國防工辦主任,中國文聯秘書長。魏東明(1915~1982年),祖籍浙江紹興,生于天津,清華大學外語系學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湖南大學副校長、湖南省文聯主席等職。柳林,原名王勁秋,河南人。呂熒(1915~1969年),原名何佶,安徽天長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亞蘇,山西人,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學生,浪花骨干中的一位女性。
碧野在回憶錄《三人行》中生動地畫出了“魏伯的風格”:“老家豫西,生來就像黃土高原似的粗獷、純樸厚實”;“魏東明的風貌”:“精力飽滿,熱情奔放,不修邊幅,頭發亂蓬蓬,像一頭獅子”;“亞蘇的風采”:“容貌美麗,身材苗條,外表文質彬彬,完全是個漂亮小姐,但內心火熱,她的生命在為革命燃燒。”
谷牧回憶,1976年后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秦川、國家建委副主任的宋養初、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當年都是泡沫社、浪花社的成員。著名導演夏淳也是《泡沫》《浪花》的忠實讀者。
谷牧初到北平時,一度成為北平圖書館的常客,也寫小說和小品文。刊登在《泡沫》上的《海上的斗爭》《剿匪》等,都是這時的作品,用的筆名主要有谷牧、牧風、曼生、曼、子穎、景希。他說:“作為一個文學青年,當時的作品是不太成熟,而且在找到黨組織之前,有的作品帶有賺稿費糊口的性質,所以我并未支持學者編我的作品集。”(《谷牧回憶錄》)
《浪花》第一期中的小說有李蕤的《掘坑兵》、宋昕的《石碣村》、余一谷的《孩子們的疑問》;散文有默丁的《引(救亡速記之二)》;詩有魏東明的《陶真這孩子》、王蕪林的《五月》;散文詩有魏伯的《我要走》以及譯文多篇。1936年8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小說有碧野的《一枝搶》;報告文學有宋昕的《六一三》。這一期有“紀念高爾基逝世特輯”,內有夢宇譯的《高爾基的生平和作品》,丹朱譯的《高爾基的奮斗史》,堯生的《紀念革命文豪高爾基》,另有高爾基的《新的太陽》(朱健翻譯)。從題目上讀者就可以感受到時代的氣息。谷牧說,當時還是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的袁寶華,曾在《泡沫》上發表描寫河南民工挖河的詩:“泥水里忍不住饑腸萬轉,淚泉模糊了我困乏的雙眼。命運的惡浪沖擊著生活的漏船,從心底我暗自咒罵昏聵的老天……”典型地表現了《泡沫》和《浪花》這類左翼文學青年刊物所追求的普羅文學的風格。
《浪花》出版時,谷牧被捕入獄。“魏伯巧妙地把新出的《浪花》送入獄中,谷牧在鐵窗下讀到《浪花》,立即敏銳地判斷這是《泡沫》的續刊。他知道戰友們仍在繼續作戰,喜不自勝。”(碧野:《人生的花與果—我的生活道路和創作生涯》)
谷牧在《谷牧回憶錄》中說,剛出獄,就接到上級黨組織的通知,要他去北京大學參加一個討論文學方向的集會。谷牧到會才知道,討論的內容就是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谷牧回憶:我內心是贊成“國防文學”這個提法的,因為它明確簡練,動員、團結面廣,符合當時抗日救亡形勢的需要。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是左翼文壇旗手魯迅先生提出來的,我對之不能公開地說不同意。多虧當時沒有講出自己的看法,否則,在“文革”中,我的罪名還得加上一條“鼓吹‘國防文學”。
其實,兩期《浪花》已經刊登了多篇兩個口號論爭的文章。第一期有柳林的《國防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洛底的《國防文學和作家的聯合戰線》、未白的《國防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第二期有蘇林的《關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柳林的《人民大眾對于文學的一個要求》、勁秋的《民族革命戰爭與報告文學》。其中柳林寫于1936年5月19日的《國防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文末附注“本文根據本社討論結果起草”,可作代表。全文一萬余字,分“國防文學”之產生的時代背景、對于“國防文學”之一般的誤解與批判、“國防文學”的任務三大部分,擁護“國防文學”的態度異常鮮明。文章指出:國防文學是在“歷史的現階段的中國的現實中正確地把握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的文學實踐所必然產生的嬰兒”。“一般‘學院派氣息的文人和一些對于文學的效用沒有正確認識的人的誤解,是有意無意地否認了‘國防文學之存在的理由,客觀上成為‘國防文學的敵人。”最后號召“全國的文學大師,英勇的青年作家們!最悲慘的命運迫臨我們的目前,最偉大的責任擱在我們的肩頭;凡不甘作奴隸的人們起來!集中到文學的‘國防的前線上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