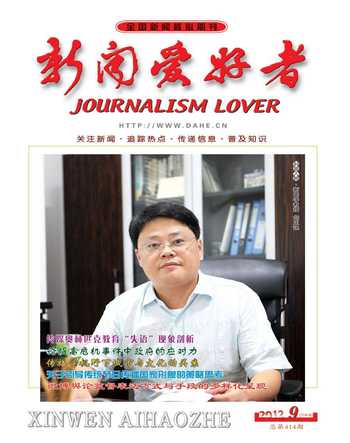試論微博時代的網絡誹謗
楊嘉嵋
【摘要】韓寒以“網絡誹謗”為由一紙訴狀將方舟子告上法庭,這是2012年春最吸引公眾視線的網絡民事糾紛。微博時代的網絡誹謗如何認定,網絡誹謗出現的社會背景是什么,此類侵權行為有無一定的積極意義,政策、法律規制給了我們什么啟示,本文將按照上述主線對微博侵權這一重要新生事物進行詳盡闡釋,以期對未來類似事件的審視提供有力參考。
【關鍵詞】微博;網絡誹謗;法律
“龍年春節,是方舟子陪我們過的”——2012年初春,中國公眾常常會冒出這樣一句有趣的調侃。1月29日,韓寒委托律師,就方舟子涉嫌網絡誹謗,在上海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方公開更正、道歉,賠償經濟損失10萬元。盡管迄今為止又經歷了韓寒修改訴狀、撤訴等風波,但這場“文戰”不再是“無聊口水戰”,而是進入了嚴肅的司法程序。
從方舟子接棒麥田發出第一條“質疑”韓寒的微博后,MicroBlog就成為其發布證據、自辯正義的主戰場,數量驚人的網友也以“方粉”、“韓粉”的身份攪動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微博激戰。微博作為當今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公共領域,其功能有沒有變化?微博時代的“網絡誹謗”有什么特點?
微博時代的公共領域
縱觀現代社會輿論發展狀況,公共領域由公共場所逐漸演變為以媒介作為平臺和中介。因尼斯認為:“如果一種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觸到,它就會被民主化。”[1]微博作為普通人易接觸的平臺,推動公眾成為一個個“自媒體”——只需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就可發布信息。“一句話就可號令江湖”的便捷速度,超大面積轉發、評論,雙向溝通的傳染效應,平等對話的民主姿態等都使中國公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自由。
盡管諸多熱點新聞在微博上呈現出碎片化圖景,但微博由初始的社交平臺逐漸轉變為輿論監督的利器、法治進程的推力則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傳媒大學網絡輿情(口碑)研究所發布的《2011上半年中國網絡輿情指數年度報告》顯示,網絡熱點事件中,18.8%的源頭是微博。”[2]在微博里,社會的發展趨勢、人民的人心走向、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公眾的表達水平都以最鮮活、最直接的樣本形式呈現于眼前,“微博已經超越網絡論壇成為中國第二大輿情源頭”[2]。但是,隨著網絡技術的更新、普及和表達空間的日益擴展,微博的民主開放品質開始受到一系列問題的挑戰,如精英掌控話語權、網絡語言暴力、虛假新聞、群體極化、網絡炫耀、網絡泄密、網絡侵權、網絡犯罪等。“韓方大戰”就是典型的網絡侵權中的網絡誹謗糾紛。
微博時代的網絡誹謗
虛擬中的真實:網絡誹謗。網絡是社會通信、社交工具,同樣需接受政策、法律法規的規制。在網絡侵權的類型里,侵犯名譽權是最典型、最常見的一類。從“艾滋女事件”、蒙牛“誹謗門”到“微博第一案”,網絡誹謗已不再僅是“圍觀者”看個好玩的鬧劇,而成了普通公民和法人維權的訴訟依據。
2002年12月23日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對網絡侵權行為作了單獨規定,其第63條規定:“網站經營者明知網絡用戶通過該網站實施侵權行為,或者經權利人提出警告,仍不采取刪除侵權內容等措施消除侵權后果的,網站經營者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3]法律法規的出臺,正是對虛擬空間的誹謗具有真實性的最好注解:“艾滋女事件”始作俑者被判有期徒刑3年;蒙牛“誹謗門”的3名被告分別獲有期徒刑1年、緩刑、拘役和罰款……法律法規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試圖或已經發出誹謗信息的人頭上,警示他們必須為其行為付出相應的法律代價。
質疑還是誹謗。我國有關網絡誹謗的民事侵權成立,須具備四個要件:有損害事實、行為人有過錯、行為的損害結果、行為與結果間的因果關系。[4]
上述網絡誹謗侵權行為成立的各項要件里,是否“捏造、散布虛假事實”當屬最重要的底線要件,其在某些案件里經過調查取證后容易鑒別(如“艾滋女事件”),在某些案件里卻令人難以辨清(如“韓方大戰”)。“散布”的定義與內涵并無太多歧義,本來明晰準確的“捏造”卻在“韓方大戰”中給了中國網民新的課題:質疑的權利和誹謗的邊界在哪里?
用實質性證據說話。質疑是公民的權利,發表質疑言論是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然而,任何一項自由都存在邊界,質疑的重要邊界之一就是需要質疑者提供實質性證據,即證據有足夠的數量且能形成較完整的證據鏈條;證據的指向非常明確,基本上不存在其他可能性。證據的可靠性越大,證明效力就越強。反之,如果僅靠道聽途說或靠自己的猜測、推理而導出的“證據”就涉嫌誹謗。從方舟子目前披露的所有證據來看,不僅有諸多場合聽來的只言片語,而且其對韓寒作品的文字分析也基本以猜測、推理為主,并無“還原當年現場”的實質性證據。
不用自己得出的結論進行指控。合理的質疑,是在大量確鑿證據的基礎上對某人或某事提出疑問,對其真實性、合理性表示懷疑,它的姿態應該是一個問號(?);誹謗則不然,誹謗行為人通過前述“證據”推導得出“結論”,這種“結論”通常具有負面效應,對當事人本身是一種指控,對當事人名譽是一種破壞,它的姿態是一個感嘆號(!)。方舟子不僅拋出了大量經不起推敲的“證據”,而且言之鑿鑿地認定韓寒一定被“代筆”,存在一個寫作團隊。這已經越過了質疑的界限,走向了指控,而缺乏過硬證據的指控涉嫌誹謗。
避免分階段、多手段攻擊炒作。質疑的動機與傳播方式都在合理范圍之內,具有單一性和純凈性;誹謗則在不同階段使用多種手段對事件、人物加以攻擊炒作,目的在于使對方的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蒙牛“誹謗門”中,北京博思智奇公關公司和蒙牛產品經理共同策劃了攻擊文案《DHA借勢口碑傳播》,其網絡攻擊手段包括:“尋找網絡寫手撰寫攻擊帖子,并在近百個論壇上發帖炒作,煽動網友不滿情緒;以兒童家長、孕婦等身份擬定問答稿件,‘控訴伊利;發動大量網絡新聞及草根博客進行轉載和評述等。”[5]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證據的硬度、是否得出結論和是否攻擊炒作是網絡誹謗的明顯特征,只要經過理性的認真檢驗,網絡誹謗并非不能與合理質疑區分開來。
微博時代的網絡誹謗特點
經濟成本更低,傳播更快更廣。相較以前的博客、網帖等大頁面爆料平臺,微博特有的140字的發表形式將核心事實、觀點濃縮成簡短精練的語句,即使再加上圖片、視頻,其經濟成本也更低。個人發表誹謗言論,只需很短時間和少量網絡流量;團隊發表誹謗言論,除了必要的勞務費外,也基本不用花銷其他的成本費用。另外,微博的評論、轉發方式具有“流毒斃鯊”的性質,①“毒素”呈幾何級數迅猛增長,綿綿無窮。從這個角度來講,微博正是因之精簡深刻、易于傳誦、“毒源”眾多而傳播得更快、更廣;反過來,此傳播特性又為節約誹謗者的傳播成本起到了客觀上的推動作用。
關注度更高。在“閱讀快餐”時代,微博的短小精悍、信息量大正好迎合了人們的閱讀偏好;日常生活中沉重的工作、經濟壓力使人們通過某些每天都會更新的微博來獲知社會最新資訊、窺視他人生活來達到解壓的目的,這些都是微博深受網友喜愛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氛圍沖擊下,巨量評論和轉發就是自然發生的后續,誹謗信息也就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大江南北。
維權的成本更高。當微博誹謗出現時,一般來說,被誹謗人有這樣幾個舉措:用各種方式澄清誹謗信息、刪除誹謗信息、向法院提出訴訟等。所有舉措都要花費被誹謗人大量精力和金錢,連公眾人物也拖累不起。就拿“刪除對方誹謗信息”來說,一方面是評論、轉發的速度極快、數量驚人;另一方面是刪除的手續復雜、費用較高,這樣的維權成本幾乎已經超過了公民自身的能力。
網絡誹謗產生的社會背景及一定的積極意義
社會背景。近年來,影響較大的網絡誹謗案件層出不窮,對我國當下的輿論環境和社會趨勢的走向有著重要影響。網絡誹謗產生的社會背景有以下幾個方面:
利益競爭的逐漸惡化。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商業、權力、名氣等領域更是出現了“贏了就是硬道理”的口號,不擇手段導致一波接一波的惡性競爭。既然錢、權、名都與當事人的名譽、社會評價緊密相聯,那么,從這個角度入手成本最低、成效最快;而網絡作為“自媒體”和傳播迅捷廣闊的媒介也就成了破壞名譽的上佳之選。事實證明,盡管誹謗者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其行為對無辜者造成的精神、經濟、名譽傷害卻難以精確估量和一一彌補。
自我表達與維權的強烈意愿。政治體制改革、市場經濟運行、文化產業發展使人們習以為常的諸多價值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個體權益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們壓抑多年的表達欲望也在這種氛圍中蘇醒,越來越多的人渴望能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樣不僅能參與最新最活的社會熱點事件,還能部分釋放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釋放的正義感,獲得自我認同。經過博客、帖子等寫作形式的歷練,網民對網絡表達不僅不再陌生,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網絡傳播經驗。精練簡約的微博在此歷史時刻登上舞臺。當誹謗的信息出現在微博頁面時,無論網友是支持、贊同還是駁斥、辱罵,其實都在客觀上幫助誹謗者達到了目的——大規模的熱切關注。
互聯網立法滯后,監管力度不足。如前所述,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明確了發信息者及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發布信息上的相關責任,為被誹謗人提供了法律支持。但在民事領域,無論個人還是企業,在起訴誹謗者時都需提供直接切實的證據。由于互聯網的虛擬性和匿名性等特點,當公民遭遇網絡誹謗時,個人取證能力十分薄弱;公安機關多以非刑事案件裁定而不予立案;網絡服務商在短時間內無法辨別信息真偽。因此還需要更有效的立法。
牛虻效應:一定的積極意義。關于網絡誹謗的負面效應已經無須贅述,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從辯證的角度來看,網絡誹謗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牛虻是噬咬或騷擾牲畜的一種小蟲,只要嗡嗡的小牛虻在跳舞,任何動物都需仔細反省自己的衛生狀況和躲避能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很多網絡誹謗的始作俑者就是這樣的“牛虻”,說他們代替新聞記者履行了部分“船頭瞭望”的職責也并不過分。這種備受爭議的“找茬”行為其實對公眾人物、普通公民也起到了很強的警示作用。
啟 示
2012年,“實名制”成為中國網絡規制的代表概念。“臺前網名,臺后真名”,受害者或警方需要查找誹謗信息的真實作者時,網站有責任公布作者的姓名和地址,這從技術上保證了調查取證的方便快捷,減輕了受害者的巨大痛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實名制”在降低偵查成本、伸張正義的同時,也封住了公眾的悠悠之口。如果社會公眾失去了可以暢所欲言的平臺,其積聚的不滿和怨氣將日益膨脹,直到成為社會穩定的真實威脅因素;而一個不清楚自己弊病的社會肌體也斷然不會是一個健康的生命系統,它只會在“咯咯傻笑中沉入大海”。
綜上所述,正因為政策、法律規制的力量無比巨大,所以其在公眾自由權利與社會安定和諧之間的平衡就顯得尤其重要,正在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國社會需要更科學的制度。
(本文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10YJC860050)
注 釋:
①《射雕英雄傳》里歐陽鋒為讓周伯通相信他的西域蛇毒最厲害,給一頭鯊魚喂了蛇毒后將之拋入大海,所有搶食了這頭毒鯊的鯊魚都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毒源”,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參考文獻:
[1]約書亞·梅羅維茨.消逝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12.
[2]鄭燕.網民的自由與邊界[J].社會科學研究,2012(1).
[3]李玥竹.網絡環境中名譽權侵權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09.
[4]吳問.我國對網絡侵權的現行規制研究[J].廣西欽州師范大學學報,2011(2).
[5]許天穎.從蒙牛“誹謗門”看網絡時代的商業誹謗[J].媒介觀察,2011(3).
(作者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