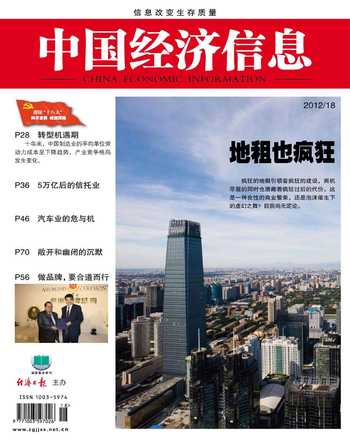5萬億后的信托業
宋奕青

當中國股市正在經歷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慘烈時,信托業悄然崛起了,迎來了5萬億時代。
2008年底1.22萬億,2009年底2.01萬億,2010年底3.04萬億,2011年底4.81萬億,2012年6月末5.54萬億。2008年以來,中國信托業的信托資產規模幾乎每年以約一萬億元的增長不斷刷新紀錄。從近三年看,信托業的資產規模增長速度,幾乎是保險業的3倍。
從1萬億到5萬億
一份由數家信托機構撰寫的《2012中國信托業發展報告》(以下稱《報告》)近日發布,這份數據詳盡的報告顯示,2008年以來,中國信托行業受托資產總額平均每年增加超過一萬億,到今年6月末已達5.54萬億元,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公募基金行業,接近了全國保險資產總額。
“應當說信托業迎來了最好的時代。”平安信托董事長童愷表示,信托公司的投資能力不斷在提高,已成為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在資金運用上,目前投資基礎產業是1.02萬億元,占信托總規模的21.11%,投資一般工商企業0.95萬億元,占信托總規模的19.68%,投資民營企業0.96萬億元,投資國家戰略新興企業724億元,投資小微企業594億元,投資三農294億元。“不過與銀行業相比,信托對于財富的吸引仍然是一個產品驅動的過程。”童愷表示。
平安信托將財富管理的目標鎖定在 120萬人這一高端財富群體。
這120萬人擁有高凈值、風險意識強、收益率要求穩定的特點。這些社會財富持有、運營者,不僅是信托業的主力消費人群,同時也被各類金融機構定為未來的拓展對象。
據《報告》統計,目前半數以上的信托產品投資者金融資產超過千萬,信托公司與私人銀行客戶重合度高達67.6%。絕大部分信托產品投資年齡集中在30-49歲,40-49歲的投資者占比達到40.5%。私營企業主和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是其中主力。
進入后5萬億時代的中國信托業,業務結果正發生微妙的變化。有觀點認為,信托產品已經成為了“富人俱樂部”而不是人們期待的“平民大食堂”。幾年中,信托認購的門檻越來越“高”,由5萬元起步抬高到100萬元,現在100萬元都難以入門。
普益財富信托業研究員范杰認為,我國信托的定位主要是投資理財,而不是財產管理。信托業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充當高端理財的角色。依據我國《信托法》對信托的定位,信托的本質功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所謂受人之托,代人管理財物,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其他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處分的行為。
縱觀世界各國的信托業務,都分為兩種:一種是受托機構只是充當單純的“受托人”,并不積極主動管理資產,這類業務實現的是委托人的特定目的;另一種是受托機構在“受托人”職能基礎上,附加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等其它職能。兩類業務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小投資者對信托產品的追捧是信托公司希望的,但這恰恰是監管層目前不愿看到的,甚至對此感到擔心。因為,信托產品只有面向自身抗風險能力強的機構客戶和實力較強的“大戶”,才能有效避免信托業的風險;相反,如果信托產品再次成為中小投資者追捧的對象,早晚要出事。
動能何來?
“過濾”掉中小投資者的信托公司2011年業績大幅提升,大都贏得缽滿盆滿,48萬元的人均年薪,使其傲視群雄,一躍而成為2011年最高薪的行業之一。
《報告》通過對平安信托超過700名客戶的抽樣調查顯示,約3/4的信托產品投資者既往投資信托產品實現了9%以上的平均年化收益。未來3年內,約2/3的信托產品投資者計劃增加信托產品購買金額。
據統計,2009~2011年,信托公司全行業累計分配信托收益分別為 552.29億元、678.04億元、1177.51億元。
正如《報告》首席研究員鄭智所說,中國信托業規模化、穩定性的高收益,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資本管制與幣值低估是包括信托產品在內的國內金融產品高收益的基礎性來源。資本管制下的中國,就像豎起了一個無形的大壩。由于其封閉性,這條無形的大壩也就面臨著兩條不同的水位線,人民幣作為一種高息貨幣形成了一個相對較高的水位線,境外的美元、日元等可自由流動的資本則處于較低的水位。
其次,在利率“雙軌制”下,信托產品收益更接近真實市場利率水平。由于融資類的信托計劃在發放信托貸款時,無需參照人民銀行制定的基準利率上下浮動限制,可以在不高于基準利率4倍的范圍內靈活設定利率水平,其高收益性有了合規性的基礎。
第三,能整合運用多種金融工具的信托計劃,在更深的層面上把握了風險,并獲得顯著高于債務融資的收益。信托公司有金融行業的“輕騎兵”之稱,是境內唯一可以跨貨幣市場、資本和實業領域的金融機構。信托平臺可以集成所有的金融工具,包括股權、債權股債混合等。
第四,杠桿化策略與結構分層是信托產品重要的高收益來源。杠桿策略在信托產品中的典型運用即信托產品的結構化分層。結構化分層是信托最常用的產品內部增信措施,又經常被稱為一種有限本金保障機制。優先受益權信托份額通常向高凈值客戶和合格投資者銷售,次級受益權則定向由融資方和交易對手認購。在償付順序上,次級受益權劣后于優先受益權受償,但所有剩余利益均歸于次級。作為融資方和交易對手的次級委托人,出于對項目的熟悉和投資能力的自信,通常愿意在事前約定將部分高收益讓渡給提供了杠桿支持的優先投資人。
第五,跨市場套利機會的存在是信托高收益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投資具有明顯不同的風險收益特征,金融的若干子市場之間也具備截然不同的高收益機會。信托產品能充分發揮跨市場投資的優勢,將投資者帶入到他們自身不能輕易介入的機構投資人市場,攫取相對高的收益。
歷盡大起大落
在信托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必須看到,信托業資產增長的軌跡。自1979年第一家信托公司誕生起,信托行業就步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到1981年底全國有241個市開展信托業務,在中國大有遍地開花之勢。2002年10月,就在信托產品加速推出,中小投資者趨之若騖的時候,人民銀行發布了,業內稱其為314號的文件,要求一個信托計劃項下的資金信托合同總數不得超過200份。314號文件對于快速升溫的信托熱來說,猶如一盆冷水,迅速在業界引起很大反響和爭論。
進入2003年以后,國內信托公司推出產品的速度更是呈現出加速度的態勢。即便是在SARS橫行的2003年4月,仍有8家信托公司推出了規模總額超過5億元人民幣的12個信托計劃。
到了2007年,信托業管理的資產規模開始“爆發”。2007年底,信托業管理的資產規模從上年底的3600多億元,增長到9621億元,重要的原因正是銀信合作“打新股”產品的盛行。
當時,股市在多年的“熊市”行情后,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實施,啟動了一年大“牛市”,打新股成為幾乎穩賺不賠的生意。銀行理財計劃不能“開戶”申購新股,但是信托計劃可以,于是銀行就把理財資金委托給信托公司去“打新股”。銀信合作“打新股”產品在2006-2007年曾讓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但此后,隨著股市的下行,此類產品風光不再。
事實上,信托真正“井噴”的時段,主要集中在2008年以來的近4年。
2008年平均每季度發行的信托產品數量為225款,往后三年這一數字呈幾何級數增長:2009年平均每季度發行381款,2010年平均每季度發行661款,2011年起,平均每季度發行超過1253款,2012年前兩個季度發行數量也均超過1200個。募集的資金規模,由2008年每季度約250億元左右,逐漸遞升,到2011年以來,每季度募集資金規模均已超過1000億元。
同一時期,基金行業受股市起伏行情影響,資產規模在2萬億的關口停步不前,2011年甚至呈逐季下滑之勢,銀行與保險業的增長速度則不到信托的一半。
2009年下半年,銀行信貸規模開始受到較為嚴格的控制,銀信合作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2010年7月達到峰值2.08萬億元(其中融資類業務為1.40萬億元,占比67.3%)。
此后,隨著銀監會一系列監管政策的實施,銀信合作業務規模開始回落,到2012年6月末,銀信合作余額1.77萬億,占信托業受托管理資產規模的31.95%。可以說,沒有銀信理財合作,就沒有今日信托業5.54萬億的受托管理資產規模。
2010年下半年開始爆發的房產信托熱,規模上雖有不及,卻是更賺錢的買賣。公開資料顯示,2010年,信托市場共發行集合類房地產信托產品528款,募資1560.85億元,較2009年分別增長1.5倍和3.3倍。加上單一類信托計劃募集的1303.23億元, 2010年房地產行業通過信托計劃共募資2864.08億元。
2010年11月,銀監會發布《關于信托公司房地產信托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房產信托暫時陷入低迷。此時,業內關于房產信托將被叫停的說法開始流傳。
2011年3月,房產信托再次爆發。國內信托產品單月發行數量、規模均創歷史新高,其中,房地產信托占3月信托產品融資量的46.45%,年化收益率更超過8%。5月,房地產信托的成立規模達到256.45億元,再創歷史紀錄。
紓困之路
歷史性地膨脹到5.54萬億后,信托也隨即陷入了多維度的困擾之中。先是年初至今信托資產投向的各種類型,從房地產、藝術品、礦業、貸款、慈善到證券都接連爆發風險問題;接著是券商創新大會召開、證監會宣布修訂《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保監會出臺新政“13條”征求意見稿,對融資類集合信托業務上產生了直接沖擊,使信托在資產管理業務上失去了過往的制度優勢,這對于正在業務轉型道路上苦苦摸索的信托業無疑是一重大利空預期。
無論是風險暴露還是業務競爭,都是一個行業在高速發展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過程。
“信托行業整體來說還很不規范。抓住政策的縫隙,就會爆發,一旦被糾正,又會陷入長時間的低迷。”上海某理財機構副總經理李霞坦陳,她在信托行業浸淫多年的經驗就是——“信托行業每一次大發展,都是與監管政策賽跑的過程。”
在銀信合作受限、房地產信托的膨脹與風險等現象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政策的影響。對此,平安信托董事長童愷表示,“2005-2007年的時候,通道型銀信合作業務模式比較流行,業內也多這樣操作,但是當時的銀信合作,信托公司基本上是依附在銀行,說難聽點就是‘吃銀行。這種模式沒有任何太多長期價值,且使你的業務模式有很強依賴性,受宏觀經濟波動影響也特別大。”
銀信合作的“失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貸管控的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監管機構的警覺。自此,監管層多次下文限制融資類銀信合作業務的發展,到今年上半年底,銀信合作余額已回落至1.77萬億元,占信托業受托管理資產規模的31.95%。
民生銀行私人銀行部副總經詠認為,銀信之間肯定存在競爭,但是現在市場尚未完全開發以及客戶需求并沒有完全滿足的條件下,銀信之間的合作肯定會大于競爭。“銀行與信托都想把市場做大給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可能是銀行產品和客戶需求相比較而言還不夠。所以也借助信托力量,加上銀行很好的客戶基礎以及服務客戶的手段等等,再改進一些服務方式,然后滿足這個市場。”
《報告》中指出,投資類銀信合作業務,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比如,部分中小銀行資產管理能力較弱,可以將理財資金委托給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投資于貨幣市場工具、債券、各種具有穩定現金流的權益類資產等。銀信合作需要“去信貸化”,信托公司未來要靠自己的資產管理能力,吸引銀行理財資金。如果信托公司靠自主資產管理能力吸引到銀行作為客戶,管理銀行理財資金,這樣的銀信合作不僅不應該受到限制,還應該受到鼓勵。
顯然,在這場財富的盛宴中,并不單單是信托公司“獨門宴”,銀行理財、基金、券商等金融機構都在虎視眈眈。可以預見,在銀行、信托、券商、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諸侯并起的財富管理市場,未來市場的競爭必將進一步加劇,而在這一競爭中,各方財富管理能力以及風險分析及處置能力也必將進一步予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