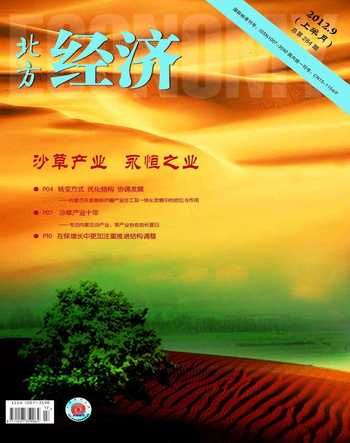我國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權缺失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陳祥升
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在我國主要指鐵礦石、石油、大豆、稀土等。無論我國作為買方市場還是賣方市場,我國都沒有定價權,這與傳統的經濟理論所制定的規則是不一致的。我國鐵礦石進口世界第一,2011年,國際鐵礦石巨頭再次更改定價規則,從年度定價改為季度定價,中國鋼鐵企業要比2010年多付700多億美元。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09年中國大豆進口量為4255萬噸,比2008年同比增長13.7%。但是,大豆的價格幾乎全部是國際四大糧商說了算,因為成本太高,中國本土大豆種植面積已不斷萎縮。 石油產業方面,2009年中國石油消費量為40837.5萬噸,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其中石油凈進口量21888.5萬噸,原油進口依存度達到52.5%,在國際油價面前,中國完全跟著國際市場走,“國際油價一發燒,國內油價就感冒”。那么作為賣方,我們是否就掌控定價權呢?中國的稀土儲量和產量都是全球第一,然而稀土賣成了白菜價。全球絲綢產量的70%在中國,而且中國絲綢的70%用于出口,應該說,中國是世界絲綢行業毋庸置疑的老大,可是作為最大的供應者,我們依然沒有定價權。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雙方決定的,當供求雙方達到平衡的時候,市場會有一個出清價格,也就是說,供求雙方在商品價格決定過程中是有發言權的。目前,在大宗商品的國際貿易中,主要有兩種定價模式:對于存在成熟期貨品種和發達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來說,其價格主要參考世界主要期貨交易所的標準合約價格確定。如全球原油最重要的定價基準是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Brent原油以及美國的WTI。據統計,全球每年石油貿易量在130多億噸左右,通過現貨市場的交易量只有20億噸左右,大部分都沒有進行實物交割;其他如鐵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則多由交易雙方每年談判達成。 通過對眾多文獻的歸納,決定一國是否能夠取得商品定價權的因素很多,如期貨交易所的影響力,本國的產量、需求量,行業集中度、信息等。 那么在我國,影響我國國際貿易品缺少定價權的主要因素是:
一、行業集中度低,企業之間惡性競爭
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速度很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基本以每年20%多的速度增長,有些年份甚至達到30%多。但是國內某些行業的市場競爭格局變化不大,各個行業集中度都比較低,貿易主體多,行業規模小,對外缺乏統一的聲音,自然缺乏影響力。2008年,我國共有鋼鐵企業1000多家,其中居前九名的鋼企產量只占全國總產量的40%;而歐盟前四家、日本前四家和韓國前兩家鋼企的產量分別占其地區和本國總產量的73%、75%和85%(劉剛,2009)。國內鋼鐵行業的鐵礦石需求方基本是由三種力量組成:一種是代表大型國有鋼廠利益的集團,他們在經濟和政策上都擁有一定優勢;一種是中小型的民營鋼廠,自負盈虧,經濟效率相對較高,但受到一定的限制;還有一種是貿易商,為賺取價差而存在。所以,雖然整體上我國作為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擁有比較大的議價優勢,但由于內部力量的分化,使得整體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大豆、棉花等都是這種情況。在鐵礦石的進口中,雖然中剛協極力協調,希望能夠承擔談判的主角,但是中剛協與各鋼廠并沒有那種天然的聯系,也得不到鋼廠的充分信任。而反觀鐵礦石的賣方,市場主要由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主宰,行業集中度高。我國的稀土雖然具有資源壟斷優勢,但稀土行業沒有培育和形成在國內和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骨干企業,行業企業眾多,集中度低,產能過剩必然導致價格的惡性競爭。近幾年,國家也在進行稀土相關企業的整合,如包鋼稀土對北方稀土企業的整合,但是要形成具有話語權的企業和市場地位,不是靠國家政策可以完成的,一定要通過市場競爭,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從眾多企業中脫穎而出,最后成為行業翹楚。
二、期貨市場小,缺乏國際影響力
一個國家要掌握商品的定價權就必須要有對國際有影響力的期貨交易場所。現代社會,金融資本在商品定價權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一般來講,期貨交易所中商品交易量越大,交易越活躍,就越容易撐握商品的定價權。目前,我國有3家期貨交易所,只有10個交易品種,而美國商品期貨市場則有多達 348個交易品種。交易品種稀少、市場規模小、市場開放度不高、市場參與者有限等因素制約了中國期貨市場的發展,使之難以發揮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作用。目前,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基本上掌握在幾大期貨交易所手里:國際石油價格的確定主要由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期貨價格決定;國際農產品價格主要以美國芝加哥期貨價格作為參考;國際金屬價格主要參照英國倫敦期貨價格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大宗商品進出口只能被動地接受國際價格。與此同時,由于我國企業在商業秘密的保護等方面缺乏管理經驗,外國的供應商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了解或預測我國的庫存狀況及采購時間、品種和數量,利用期貨市場進行炒作,抬高價格,賺取巨額價差。此外,由于我國企業缺乏利用期貨市場避險的能力以及我國沒有相應的國內期貨市場進行價格風險規避,這就使我國企業進口面臨的價格風險絕大部分由自己承擔。
三、產品技術水平低,產能彈性缺失
我國出口產品中加工貿易產品占比一般在50%以上,而一般貿易相對不發達,且我國加工產品企業大多處在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中的產品制造環節——即價值微笑曲線的最底端。我們知道,制造環節相比其它六個環節是創造價值最低的環節,如我國稀土主要是應用在傳統領域,應用在高新技術領域的不到 50%,特別是在稀土新材料領域,我國幾乎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如在國際軍工材料市場上金屬釹、金屬鑭、金屬鏑、金屬鋱等提煉于稀土的稀有金屬,其粗材與精材的純度每提高 1個百分點,價格就幾乎翻1倍。而目前的現狀是國際市場的稀土精材多為日、美等國以技術優勢掌控,而我國出口的多為稀土氧化物或其他合金型低附加值稀土加工產品。 無論作為資源需方或是供方,中國企業在產能運轉率方面都缺乏一定的彈性,產業鏈短,很多企業局限于初加工環節,這就直接造成了在市場向好時,企業快速擴產滿負荷生產,過度競爭造成全行業利潤微薄;市場一旦下滑甚至持續低迷時,企業只能適量減產,卻慎言停產,必要時借助政府之力拉動需求。 正是這樣缺乏彈性的工業產能,讓中國無論作為供方還是需方都面臨相對于交易對手的過剩問題。像我國鋼鐵行業7億噸產能如不能彈性運轉,面對市場的變化,三大礦仍有底氣漫天要價;即便上期所開設了銅、鋁、鉛、鋅、鋼鐵等所有的金屬期貨,具有反映和放大供需關系的期貨價格仍然不能反映中國的利益。
四、商品信息體系建設滯后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大宗商品信息體系,從商務部、農業部等網站可以找到綜合性的宏觀數據,如月度、年度的進出口總額等。沒有大宗貿易商品的供求數據,企業定價決策就缺少定價依據。美國農業部有500多人的專門機構,研究重要農產品市場的供求信息,每月向社會發布重要農產品的全球和分國別的供應、需求數量等信息,該信息對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國際農產品企業定價的重要依據。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