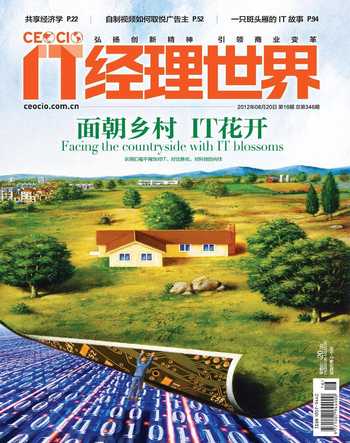通才如何煉成
汪丁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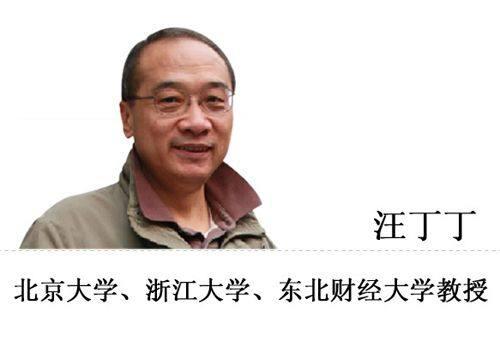
寫這一主題,最好的開篇是引用我寫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一位研究生的信:……你在西方的學習,年輕時,腦內的神經元網絡有極強能力建立各類知識在細節之間的神經元連接。所以,首先當然是勤奮,其次是廣泛。這兩個因素合在一起,就稱為“博聞強記”。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注重各類知識的細節。例如,羅素在龐加萊那本書的英譯序言里特別指出,博聞強記的學者很多(因為這是“學者”的定義),但龐加萊的特點是博聞強記并且注重細節(熟悉細節,這是“專家”的定義)。難得的,就是同時熟悉細節和廣泛的知識。我出國時已經32歲,記憶力遠不如年輕時那樣“過目不忘”,但仍比現在強許多倍。我反省自己記憶力的演變過程,總的趨勢是由具體的場景演變為抽象的關系。我指的,是“場景記憶”,隨著歲數增加,這部分可讀取的記憶在全部可讀取的記憶里占有的比重很可能越來越小。各類知識之間的抽象關系,隨著歲數的增加,越來越清晰。在這一演化過程中,我意識到,細節,特別關鍵。如果在最初(年輕時)不很熟悉各類知識內部的細節,那么,抽象關系就停留在“抽象”層面,不能(在中年或晚年)獲得直觀呈現。
讀了這段文字,我相信,一些讀者已全然明白我下面要展開的思路,不必繼續讀這篇文章。恰好我主持的跨學科教育實驗,在期末考試時出現了一些困惑。學生們的這些困惑是否可以緩解,與他們能否理解我這篇文章有密切的關系。畢竟,跨學科教育的主旨之一是“貫通各類知識”,它的另一主旨是“培養有靈魂的專家”。
人類知識原本是貫通一體的,中西皆然。貫通一體的知識裂為百科,流布天下,成為相互分離的專業知識,在西方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中國則更晚,是西學東漸之后的事情。于是,現在的大學知識,只能陳列為一系列課程。也是追隨西方反思,中國教育界近年試著講授“通識”課程。不過,以我的觀察,目前流行的通識教育遠遠不是跨學科教育。因為,那些通識課程仍是分離的知識而非貫通的知識,甚至也不表現出試圖貫通人類知識的傾向。
我們即將或已經進入的時代,被稱為“知識時代”。這一時代的勞動者,德魯克稱為“知識勞動者”(knowledge worker)。知識勞動者的主要技能不再僅僅是專業知識和技能,而是協調不同專業知識的能力。為了培養這種能力,根據教育界領袖們的建議,二十一世紀各國教育的主旨正在從傳授知識轉變為培養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由于專業化的局限性,知識勞動者怎樣可以判斷他專業之外的任何一項知識是“新的”呢?所以要有跨學科教育,成為對專業教育至關重要的補充。
在跨學科教育視角下,人類知識是貫通一體的,只不過因為專業化的緣故,每一專業的學生為應付考試,只熟悉整體的某一局部。事實上,每一個人,以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去追逐無限多的知識。那么,如何培養知識勞動者?跨學科教育不同于專業化的教育,根本在于它只呈現一系列模塊化的整體知識而不要求學生深入到任一模塊內部去熟悉知識的細節。這樣,學生在跨學科教室里學習的,是一幅知識地圖。同時,學生在專業課程的教室里學習知識地圖的某一模塊內部的細節。例如,我主持的是“行為金融學”實驗教育,我必須安排足夠多的金融學專業課程。但由于這一實驗同時還是跨學科教育實驗,所以我必須減少一些金融學專業課程,為了增加一些跨學科課程。
如果教學方法仍是專業化的,那么,跨學科課程永遠收效甚微。所以,培養知識勞動者,我們首先要培養跨學科教師。知識在跨學科教師的頭腦里呈現為整體,是消失了細節的整體,是由許多知識模塊聯接而成的整體。一名教師的跨學科能力,在他講授某一知識模塊內部的細節問題時,可獲得充分表現。不同于專業化的教師,細節問題,在跨學科教師的講授中,處處表現出通向其他知識模塊的沖動。
怎樣培養優秀的跨學科教師呢?我開篇引用的那封信表明,要從青年(如果僅僅是知識的貫通)甚至童年(如果不僅是知識的而且還有人生的貫通)開始培養。因為,腦內神經元網絡通常隨年齡增加而漸漸地“官僚化”,從而更適合某一專業而不適合跨學科。又如開篇所述,記憶力的趨勢是從具象的場景記憶漸漸轉為抽象關系的感悟。如果你在腦的青年時期不努力學習各類知識模塊內部的細節,那么,這些知識模塊之間的聯系,對你而言,充其量不過是老師告訴你的那些聯系,而不能成為你有直觀感悟的知識聯系。也就是說,沒有細節,你將很難感悟模塊之間的聯系,于是你仍是一名專家而非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