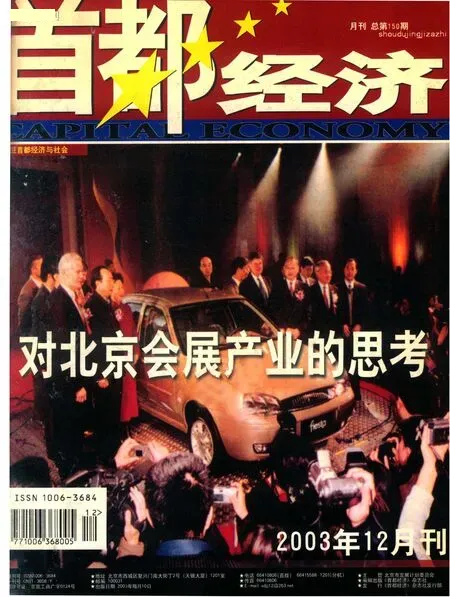智慧城市萬億投資商機的背后
師燁東

2011年被稱為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元年,年中有超過154個城市提出建設智慧城市,其中包括我國全部一線城市與80%的二線城市。2012年,智慧城市的建設掀起更大規模熱潮。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6月,僅與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電信運營商提出進行智慧城市建設的城市數就超過了320個。保守估計,在2012年底將有超過400個城市開始開展智慧城市的建設,相關專家預測全國在智慧城市建設上的投資總額可能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而在“十二五”期間智慧城市建設所帶來的產業機會更是可能高達2萬億元。無論是打開報紙還是瀏覽網絡,諸如 “中國移動500億元打造智慧山東”、“中國聯通與23省118個城市簽約智慧城市建設項目”、“中國電信簽約25省150個城市建設智慧城市”之類的新聞時常映入眼簾,可見智慧城市建設的火熱程度一點不亞于2000年左右時全國各地紛紛宣布對“數字城市”的打造與建設。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竟引得如此多的地方政府與公司、企業紛紛大規模投資進行建設?
智慧城市是什么
智慧城市由英文‘Smart city翻譯而來。2008年,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認為智慧地球應以智慧城市為區域基礎逐漸發展而來。隨后,智慧城市的概念傳入中國。
在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童騰飛看來,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傳入到中國后,地方政府及企業都結合了中國特色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與詮釋。因此,中國所提出的智慧城市與IBM提出的‘Smart city并不能簡單的等同,而可以認為是一個相對更為復雜與龐大的概念。網絡上關于智慧城市的定義很多,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概念是:“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知識社會創新環境下的城市形態,智慧城市通過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維基、社交網絡、Fab Lab、Living Lab、綜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應用,實現全面透徹的感知、寬帶泛在的互聯、智能融合的應用以及以用戶創新、開放創新、大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征的可持續創新。伴隨網絡帝國的崛起、移動技術的融合發展以及創新的民主化進程,知識社會環境下的智慧城市是繼數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發展的高級形態。”
按照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德仁教授的觀點,智慧城市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表達,即“智慧城市=數字城市+物聯網+云計算”。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總監龔承亮認為,數字城市是信息化的一個初級階段,其為城市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系統服務,也讓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智慧城市是信息化較為高級的階段,但其建設需要按部就班的來,而之前十余年的數字城市的建設可以認為在信息基礎設施、消費理念、政府管理能力等方面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從技術角度來解讀智慧城市,李德仁教授的公式是正確的。”但是對于智慧城市來說,其涵蓋的范圍更廣,僅僅數字城市與物聯網、云計算的技術加在一起,不能等同于其整體概念。智慧城市包含了更多城市生態環境、市民生活、產業生產等方面內容,注重的是整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政府管理的更加便利與市民生活的便捷與幸福。
童騰飛認為,雖然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待智慧城市會有不同的定義,但其所敘述的本質是相同的,即“從技術層面,智慧城市建設是技術系統的智能化響應與判斷,是信息化城市的一個較高層次的發展;從社會意義來講,其目的是為了讓城市主體運行更加高效、方便,讓市民生活更加幸福。”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什么
智慧城市的建設之所以這么熱,與我國眾多區域面臨城市化過程中資源緊缺與人口眾多的管理問題、智慧城市建設可帶動地方政府經濟發展以及相關企業的利益訴求有密切關系。然而,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完整的規劃、合理的引導與很多標準的制定,并不是提出概念投入資金建設就能做成。2000年左右,“數字城市”的概念開始在中國熱炒,許多地方政府紛紛宣布投入資金打造數字城市。不到十年時間,隨著電信運營商與政府合作的“無線城市”概念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又開始宣布打造無線城市,此時數字城市的建設在很多城市有何成果仍不得而知。面對“智慧城市”概念的洶涌來襲,地方政府與企業都需要理性思考,避免盲目過熱建設可能帶來的投資與產品浪費。
童騰飛認為,智慧城市的建設應該以服務城市管理與市民生活為目標,做好頂層設計,在建設時有相應標準的細分,有合理運營模式,同時還應有一個產業與企業對接的平臺來合理促進智慧城市相關企業。“頂層設計是首要的問題,政府應該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對相應的產業、企業進行合理引導,才能避免建設過程中出現盲目投資與浪費問題。物聯網傳感器、接入手段及電子信息的標準化也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國家層面與北京市都在與產業聯盟進行協商,以期逐步推進標準化的制定。標準的制定也需要一個過程,目前只能依托城市管理需要與百姓需求程度來對不同標準的制定排先后次序。對于智慧城市的投資是一個無從估算的大數目,而且其建設將是一個緩慢推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應有合理的運營模式,從政府管理與企業投入利益平衡的角度,通過政府與企業、民眾的供需對接來促進企業投資,而不應該僅靠政府資金來推動建設。”
太極計算機股份有限公司創新中心總經理于躍認為,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一個很長的周期,其推進會有很長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結合各地不同的特色有相應的差異。但是政府與企業共同協商的頂層設計是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在于躍看來,頂層設計需要有四個標準,即“高、新、遠、全”。“高”即意味著政府需要站在高處,通盤考慮智慧城市的建設中需要什么,應該做什么;“新”即頂層設計不能脫離開新技術與新形勢,要結合當前實際情況考慮與開展;“遠”即頂層設計的規劃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考慮,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需要什么標準與成果;“全”即頂層設計需要對整體產業、城市建設與管理、市民生活等各方面全面思考。在頂層設計逐漸完善之后,政府應與企業共同協商標準的制定以及相應工程中資金、技術業務等的落實模式。與此同時,于躍還認為智慧城市不僅僅是政府的事,社會公眾也可以受益。“比如家庭中的電器控制。如果進行傳統布線,不僅浪費材料,施工麻煩,而且價格貴,是資源與民眾財富的雙重浪費;如果進行無線化管理,不僅布置輕松,節省空間和資源,而且還更加經濟。但是如果民眾不了解無線控制家電的概念,相應的建設就無從談起了。”
政府對智慧城市建設的頂層設計是當前建設的首要重點,這成為政府與企業層面的共識。龔承亮認為,標準是頂層設計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標準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與技術、工程設計、管理的成熟度息息相關,在實踐中會通過試點項目來總結出標準,指導后續的工程建設工作。政府當前還應注重對產業鏈的打造與概念的推廣。智慧城市的建設是一個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而公司投資進行建設、政府花錢購買業務的模式在龔承亮看來是一種多贏的局面——公司進行長線投入,逐步回收利潤;政府不必一次投資過大,可以相對快速實現管理的信息化與現代化;而市民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實際的益處。以此模式為基礎,逐漸實現不同專業的分工,并進行產業鏈的打造,將有效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對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應用還需要進行推廣,管理者、建設者與使用者都應該有相應的認知,知道其未來成效與益處。民眾的消費與生活意識提升上去,可以更好促進政府與企業建設智慧城市的熱情”龔承亮說道。
北京的標桿作用
無論是數字城市、無線城市還是智慧城市的建設,依托于北京良好的經濟態勢與完善的政策引導,北京市目前所取得的成果都處于全國的領先地位。龔承亮認為,北京市應該利用這些優勢,為其他省市樹立一個“榜樣”的作用。同時,其他省市智慧城市的建設也不應該是某一地方的“縮減版”,而應該根據地區實際的經濟情況與地方特色進行合理發展。
北京十余年來的數字城市建設已有相應的成果,北京市政府管理工作與市民生活的便利程度都得到了極大提升。諸如政府管理所用的“電子政府”系統,住房公積金系統、社保卡系統,市區內的電子社區,以及“首都之窗”門戶和公共服務平臺,都是使政府與市民得到實惠的應用。
在網絡與無線城市建設方面,北京城區已經實現六大區域的免費wifi接入,無線上網非常容易。預計2012年年底,全市范圍內將實現20M寬帶全覆蓋,新增光纖到戶覆蓋家庭超過100萬戶,新增光纖寬帶接入家庭80萬戶,10M及以上寬帶接入產品滲透率超過25%。
由于數字城市與無線城市相對完善的建設,北京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上有非常良好的基礎。北京市政府層面非常注重對產業的引導與政策的制定。為了實現“智慧北京”規劃目標,政府出臺的《智慧北京行動綱要》提出了8大行動計劃,包括了城市智能運行、市民數字生活、企業網絡運營和政府整合服務4項智慧應用行動計劃以及信息基礎設施提升、智慧共用平臺建設、產業與應用對接、創新發展環境 4項智慧支撐行動計劃。北京市計劃通過實施8大行動計劃,組織市內各級政府和社會的資源,共同推進應用、產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智慧提升,實現從“數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躍升。一些相應的建設標準、管理條例、相關法律與評估標準也正在商討、制定之中。北京市關于智慧城市已有很多實際應用,如藥品監管,農作物生長環境數據采集與可視化數據監控,軌道交通安全視頻監控平臺,地區動態停車信息等等。
在中國,智慧城市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概念,其建設過程可包括前期信息基礎與物理端口設施制造、中期數據處理設施建設和后期的服務平臺建設,建設過程涉及到電信設備制造企業、物聯網企業、數據分析企業、電信運營商等等,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將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拉動作用。與此同時,智慧城市的建設還涉及到城市管理、城市環保狀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市民的生活便捷程度、滿意程度等各個方面。
智慧城市的建設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合理規劃與引導,民眾消費與生活意識的提升,產業逐步發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而北京依托著經濟與規劃上的優勢,在智慧城市建設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將給其他城市帶來相應的標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