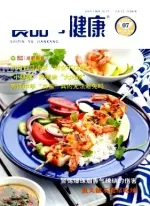紅袖織綾夸丹柿
宜晴
小時候總是有著滿把的空閑時光等著我們去揮霍,每常下了學,便老愛跟在同學屁股后頭跑,東一家西一家的竄進竄出,到了炊煙裊裊時分也不避諱,非得母親再三再四地喊了回家吃飯才拍拍蒙塵的衣褲意猶戀戀地回家去。于今,往事多數已是忘卻了,唯獨剩下一二張畫面,仿佛記憶中特地定格的照片,是無憂的快樂,是新知的好奇,是永不褪色的飽滿。
那是一個初冬的午后,我第一次隨著軍屬身份的同伴冒昧地闖入門禁森嚴的軍區大院兒,在那些大院兒前的空地里,我第一次見到了懸掛于明爽秋樹枝頭的丹柿點點。那曾是我童年印象里多么瑰麗的一幕呵,幽碧的初冬天底下,是落盡深綠的椏槎,午陽特有的逼目的光線打透了所有物什,也為這干凈的柿樹披上一層薄薄的光衣,稚嫩的小手遮籠雙眸,此刻整個寰宇便只剩下細如秋毫的光絲,而那玲瓏如燈的冬柿正沉著地懸在那最高的枝椏之上,四散的天地晶光恰為這天地間凝結的靈物鋪設了最好的舞臺背景。
畢竟稚童無知,哪里曉得天光云影天地大美的道理,只是呆呆地再也不愿挪步,可恨偏偏飛來一只熟道的雀鳥,伶俐地占住樹杪左右顧盼,并不時拿那銳喙一下下地銜啄一只殘了一半的丹柿。鳥兒以它無比高傲的姿態享用著那只柿子,同時也睥睨著樹下眼露貪求之欲的孩童。終于,雀鳥居高臨下地飛遠,那只殘柿被飽滿的果肉沉甸甸地墜著,柿蒂牢牢連續著那半枚欲墜的果實,在光影映照下,一團火紅之中隱隱可見到幾點黑色種子,被下墜的果肉拉扯出來的絲絲果肉也能辨得格外分明。
不知是否因為初冬的空氣過分明凈的關系,此刻疏朗的空氣之中竟也摻染了幾分甜津津的柿香。當柿蒂還留在梢端隨冬風而動的時候,銜了果兒去的雀鳥為這方寰宇留下一縷馥郁的馨甜,可它卻早已消逝在夕陽之中。年長之后,讀到白居易《杭州春望》,其中有句:“紅袖織綾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讀著品著,仿佛眼前就有當時被鳥銜殘的柿果妙影,那分悠久的氣息,似乎連續了今古,而我遙望著那枚四方菱形的柿蒂,看到了可愛的從前,看到了無數幽幽淡淡拂去還至的人間情愫。
柿,亦有稱其為朱果者,屬柿樹科。六月間開鐘狀黃白色花,果實大小互殊,形狀亦不一致,普遍呈卵形或扁圓形,八至十一月間成熟。杜牧說:“過雨檉枝潤,迎霜柿葉殷。”霜降前后,柿葉如丹,而那墜滿枝頭的果實,如盞盞小紅燈籠越出墻外,則分外可人。據《酉陽雜俎》記載,柿樹有“七絕”:一多壽,二多蔭,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觀,六嘉實可啖,七落葉肥大可以臨摹書寫。足證柿為世之所珍,非一端也。柿可分干澀兩種,干者在樹上成熟,采后便可啖食,澀者須經脫澀加工后,方可供食。我們常見到的
柿子有兩種,一種是圓扁的“大蓋柿子”,更多的是小而圓、甚至還長出幾個尖嘴兒的“火柿子”。其實,柿有多種,按宋代吳自牧《夢粱錄》所載:“柿,方頂、牛心、紅柿、椑柿、牛奶、水柿、火珠、步檐、西柿。”暮秋之際,葉落草黃,樹枝上獨“火柿”高掛,紅裹金球,此時紅葉如醉,丹實似火,故蘇軾有詠詩云:“柿葉滿庭紅顆秋”,讀來令人神往不自禁矣。
中醫認為,柿子性味甘、澀、寒,入脾、胃、肺經,有清熱潤燥、生津止渴、養陰止血之功,適用于燥熱咳嗽、痰中帶血、胃熱傷陰、煩渴口干、痔瘡下血等,北方人很喜歡將柿子脫澀后制成柿餅、柿干等,此時的柿餅,表面凝結了一層薄薄的白色結晶體,是為柿霜,柿霜的潤肺力極強。
柿子,珊然可愛,無論帝王貴戚抑或是庶民百姓都格外喜歡這枚秋冬時節的嘉果。
明《嵩書》中載有:“戌午大旱,五谷不登,百姓倚柿而生。初冬削柿作餅,鬻錢完賦,即以批曝于雜橡實、荊子磨面作糊啖之,遂免流移。”
明清宮廷尤喜柿子,除了柿子味美,也因“柿”字諧音為“事”。明代時,每年元旦日宮里會將柿餅、荔枝、桂圓、栗子、熟棗共裝在一個盒內,大家一起吃,這樣的節令小吃盒兒被稱作“百事大吉盒兒”。之后的清朝,喜愛把玩如意的清宮帝后們常會在各色材質的如意云頭上雕琢出兩個柿子,就叫“事事如意”,而有萬年青、柿子裝飾的如意,則被喚為“萬事如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