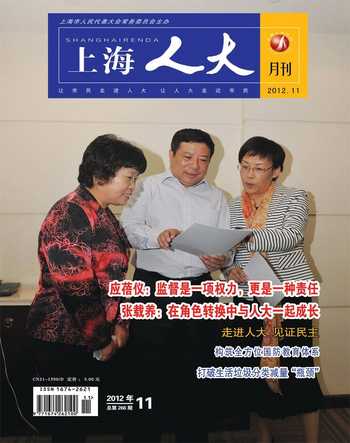打破生活垃圾分類減量“瓶頸”
朱琦
上海要突破環境資源制約,解決“垃圾圍城”難題,實現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化刻不容緩。為了持續推動這項工作,市人大常委會在去年進行專項監督的基礎上,今年繼續開展監督,圍繞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分類處置能力建設和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等內容進行重點調研。
據悉,2011年以來,市政府已連續兩年將“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列為實事項目,去年在本市1080個居住小區試點,今年試點范圍進一步向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集貿市場和公園等1050個新場所拓展。與此同時,與分類投放相匹配的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置全程分類體系也在逐步推進。2011年順利實現進入末端處置設施的人均生活垃圾處理量減少5%的目標,目前正在為再減量5%的目標積極努力。
9月25日,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聽取并審議了關于本市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化工作情況的報告。如何化解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化工作中的三對“矛盾體”,成為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中熱議的焦點。
化解居民參與分類和“二次分揀”的矛盾
垃圾分類和減量化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發揮各自作用,特別是廣大居民的積極參與才能持續推進。
人大在調研中發現,盡管試點小區居民對垃圾分類的知曉率、參與率有所提高,但從當前運轉情況看,這項工作主要還是靠政府的投入來推動,“外在推力”大多來自綠化市容部門和街鎮政府。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內生動力”不足,一方面是沒有有效的激勵引導措施,另一方面又缺乏強有力的制約措施。據統計,在一千多個試點小區中居民參與率能達到60%以上的不多。同時,分類投放的準確率也較低,垃圾分類基本上依靠“二次分揀”來實現。“現在一些小區所謂垃圾分類搞得‘好,實際上是‘二次分揀搞得好,不少小區居委干部充當了‘分揀員的角色。”陳強努委員直言。
在常委會審議中,不少委員和代表擔心這種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和“二次分揀”的運作機制難以可持續發展。如何化解居民參與分類和“二次分揀”的矛盾,委員們指出,除了要加強社會面的宣傳發動,讓垃圾分類的理念“入腦入心”,還應加強垃圾收費等政策研究,通過約束和激勵相結合的方式,破解居民參與率低的瓶頸。陳兆豐委員認為,上海可以借鑒臺北實行垃圾收費的經驗,盡快推出垃圾收費試點。“現在上海實行垃圾收費的條件已然具備。”陳兆豐委員分析,“一方面,去年國務院就已下發文件,明確要求按照誰產生、誰付費的原則推行城市垃圾收費制度;另一方面,上海擁有一批具備管理條件、管理設施和管理能力的小區和街道,試點的基礎較為扎實;此外,廣州等一些兄弟省市已經試點垃圾費按袋按量收取模式,也可以給予上海一些啟發。”
化解回收體系和末端處置不對接的矛盾
近來,一種“阿拉環保卡”正在申城悄然走紅。原先家里的廢舊手機、墨盒、家電等電子廢棄物,大多數人都會簡單地扔進垃圾桶,或賣給馬路上的回收“游擊隊”換點小錢,這在無形中使得電子垃圾日益成為威脅城市環境的“毒瘤”。日前,浦東新區金橋再生資源公共服務平臺推出一項環保行動,市民通過交投電子廢棄物獲得的積分可以通過“阿拉環保卡”消費或變現,輕松實現“變廢為寶”。
當下,政府將回收體系建設作為城市垃圾減量的重點工作,相關部門積極推進“回收點、交投站、分揀加工中心”三級回收網絡建設,支持企業創新回收模式,開展再生資源回收服務平臺和“在線收廢”網絡建設,方便公眾交投,提高回收效率;同時,支持企業擴大回收范圍,促使廢玻璃、廢舊衣物、電子廢棄物等逐步進入回收系統。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本市回收各類廢舊物資達722萬噸,有效促進資源循環利用,減輕了垃圾處置的壓力。
然而,人大在調研中也了解到,當前,正規的廢棄物回收企業敵不過馬路回收“游擊隊”,回收體系與末端處置“脫節”,仍是本市生活垃圾分類與減量化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點。
目前本市廢舊物資回收行業仍以“馬路游擊隊”為主,存在散、小、亂現象,規范化、規模化的回收企業并不多。受用地等因素制約,不少廢舊物資交投堆放點設置規劃并未真正落地。當前本市尚未形成比較規范的回收從業隊伍和完善的回收網絡。回收網絡不健全,加上回收價格低,大量本來可以循環再利用的廢舊物資被“排除”在回收系統外,作為垃圾被填埋或焚燒。與此同時,相當數量的回收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未能與本市的再生資源循環利用企業形成有效對接,不少回收物品直接流向外省市,導致本市一些具備規模化加工處置能力的再生資源利用企業“吃不飽”,造成生產能力的浪費。
對此,甘忠澤委員認為,有關部門必須致力于回收體系的重組整合,對于一些有條件有積極性的再生資源回收企業和加工處置企業加強扶持力度,使其做大做強。
化解濕垃圾資源化利用和技術標準缺失的矛盾
上海每天約有700噸單位餐廚垃圾、445噸菜場垃圾和居民廚余果皮被有效處置,分別制成飼料添加劑、有機肥料介質等產品。“市級大型設施集中處置和區縣中小型設施分散處置相結合、分散處置為主”的濕垃圾處置格局逐步形成。
“垃圾要真正實現減量化,就要增加其循環利用、再生利用的比重,逐步減少焚燒、填埋的比重。”甘忠澤委員指出,垃圾分類主要實行干濕垃圾分類模式,如果能對生活垃圾中的主要垃圾——濕垃圾“集中攻關”,進行資源化利用,那么填埋、焚燒的比重就會大大下降,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化的目標才能實現。
但實際上,濕垃圾的資源化利用遠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人大在調研分析后認為,其主要原因在于濕垃圾用來制作有機肥或飼料缺乏相應的技術標準支撐,導致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的技術路徑不清晰,各區濕垃圾處置設施建設進度明顯滯后,有些分類出來的濕垃圾經過壓水后只好仍作填埋、焚燒處理。由于缺乏產品標準,目前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的主要形式是發酵堆肥,其“產品”也只能用于綠化、林地,出路有限。
如何打通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的“出路”?一些委員提出,有關部門應當通過完善技術、制定標準,切實解決當前濕垃圾資源化利用遇到的技術標準障礙;一旦技術路徑明確,要加大統籌力度,科學安排全市濕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進度和區域布局,促進資源的有效共享和合理配置。
廚余果皮占到家庭垃圾的一半之多,如何推進其源頭減量也是委員們關切的問題。張載養委員認為,當前上海已有條件推廣使用家庭廚余果皮粉碎機,比如在排污管道具備條件的地區,試點推行居民家庭安裝廚余果皮粉碎機;新建全裝修住宅應當將安裝廚余果皮粉碎機作為建筑標準大力推行,利用技術手段實現家庭垃圾的源頭減量。
市人大常委會在去年進行專項監督的基礎上,今年繼續開展監督,圍繞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分類處置能力建設和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等內容進行重點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