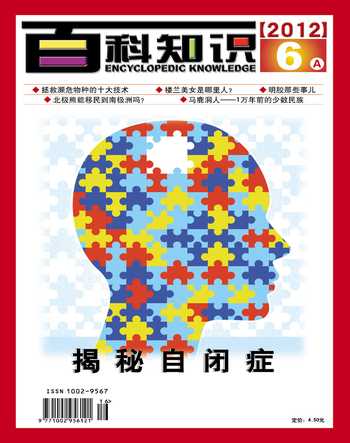北極熊能移民到南極洲嗎?
余夫



北極熊生活在北極地區嚴寒的冰雪環境中,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北極熊的生存受到了極大的威脅。于是有人突發奇想:那就將北極熊遷移到南極洲吧!這聽起來似乎是一種合理的做法,因為畢竟都是極地地區,氣候條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那么,這個想法真的能實現嗎?
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
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是指能夠維持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條件的地方,例如海洋、河流、森林、草原和荒漠等。每一種野生動物都在身體結構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對它的棲息地具有特殊的適應,由此可見棲息地對于野生動物的重要性。
人類經濟活動的迅猛發展對野生動物造成最大的影響之一,就是不斷蠶食著它們的棲息地,毀壞了它們的棲息環境。棲息地的惡化將使野生動物的實際分布區縮小,導致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因此,野生動物保護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保護它們的棲息地,即就地保護,建立自然保護區就是就地保護的有效措施之一。
對于一些數量特別稀少、僅僅依靠就地保護已經不足以保證該物種延續的、處境非常危險的野生動物,則需要進行遷地保護。在有條件的地區,如動物園、研究所、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等,利用良好的設備和先進的技術,進行籠養條件下的人工飼養繁殖,建立起中心種群和譜系簿,使之達到繁衍和發展,把種群保存下來并加以擴大。當這個物種的遷地保護成功,繁殖到足夠多的數量之后,可以逐步將它們釋放到原產地,即“再引入”。
“再引入”是指把一個在原分布范圍內已經消失的物種重新放歸原產地,并努力恢復其自然種群的行動,是保護瀕危物種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遷地保護的最終目標。我國麋鹿的“再引入”工作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范例。
“再引入”的成功范例
麋鹿俗稱“四不像”,在我國曾經廣泛分布,但野生種群在明、清時代滅絕,僅有200~300只被飼養在當時的北京南海子皇家獵苑里。麋鹿野生種群滅絕的原因除了被大量獵捕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近代南北各地許多沼澤或近海低洼荒地均被開墾成農田,使得只適于在沼澤地帶棲息的麋鹿沒有了容身之地,成為平原地區最早的生態災難的犧牲者。
1894年北京渾河(永定河)發大水,沖垮了皇家獵苑的圍欄,多數麋鹿逃散。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獵苑中的麋鹿全部在戰亂中消失。幸運的是,在1865~1894年間,有一些麋鹿被陸續盜運到歐洲,被飼養在各地的動物園或飼養場中,后來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到數千只,已經從瀕危物種紅皮書的名單中劃掉。
1985年8月24日,20只麋鹿(5只雄獸,15只雌獸)從英國返回它們的祖輩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被散放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內。將一個物種如此準確地引入它的原產地,在世界“再引入”工作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很有歷史意義。此外,我國還在江蘇大豐、湖北天鵝洲等更為廣大的濕地環境中先后建立了麋鹿種群,這些地方也都是麋鹿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現在,重返家園的麋鹿已經重新適應了當地的氣候和生態環境。
在我國,與麋鹿遷地保護的故事類似的還有普氏野馬、高鼻羚羊等。而國外的野生動物遷地保護起步更早,成果更為顯著。例如,歐洲野牛曾分布于歐洲中部、西部和南部的廣大地區,后來范圍逐漸縮小,在野外生存的最后一頭于1921年2月9日被獵殺,后來通過利用全世界動物園中飼養的56只歐洲野牛進行再引入工作,終于使其免于滅絕之災。美洲野牛的命運也與此類似。
指猴是馬達加斯加島上的著名特產動物之一,由于人類的殺戮和森林的消失,指猴在很長時間內已經絕跡,直到后來在該島的東岸重新發現了一些成年個體。1966年,科學家將收集到的9只個體放養到馬島東北部林木較為茂盛的曼戈比島上。通過數十年艱苦的努力,這種世界上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的生存出現了轉機。
在鳥類中,遷地保護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菲津賓保護食猿雕的計劃、巴基斯坦對彩雉的再引入、德國對普通松雞的再引入等等。
除了瀕危野生動物的遷地保護之外,人類也曾為了維持當地的生態平衡而引入新的物種。例如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在狼群被人類的獵捕而消失后,草食性動物由于缺乏食肉動物的制約而大肆繁殖起來,尤其是馬鹿的數量已經失控。這一后果直接導致了黃石國家公園里的很多幼樹因被植食性動物的大量啃食而難以生存。
為了使國家公園內的生態恢復到從前的自然平衡狀態,黃石公園實施了狼的引入計劃。1995年,黃石公園從加拿大引入了14匹狼,一年以后,又有17匹狼來到這里,后來繁衍到200匹左右,成為世界上狼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當地的林木也再現了生機。黃石公園“引狼”計劃的成功也引起了美國其他各州的關注,后來有十幾個州都在考慮推行狼的引入和恢復計劃。
富有爭議的援助遷移
上述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將原來在一個地方消失的物種重新引入到該物種曾經生活過的地區。那么,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即一些動物是原來一個地區所沒有的,但被人為引入到這個新環境后,能完全融入而不破壞當地的生態呢?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例如雉雞(也叫環頸雉、山雞、野雞等)。它的原產地就在中國,除西藏的大部分地區和海南島外,雉雞的蹤跡遍布中國各地,而且數量相當多。自1300年起,雉雞陸續由它的原產地中國以及俄羅斯東部和朝鮮等,被引入到世界各地,現在已廣泛分布于亞洲、歐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群島等地,成為當地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著名的水鳥——鴛鴦主要在中國北方以及俄羅斯東部、日本和朝鮮等地繁殖,越冬時到中國南方,偶爾也到達緬甸和印度東北部一帶,而在英國和北歐一帶也有成功引入的種群,成為當地的留鳥。
原產于歐洲、非洲、亞洲等地的原鴿,已經被引入到北美洲和中美洲各地。而原產于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亞等地的多種鸚鵡,在中國香港等南方地區就曾因為籠養的個體不斷逃逸到野外,逐漸形成了野生種群。
通過這些例子,有一些科學家想到,能否將那些面臨威脅的物種遷移到更適宜的地方,包括遷到該物種正常棲息范圍之外的生態系統中去呢?這個嘗試將一個物種重新安排到一個新的棲息地的做法被稱為“援助遷移”或者“有組織的遷移”。這是一項富有爭議的策略,有些人認為,這種做法有些狂妄自大;也有人認為,對于確保某些物種的生存機會而言,這很有必要。目前,一些植物和無脊椎動物已經成為了這種有組織遷移的首批試驗品。因為有的科學家認為,相比高等動物而言,它們似乎更容易被遷移與管理。
“香榧守護者”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一個“援助遷移“項目。美洲榧是一種高度可達到18米的常綠植物,目前正從其原產地美國佛羅里達州迅速消失。科學家為了拯救這個瀕危物種,已經將十幾棵美洲榧成功地從佛羅里達州遷移到了被認為氣候適宜的北卡羅萊納州。
另外,在一個小規模實驗中,科學家將兩種蝴蝶從英格蘭南部轉移到了采用氣候模型預測出的適宜棲息的北部地區。10年之后的結果顯示,這些新來的昆蟲移民“人丁興旺”,生活狀況不亞于它們那些生活在南部地區的“兄弟姐妹”。
但是,即使有這些初步成功的例子,遷移一個物種也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它在政治、社會、經濟、科學、生態和倫理等各個層面上都具有很復雜的因素。目前,人類在這方面的研究能力還屬于初級階段。當人們認為,這里就是適合某個物種棲息的地方,這里的氣候是我們未來所期望的……但實際上,除了氣候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很重要。在我們能夠充分理解一個物種是留在原地好,還是有遷走的必要之前,還有一大堆基礎科學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物種入侵的前車之鑒
事實上,援助遷移最大的隱憂不僅是一個物種能否成功地適應新環境,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它會不會適應能力太強,反而成為一個入侵物種,也就是一個被引入到非原產地的地方后,形成自我繁殖能力并給當地生態系統造成損害的物種。發生在澳大利亞的“人兔之戰”就是一個最好的反面例證。
1788年以前,澳大利亞根本沒有野兔。20多只歐洲野兔搭乘英國皇家海軍第一艦隊的艦船,從英格蘭來到了這片肥沃的土地上。其中的13只野兔逃逸到了野外,它們在自然界迅速繁殖,一場可怕的生態災難爆發了!為了抑制野兔的擴散和繁殖,澳大利亞人絞盡腦汁,從最原始的獵殺、布網、堵洞、挖溝、煙熏、投毒、設夾子和驅狗追殺,到運用化學武器、開展“生化戰”,再到效仿長城修建總長度超過3000千米的籬笆來防御野兔。
這場“人兔之戰”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外來物種入侵事件。同樣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在不時地上演。英倫三島本來是紅松鼠的家園,但自從19世紀末北美洲的灰松鼠被引進后,紅松鼠的噩夢就開始了。灰松鼠的個頭比紅松鼠大,且身體強壯,在森林中沒過多久就“反客為主”,使英國本地的紅松鼠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數量銳減。此外,在灰松鼠的身上還帶有一種它們自己已經免疫,卻對紅松鼠致命的皰疹病毒。灰松鼠還給英國的林業造成了巨大損失。每年一到夏天,大量正處在交配期的雄松鼠就瘋狂地撕咬樹皮,試圖靠這個動作吸引雌松鼠的注意,最后雖然它可如愿“抱美人而歸”,卻留下許多被啃掉樹皮的樹木慢慢枯死。
當前,在世界各地,外來物種入侵的現象已經愈演愈烈。這些入侵性的動植物侵害本土野生生物的方式包括:吃掉本土生物;產卵;毀壞它們的棲息地;散播疾病或在生態系統的同一個小生態環境與本土生物競爭等等。由于在新的環境中沒有天敵,許多入侵物種都大獲成功。
物種遷移的奇思妙想
盡管如此,有些人仍然相信,通過總結過去的教訓,科學家預測一個引入物種是否會成為入侵物種的能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被隔離的環境,如湖泊或者海洋中的島嶼,可能更易受入侵物種的攻擊;動物遷移的距離遠近或許也是因素之一,將一個物種從一個大陸遷往另一個大陸似乎比在同一個大陸的臨近地區之間遷移的風險更大。
目前,科學家已經可以利用生態數據和計算機模型預測一個新的地點在幾十年后是否適宜某個物種生存,從而能夠降低援助遷移的風險。當然,在決定進行援助遷移之前,政策制定者應該對被遷移物種所能獲得的利益、遷移給新的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遷移行動的可行性以及遷移決定的社會接受度進行評估和平衡。對于可能是拯救某些物種的唯一機會,他們需要認真考慮將那些受到嚴重威脅的物種遷移到其他具有廣泛生物多樣性的地區。
自從“援助遷移”的概念提出之后,各種關于物種遷移的奇思妙想層出不窮,例如將獵豹引入北美洲、將科莫多巨蜥搬到澳大利亞、讓野馬入駐美國大平原……。不過,大多數科學家對援助遷移的態度仍然沒那么樂觀。他們認為,要預測一個物種是否會成為入侵物種,依賴目前的技術和模型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強制的遷移工作具有高度的風險。因此,如果我們把物種到處遷移,我們制造的問題很可能和我們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回到是否能夠將北極熊遷移到南極洲的問題,雖然北極和南極都是極地地區,但二者的環境條件和生態系統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南極是一個被大洋環繞的大陸,而北極卻是一個被大陸圍繞的海洋盆地;南極和北極都很寒冷,但是南極的氣候卻要比北極惡劣得多:南極的年平均氣溫為-50℃,最低溫度為-89.2℃,而北極的年平均氣溫為-18℃,最低溫度為-68℃。南極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冰蓋,這巨大的冰蓋終日散發著寒氣,迅速冷卻著空氣,使它享有“世界冷極”、“世界風極”和“世界旱極”的極端稱號。
在生態環境方面,南極圈內沒有草更沒有樹木,僅僅生有苔蘚類低等植物;而北極圈內則不然,有些地方不但有草原,而且還有茂密的森林。南極和北極生活的陸地和海洋動物的物種也有很大差異。南極洲不存在大型陸地捕食動物,而生活著多種憨態可掬的企鵝。如果將北極熊遷到南極洲,它們將主要以企鵝為食,這種毫無防御能力的獵物可能在不久之后就會數量銳減,北極熊也會因為缺乏食物而逐漸走向消亡。
【責任編輯】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