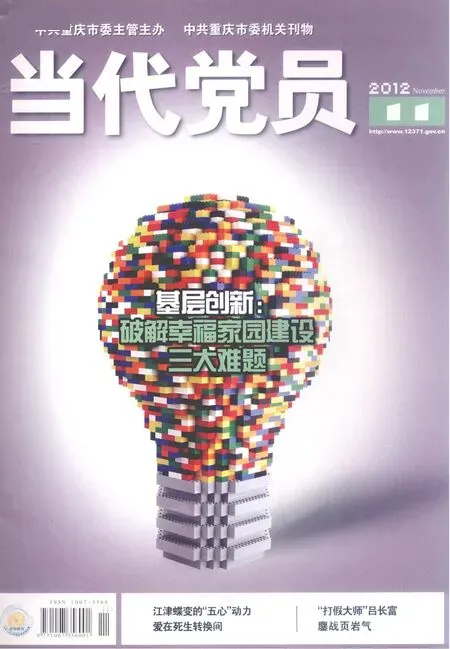老宅重生記
譚健
晨曦熹微,重慶上清寺披染著圣潔的金黃。
中山四路85號,磨磚對縫的灰色磚墻,簇擁著懸山式的門樓,推開沉重的黑漆木門,充盈鼻腔的是滿墻爬山虎的清香。
一道黑漆木門,把這座公館與外界隔絕開來……
“棒棒”公館
謝晉富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觸碰戴笠公館的大宅門,是在2008年的夏天。
那年7月,老謝從四川鄰水一路東行,來到重慶,投奔在這里當“棒棒”的兒子。
他穿過黑漆斑斑的大宅門,走下青石臺階,躲過院子里的幾攤污水,順著邊上的木板樓梯上了二樓。
在他腳下,散發著腐味的木板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仿佛在訴說公館的前世今生。
二樓,東扯西牽的電線把長廊的空間切割得支離破碎,頂樓一間小屋已經坍塌了。
此刻,謝晉富并不知道,這座三層小洋樓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有著“蔣介石的佩劍”之稱的戴笠的公館。當然,謝晉富更不會知道,就在這里,中國諜報人員曾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情報。
謝晉富只知道,這里是自己當“棒棒”的兒子和20多戶進城務工人員的出租屋,每個月的租金是200元。
大門外,站著重慶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史若飛。
史若飛喜歡逛老建筑,常常會轉到戴笠公館來。
盯著公館院子墻上那塊有了銹痕的“重慶市渝中區文物保護單位”的銘牌,史若飛發出一聲惋惜的長嘆。
嘆息的不止是史若飛,還有重慶市國有文化資產經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程峰。
“在全市,還有更多的文物遺址處在風雨飄搖中。”從2005年開始,程峰就關注起全市的抗戰遺址遺跡保護。
然而,這份愛卻略顯沉重,“全市抗戰遺址遺跡,部分殘存81處,毀54處”。
“巴蔓子將軍墓不見天日,東華觀藏經閣搖搖欲墜,法國領事館舊址危機四伏……”在2007年的渝中區“兩會”上,憂心忡忡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交了10份議案和提案,都是關于搶救歷史文化遺產的。
然而,保護又談何容易。
“這些遺址的產權分散,文物管理部門無權對公館進行管理。”程峰無奈地搖搖頭。
解放以后,這些遺址大多作為公房分配了。昔日的公館,成了平常百姓家,歷史的塵埃被油鹽醬醋所替代。
數百座老舊建筑,正一格一格地爬出人們的記憶。
另一方面,“隆隆”巨響的城市現代化腳步,則無情地把人們殘存的記憶碾得粉碎。
修舊如舊
2006年,上海新天地。
“青春是可以復活的!”程峰擊掌大喜。
漫步石庫門,青瓦灰墻的老上海建筑之間,是各式各樣的高檔咖啡館。
流連其間,程峰仿佛感覺時光倒流,猶如置身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
從這年起,程峰和市文資公司的同事們將觸角伸向全國,尋找重慶歷史文化遺址遺跡的“重生”之路。
“石庫門模式”讓他們眼前一亮。
石庫門曾是上海破舊、擁擠的惡劣環境的代名詞。
如今,通過修舊如舊,石庫門被開發成上海文化休閑旅游的勝地,數百棟老舊建筑獲得了重生。不僅如此,這里還成了“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
程峰等人的石庫門之行,改變了戴笠公館的命運。
從上海歸來,程峰逢人必講“開發性保護”。
2007年5月14日,經過長期醞釀,市文資公司向市政府報送《關于保護開發歷史建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建議》,建議維修改造戴笠公館,將其開發為巴渝文化會館。
建議得到市委、市政府同意。在相關部門的支持下,經過同戴笠公館原住戶協商,市文資公司取得了戴笠公館的產權。
2008年9月30日,戴笠公館修舊如舊工程啟動。
程峰總愛往戴笠公館跑,他擔心工人會傷到公館里的寶貝。
一個日本造的壁爐成了修復工程的焦點——由于年久失修,壁爐出現了破損。
“修復困難嗎?”程峰問。
“瓷磚是日本造的,工藝難度很大。”專家回答。
“砸了,照著樣式重建一個。”有人建議。
“那豈不是成了‘假古董了!”重建的建議被專家組否定。
最終,專家查閱了相關文獻,采取修補的方法,把破損的部分補齊,讓壁爐恢復了原貌。
不僅是壁爐,公館內的木地板、墻面顏色、條石、青磚褐瓦等元素,全部得到特殊的保護處理,被保留下來。
文化造勢
戴笠公館復原了。
2010年初的一天,站在公館外的史若飛心情不可名狀。“重慶的書法藝術何時也能像這公館一樣恢復青春?”
從全國來看,重慶的書法藝術氛圍還不夠濃。
“實際上,重慶有不少書法大家。”史若飛說。
晏濟元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晏濟元,別號素貞老人、老濟、濟公、江洲散人。
人們熟知晏濟元,是因為他的畫。朱德曾經評價“海外有個張大千,國內有個晏濟元”,其繪畫上的成就可見一斑。
“晏老的書法也堪稱一絕。”史若飛眼波流動。
即便如此,重慶的書法藝術依舊不為人道。
“我們缺少對外展示的陣地。”史若飛搖搖頭。
當年4月底的一天,巴渝文化會館的人找到史若飛。
“巴渝文化會館將成為我市的傳統文化藝術地標。”來人雄心勃勃地說。
巴渝文化會館便是修復后的戴笠公館。
“需要我做什么?”史若飛問。
“請您出面,請晏老出山,辦一場書法展。”
“行!”史若飛一口答應。
巴渝文化會館修復后,需要裝填文化產業,以維持會館的運營,從而實現歷史遺址的“活保”。
于是,市文資公司專門成立了重慶嘉禾實業有限公司,程峰任總經理。
“要把會館建成‘匯聚巴渝文化特色,展示巴渝文化魅力的文化陣地。”程峰信心滿滿。
新生的巴渝文化會館急需一場“處女秀”,借此揚名立萬。
晏濟元成為這場“處女秀”的不二人選。于是,會館找到了與晏濟元有著深厚交情的史若飛。
經史若飛引見,晏濟元同意在巴渝文化會館舉辦其個人書法展。
2010年5月10日,巴渝文化會館正式開館。
巴渝文化會館的“處女秀” ——“晏濟元書法藝術展”也同時開幕。
持續十天的書法藝術展,吸引了近千名參觀者到現場觀摩,西南大學、遵義醫學院、第三軍醫大學的同學甚至自發前來參觀。
此后,巴渝文化會館還陸續舉辦了十幾場書畫藝術展。
“涂山三杰”、王閑影、李際科、許伯建……一個個巴渝文化精英紛紛走進會館,讓會館攢足了人氣。
文化“金蛋”
2012年4月8日下午,巴渝文化會館三閑堂茶藝會所。
“下面一件拍品是蘇葆楨的《葡萄》,尺寸35cm×70cm,無底價開拍。”拍賣師向在場的競拍者宣布。
競拍者盯著旁邊的拍品,畫中淺紫色的葡萄粒粒飽滿晶瑩,充滿了豐盈之美。
“200元。”有好事的競拍者第一個喊出了報價。
在座的競拍者發出一陣哄笑。
眾所周知,被譽為“蘇葡萄”的國畫大師蘇葆楨,正是以其獨樹一幟的葡萄圖而享譽海內外。
“10000元。”第二個競拍者把競拍價拉到正常的競拍價位上來。
隨后,又經過三輪競拍。
“70000元。”競拍者第六次喊價,現場再無人舉牌。
“70000元第一次。”
“70000元第二次。”
“70000元第三次。”
“成交!”一聲槌響,《葡萄》最終以70000元成交。
這天進行的是“巴渝文化會館春季競拍會”。
此前的“晏濟元書法藝術展”及隨后舉辦的十幾場書畫藝術展,叫響了巴渝文化會館這個品牌。所以,當會館一說舉辦競拍會,便得到不少收藏家的響應。
這次春季競拍會上,共推出44件拍品,其中,會館自有拍品19件,以會館名義征集名家作品18件,合作方嘉華拍賣公司提供拍品7件。
經過激烈的競拍,競拍會實際成交42件拍品,成交金額達611400元。
這樣的競拍會,巴渝文化會館至今已舉辦了五場。
“通過舉辦競拍會,會館可以賺取服務費用,從而獲得會館的保護修復資金。”程峰說,“下一步,我們將把書畫藝術與禮品饋贈相結合,推出適銷對路的定制禮品。我們要讓經過歲月洗禮的歷史文化遺址產下更多的‘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