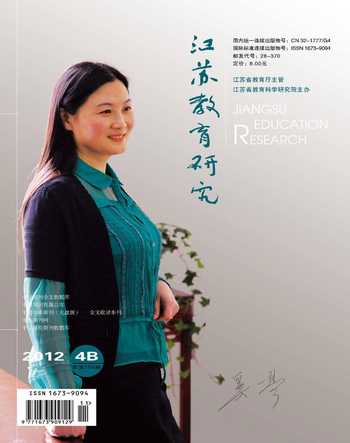把握時代發展內涵 變革領導思維方式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頒布。依據《綱要》精神,2010—2020年,發展義務教育的總體思路,一是要遵循《義務教育法》的法律規定,二是把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作為重點,三是把提高質量作為根本任務,四是把解決或緩解義務教育階段熱點難點問題和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結合起來。作為在教育變革中處于變革主體的學校而言,學校領導力首先表現為對學校發展的自我意識的把握能力。面對變革,學校該具有怎樣清醒的自我意識,又如何把握自身的辦學方向和價值追求?這是每一所學校在新的歷史發展節點都需要做出的主動回應。
一、建立動態生成思維,把握“我為什么做”,不斷提升學校質量內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計劃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菲力浦·庫姆斯在他的名著《世界教育危機———八十年代的觀點》中指出:“比起習慣上定義的教育質量以及根據傳統的課程和標準判斷學生學習成績從而判斷教育質量,這里所說‘質量還包括教與學的‘相關性問題,即教育如何適應在特定環境與前提下學習者當前和將來的需要,還涉及到教育體系本身及構成教育專業要素(學生、教師、設備、設施、資金)的重要變化,目標、課程和教育技術以及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環境等。”因此,在庫姆斯看來,教育質量不是一個靜態的、封閉的概念,而應該是動態的、開放的概念:“質量和水平是相對的,是根據特定的時間、地點,特定的學習者和他們的環境相對而言的。”
庫姆斯的教育質量思想把握了教育質量與教育環境之間互動的和辯證的關系,他批判了把教育質量理解為脫離時代和學校的變遷,以一種一成不變的標準做出評價結論的傳統思維。社會的不斷進步,對人的要求在不斷變化,對教育的價值追求也不斷發生變化。在新的變革背景下,每一所學校的校長首先要對時代命題作出積極回應,建立動態的思維方式,在辦學目標追求的內涵提升和科學質量觀的確立中,發揮積極的引領作用。事實證明,任何一所學校的改革都是從質量觀調整和改革開始的,尤其是每一所優質學校,之所以能成為有口皆碑的優質名校,首先是老百姓對其質量觀的認同和“教育產品”特質的認同。
常州市局前街小學是一所百年老校。“面向全體學生,讓學生全面發展,全面提高教育質量”,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局小辦學堅持的根本。所謂的“全面發展”,在當時特指“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協調發展。所謂的“高質量”指的也就是學生在“德、智、體、美、勞”方面都獲得較好的發展。在育人目標的定位上,局小實現了“認知領域”外的拓展,這無疑是巨大的進步。在這一辦學理念背后更蘊含著學校“質量觀”的積極意義,局小并沒有把“教育質量”等同于“學科知識的獲得”和“學科技能的習得”。“全面發展,打好基礎”的辦學宗旨孕育出“輕負擔、高質量”的辦學特色,百年老校在教育改革的主動回應中書寫了輝煌的篇章。
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局小站在時代的臂膀上對學校的教育價值又一次作出了自覺的思考。大家對“人”這一獨特生命個體的認識進一步明晰,局小的“高質量”理念受到了時代的挑戰。究竟如何認識學校教育中的學生,“高質量”的時代內涵是什么?關注生命,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就是這一變革可能的突破口之一。時代的文化轉型,根本的體現是對生命的尊重與信任;時代的發展,根本的需要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個體的出現。2005年,學校加入了華東師范大學葉瀾教授的“新基礎教育”研究。
在世紀之交的學校變革中,基于對學校教育價值觀的重新認識,局小在“輕負擔、高質量”的辦學特色中,關注了傳統和現代的融合,進一步提出了“教育是一種生命關懷”的辦學理念。在這樣的價值追求下,學校通過成長空間的創設與拓展,通過高質量的學校教育生活的創造,促進著每一個生命的健康成長。
“教育是一種生命關懷”,這一教育理念實現了局小辦學質量內涵的時代詮釋。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我們嘗試著去回答:教育如何適應在特定環境與前提下學習者當前和將來的需要?如何為培養在未來迅速發展和變革的領域里有效地發揮作用的人而制定新的課程標準和教學計劃?我們認為,有質量的教育的含義在世界不同地區應允許有不同的解釋。但是,無論背景怎樣變化,至少有一種含義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當教育賦予學生應對現實生活中多種挑戰的力量時,才可以被稱之為“有質量的”。正如立陶宛教育和科學部長AlgirdasMonkevieius所說:教育質量是有背景條件的,它的形式是演變的。我們所說的教育質量,是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的理解,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需要與可能性、理想與潛力之間,盡最大力量架設起來的橋梁。
教育質量的概念是變化的,它受地區差異、時代特征和人們的主觀意識的制約。因此,在每一個不同的教育發展階段,每一所學校都需要重新扣問自己:我們的教育是為了誰,目前又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對常州市局前街小學來說,在面對又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時,依然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辦學目標,并進一步實現在理念層次上的具體轉化,在實踐追求上的深入系統。
二、建立整體關聯思維,把握“我如何做”,不斷改善學校發展方式
教育事業發展到新階段,必然從重數量規模向重質量內涵發展轉變,這是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上好學”問題的必由之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要鼓勵學校辦出特色,積極探索發展模式,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接受適合的教育。
學習者特征(健康的、有學習動機的)、教育過程(有能力的教師使用積極的教學法)、教育內容(相關課程)、教育體制(良好的管理和公平的分配)等都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制約因素。哪怕是如庫姆斯所說的教育技術“從講課方法到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講座會到練習,包括黑板、課桌、教科書、師生比例、教室和樓道的布置、年級制度、校歷、把時間分成教學單元的電鈴以及影響孩子們前途的考試和升級制度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整個教學“系統”和“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促進學習。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每一所學校必須要回答這樣的自我追問:我們是在進行局部的變革還是系統的整體設計?圍繞本校的辦學目標,是否在整體意義上推進了質量提升?
新世紀以來,在教育宏觀領域變革的同時,學校變革也同步開始了。事實上,在素質教育推進的過程中,很多學校的變革,做的僅僅是學校表層的加減法,僅僅是從學校發展的外在層面展開的變革,是對教學目標做出的零星的反思與探索,缺少從根本上重建學校教育的改革研究與實踐。雖然這樣的變革也給學校帶來了新的發展,但這種沒有觸及學校內核、由外而內發生的局部變革,不可能給學校帶來持續發展的原動力,也無法應對時代發展對學校教育的挑戰。我們應該再次追問自己:從事的是推動外在的變革還是內涵的深層變革?
許多學校教育的改革更多地還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是對國家和政府發動的宏觀改革的積極呼應。實踐證明,學校只有主動變革,才能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變革的實踐產生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又將帶來新的探索與變革,只有形成良好的理念與實踐變革的互動關系,學校才能充分發揮實驗學校教育變革排頭兵的引領作用,開拓進取,不斷跨越新的臺階。因此,我們還應該反思:是主動推進變革還是被變革?
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頒布,學校主動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空間,學校的發展開始轉型,由粗放型發展向內涵型發展轉變,這種轉變要求我們立足于學校傳統,高瞻遠矚地分析時代背景,分析學校自身優勢與不足,認識自我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過整體的改革實踐不斷拓展發展空間,實現學校教育的深度變革。
三、建立創生歸納思維,把握“我依靠誰做”,不斷激發學校內生力量
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研究所所長楊小微提出:當代學校變革與發展的重要特征是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為此,我們面臨著許多方面的思維習慣的改變,學校各個層面的領導,都要從過去習以為常的“指令—演繹”式的思維習慣轉向“創生—歸納”式的新思維,而這常常是決定著學校辦學質量的瓶頸。
這一想法的提出,實際上是直面了學校傳統組織管理的弊端。中小學內部管理的結構,大多參照科層制范式區分出高層、中層、基層三個層次,每個層次一般都包含黨、政、工三大系列,校長室為高層,中層機構為教導處、辦公室、總務處,基層組織有教研組、年級組、備課組等等,德育、教學和后勤服務三個條狀系統通過這三個層級得到落實和貫徹。在新世紀以前,作為一所百年老校,局前街小學基本遵循了這一傳統組織結構的設置范式,各自向垂直系統的上級主管負責,每一個條狀系統的橫向關聯性不強。作為基層組織中的教師往往接受多頭管理,割裂而不關聯的工作布置既造成了精力的損耗,更影響了學校教育時空的育人價值。
學校組織機構在長期運行中基本形成了上傳下達、服從和執行的職能觀。這樣一種組織運行機制,葉瀾教授曾經將它的特征作了提煉:“上級決策,下級執行;一人指揮,眾人行動;統一任務,逐級演繹;套路相似,結構雷同。”這樣一來,具有教育性和成長性的學校組織的特性被扼殺,學校教育的創造活力和師生的創造力難以激發、生長。
庫姆斯曾提出,課程改革要取得實效,不僅要有一個廣泛的社會理解條件,而且要得到承擔這項任務的人的廣泛支持,特別是一線教師的支持。由此可見,新一輪規劃綱要的落實,呼喚每一所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因為在這樣的組織里,學校構建大家共同發展的愿景,讓每一位教師成為盟約的信奉者,共同為了美好的東西去努力,而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物質獎勵。在這里,不存在指令式的管理,更多的是民主的、參與式的共同合作性的努力。在這樣的學習型組織內,共同的團隊規范、組織對教師專業理想的承諾、團隊精神等可以轉化為領導的替身,教師完全出于責任和義務去奮斗。我們相信,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幫助學校整體實現教育質量的提升。
由此可見,在新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每一所學校都需要反思:我們的學校組織建設走到了哪一種狀態?離學習型組織還有多遠?領導方式是哪一種類型?教師工作的推進動機出于哪一種?有沒有為教師的主動創造構建良好的機制?
葉瀾教授指出:“真正面向未來的學校文化恰恰要扎根于傳統與現實的文化土壤之中,孕育出的卻是超越歷史與現實的文化。”面對新的教育改革背景,我們唯有清晰地認識自己,明晰了“我們是誰?”“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們如何行動?”“我們何以可能?”等自我的追問,才能在教育領域轉型性變革中正確地選擇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成為變革的參與者、促進者與引領者。
(姜明紅,常州市局前街小學,21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