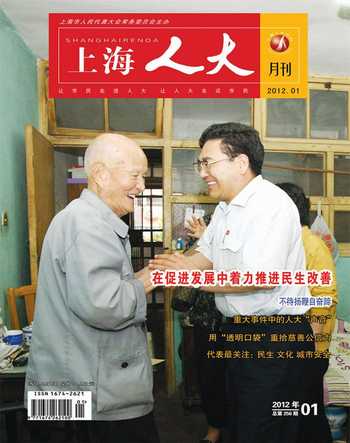城管執法、城市治理與行政法治
陳越峰
我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經濟飛速發展,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隨之松動,人口、資本、產業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目前的城鄉一體化進程不可避免地體現了階段性特點:政府主導推進和公眾有序參與相互作用,當然也出現公眾自發無序參與:貼小廣告、擺流動攤位、賣盜版碟片、無證運渣土、開“黑車”……當政府以管理秩序對這些自發無序參與進行規范時,如果僅僅追求管理秩序,且超越發展階段對管理秩序要求過高,會壓縮甚至阻斷自發無序參與的空間,而在城市謀得“飯碗”的剛性需求,就會導致各種形式逃避,甚至抵觸。
秩序沖突中最先顯現的是一些極端對抗事例,這也容易把人們的視線引向粗暴執法、暴力抗法等表層問題,由此,執法者開始反思,基于政府職能轉變,“柔性城管”、“美女城管”等舉措如雨后春筍。這些探索,當然有值得贊賞之處,然而僅在這一層面思考,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制度性解決。“柔”與“美”所衍生的賞心悅目與溫柔,如果不能調和秩序與生存發展的矛盾,最后就很可能導致表層問題也解決不了、解決不好。
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針對流動攤販執法應者寥寥,對渣土卡車撞人的查處則一片叫好?看來,對違法行為的類型化剖析,并以此為基礎確立城市治理政策很有必要。比如,對流動攤販,賣水果、賣盜版光碟和賣假藥的,需分類考量;對貼小廣告、求租、招工和辦假證的需分類考量;對無證營運和以營運為名詐騙、強迫交易的需分類考量。進一步說,對僅違反秩序和既違反秩序又侵權的行為要分別考量,是否涉及財物的違法行為也要區別考量。首先,在執法手段選擇的必要性上,要設定和選擇侵害最小的以實現目的,而非以“最嚴格執法”為名粗暴執法;其次,在執法手段的平衡性上,要在能夠實現的公共利益和受到縮減的相對人權益之間權衡,不可低估了相對人謀求城市生存的動力;最后,在執法手段運用的妥當性上,要注意不搞運動式執法。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說過,當一個人不再相信他所依賴的生活權利時,他就別無選擇,只能成為一個秩序破壞者。如果一座城市中,有為數不少的特定群體始終以破壞者的身份存在,那么需要反思的恐怕就是秩序本身了。
曼德拉的話給我們的啟示是,城市治理中的目標設定非常關鍵,沖突的根源有時恰恰在于單一并過高追求秩序和整潔。當特定情形下的謀生手段具有一定正當性,僅僅在秩序意義上“違法”時,應當反躬自問“秩序”目的設定是否符合當前實際。我們需要實現雙向互動的合作型治理,形成尊重生存權利的公共理性。不久前頒布實施的《上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辦法》、《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中規定,政府應當對攤販進行引導,充分考慮其利益訴求。體現了城市治理立法和城市治理中對各方意見的重視、對各方利益的平衡、對權利與權力的協調。這些具有上海創新特色的思考,值得肯定。
現代特大型城市治理面臨的,是統籌公共利益和個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兼顧而不造成對立,需要不斷擴大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例如,增開公交線路、延長公交運營時間、提供公共免費租賃自行車,就會使對無證運營車輛的需求不斷縮減;完善公共信息發布平臺,發布小廣告的空間必然不斷縮減;規劃設置合理的設攤地點,對流動販賣的需求則會不斷縮減……可見,規劃、建設、運營和治理系統中都需通盤考慮城市治理與權利保障、城市運營與給付安全、城市建設與發展行政、城市規劃與社會塑造的關系。現代行政法角色轉變的需求也應運而生,行政措施應盡快完成從管理防范到治理的轉變。行政的目的不是僅僅以管制手段實施,而需要在給付中實現,城市政府需要完成從管理到服務的轉變。
我們還要略微論及管理體制。目前在全國普遍推行的城管綜合執法,在集中行政執法資源、提升效率的同時,客觀上使得管理者不直接執法,執法者不參與管理政策的制定,因此城市治理者需要進行更周密的制度安排。
城市治理是一個開放包容的主題,城市政府需要在新的社會背景下不斷探索城市治理和行政法治的路徑,思考城市政府作為公共給付主體的職能及其實現方式。當然,這也是人大需要同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