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or管理危機
葉麗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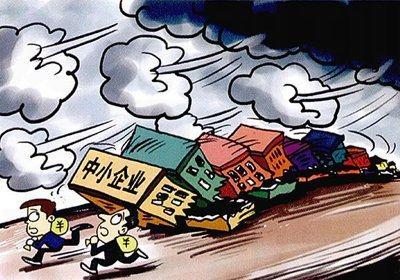
市場自有其運行規則,尤其是在溫州,不需要救助也能自行治愈。
對企業主來說,2011不是個好年頭,而在瑪雅人的預言下,2012也被籠罩上了濃重的陰影――危機似乎是擺不脫的影子,讓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小業主們無所遁形,恨不得都人間蒸發了了事。尤其是在民營經濟超級活躍的溫州,地獄式的2011之后,經濟衰敗,人人自危,而且前途未卜。
溫州人的2011可謂糾結,整個兒一話題女王的范兒:上半年是瘋狂的高利貸,高峰時期利率達到30%,早先還在侃侃而談事業理想、人生目標的富二代們都轉行做了放貸者;中間一輛追尾脫軌的動車又把他們的古道熱腸展示在世人面前;動車事件的結果尚未出來,“十一”黃金周之前,溫州最大的眼鏡廠商之一信泰集團老板胡福林破產逃亡,把老板“跑路潮”推向高峰——據說今年一共跑路了大大小小共90余位老板,一時間媒體熱議“溫州模式已死”。接下來溫家寶攜周小川、劉明康訪溫,溫州提出制定《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將上報爭創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不知是否因此傳出了“中央該不該救溫州”的討論,反正外至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日報》,內至地方媒體乃至網絡達人都紛紛參與熱議,90%以上的意見大致都是在講,溫州老板“活該”,溫州老板“素質低下”,早年賺的都是“流血的利潤”,政府“徹底不該救市”。
結論可能是對的,推論卻難免有些世俗的仇富和自以為是的清高。事實上,就此次金融危機,溫和的自由市場論者也指出,市場自有其運行規則,不需要政府救助也能自行治愈。尤其在溫州這塊基本上純市場經濟的地方,市場會在每輪危機的時候自我篩選淘汰一批已經沒有太大競爭力的企業,催生一批新的商業模式。這些新商業模式不見得會是高利貸,但誰也不知道做過高利貸的年輕后生在這一波危機慘敗之后獲得哪些教訓,下一波創業他們又可能有些什么樣的新鮮點子。而市場則在這一波一波的創業者手中逐漸成長。所以,說“溫州模式已死”多少有些噱頭的意味。
君不見,每隔三五年都會有一輪所謂危機。不用看很遠,就在最近的15年中,溫州危機,或者說中國民營企業所遭遇的危機有因為全球經濟泡沫破滅,有因為國家一個宏觀調控政策,有因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有因為國退民進,也有因為房地產政策緊縮。每到這時,就會有民間所謂經濟學家跳出來說“4成企業消亡”。一個關于浙江省,但可以類比溫州市的數據顯示:2011年1~9月,浙江省消亡企業數為2.5萬家,比2010年略增5%;但2011年1~9月期間,浙江省新增企業數10.5萬家,比2010年同期增加10.35%。浙江省各類中小企業總數有310多萬家。
關鍵并不在于有多少企業倒閉消亡,有多少老板跑路上吊自焚,甚至也不在于有多少企業新設,創業型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每三五年,總有一批企業會因為各類原因走向消亡。這時候,如果再碰上國家一個收縮性政策,或者大西洋、太平洋彼岸一場金融風暴,如同兩個同時走向波谷的波疊加,危機效應就更明顯了。可見各種宏觀危機只是加速了企業的消亡而已。
事實也是如此,不論宏觀環境多么緊張或寬松,每個企業的倒閉最終肯定是是因為自己現金流繃得太緊,以至一有風吹草動企業就緊張不已。所以,與其說是金融危機,倒不如說是企業的管理危機。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了33年后的今天,創業者們已經不是當年一窮二白的狀況,而擁有土地、設備、原材料以及勞動力等所有一切的生產資料的價格,說“身價百倍”也是毫不夸張的,這讓企業在轉型升級之時面臨巨大的財務風險,這也是此次大量倒閉企業都牽涉多產業投資的原因之一。
經濟學定義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周期性的,每隔三五年都會有一次,危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附屬物,會打破經濟體原來的固有平衡,但致不了命,找到新的機會還會東山再起。這時候,終結者就要動用他們的口頭禪含恨離開――“I will be back!”等到下一波企業自身弱點集中爆發的時候,它會再度上場。
危機并不可怕,是企業成長過程中每隔一段時間必然要經歷的一次轉折,企業能做的就是在資金管理、供應鏈管理以及其他一切能夠顧及的方面來準備好自己,隨時防范金融危機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