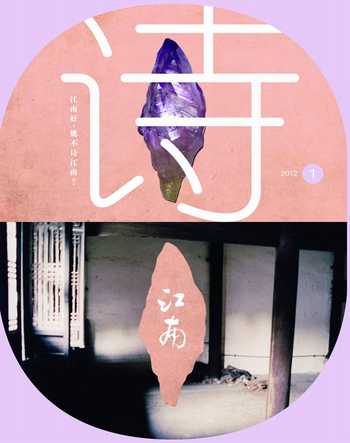走向融合的自然詩
吳澤慶
在西方現代詩人之中, 威斯坦·休·奧登 (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 被認為是繼葉芝和艾略特之后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詩人,甚至形成了以“奧登一代”來命名英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文學史概念。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英美詩壇的地位顯赫,受到學院派批評家的強烈推崇。1953年,奧登獲博林根詩歌獎, 1956年獲美國圖書獎,1967年獲得美國文學勛章。1956 年到1961年任牛津大學詩學教授。奧登在其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作品頗多、詩風多變、思想上變化多端、技巧上諸多實驗,引起了詩歌界的廣泛關注。
進入50年代,奧登開始了他的自然詩創作,《田園詩》是這階段的重要作品之一,詩中隨筆式寫法,從容、冥想和口語化特點展示了奧登后期作品中的和解精神,他的自然詩融合了心理、宗教、愛情、道德、文化和社會等因素,標志奧登已擺脫了40年代的狹隘的存在主義危機。
奧登對自然的看法沒有沿襲任何一條傳統的道路。艾倫·羅德威在他的《奧登序文》中談到,“奧登的自然詩沒有喬治亞詩風對大自然景色的單純描寫,也不同于十九世紀詩人的自然詩是對工業化社會的逃離,更不是浪漫主義詩歌中那種對人的內心世界和普遍精神的探索,也不是十七、八世紀的很多詩人通過自然詩實現對上帝的認識。”[1] 奧登的自然詩在很多方面都獨具創新,它融合了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生態學等諸多學科,涉及歷史、經濟和文化等諸多因素。喬治·W·鮑克在《后期奧登:從新年書簡到關于房子》中談到,“人性特點在自然中的顯現成為奧登的自然詩的特點。”[2] 在《田園詩》中,人的品性和情感與某些地貌密切關聯。《田園詩》的七首詩探討了自然以及自然對人類的影響,反映了人類態度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過程,探討人類歷史的主題,從廣義上看,就是所有的人類活動,包括自然背景如何定位歷史方向的發展方式。詩中自然受人類的支配,并且常常向壞的方向發展,這些設想與傳統的田園詩的主張是相反的,從傳統意義上說,自然是不變的,永恒的,為文明的都市人提供一個隱居地,一個避難所。
《田園詩》中七首詩中的每個地理現象都顯示奧登描寫的天賦,詩中對道德進行了嚴肅探討,反映了奧登對生活的美好愿望,表現了一個局外人試圖嘗試重新和自然建立密切的關系,它們中有六首詩是關于地點的。《風》的開篇喜劇色彩明顯,接著逐漸來揭示一個深奧的真諦,那就是基督對人類的愛。在《高山》中,山區被描述為一個“有著自己的度量和閑聊風格的”世界。象征著逃脫的《島嶼》是一個圣徒向往的地方,因為在那“沒有女性的骨盆能夠/威脅到他們的精神之愛”。
奧登以《風》作為開篇,約翰·富勒在他的《奧登導讀》談到,奧登在詩中把風看作上帝吹給人類鼻孔中的生命之氣,都市是墮落之城,這是人類欲望的惡果。“我被愛,故我存在” 是類似笛卡爾關于自足的觀點,不是從上帝的愛的角度來闡明,上帝的愛對人來說是必不可少。[3] 因此,獅子沒有和孩童躺在一起,可能因為上帝選擇了愚蠢的動物,如果上帝選擇了魚,昆蟲等節肢動物,世界就不會死亡。這樣的神學的冥思被風化所取代,對風化的關注成了“展示我們的真實之城的影像”,這里,“真實之城”和上文的“墮落之城”形成鮮明的對照。詩人向“風與智慧的女神”祈禱靈感,挽救他不去胡亂書寫,警示他所歌頌的主題的純潔:“地球,天空,幾個可愛的名字”。在這里,風是無重量的、沒有名字的,只是流動的空氣,不過,這里的風是上帝吹給人類的神氣,它賦予人體以生命。現在人類始祖的子孫對風帶來的后果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或孤立地,或陪伴。詩似乎在勸導人們去放棄風,然而,人們產生了猶豫。“風與智慧的女神”被要求去把亞瑟·歐·鮑沃(童謠中風的名字)接來,以讓空氣清新。 風是來自“風與智慧的女神”的祈禱,祈禱一種力量能夠激發詩人的想象,這展示了奧登書寫《田園詩》的真正意圖。奧登希望對現世的事物進行贊美,以記憶美好的事物;詩探索了大自然的美麗的各個方面,把它們看作上帝在人類身上的一種神性創造和靈感來源的體現。
《風》之后的六首詩中的口吻是一個對鄉村的拜訪的城市人。艾倫·羅德威在《奧登序文》認為,奧登的詩歌反映了一種思想不斷調整的狀態,從滑稽的知性主義到具有愛意的嘲諷,再到傷感式的樂觀主義,詩中將智慧、學識、感知和鮮明的觀點雜糅在一起。[4] 《森林》是對一個墮落的人的弱點的一種充滿滑稽式的關愛,奧登以一個文雅的講述者的姿態在詩歌中出現,對人類所在的森林娓娓道來,詩歌的語調表面上看是諷刺的、戲仿的、自我解嘲的,但整體上看,詩歌的內在中蘊含著一種略帶幽默的嚴肅。詩勾勒了人類在史前、歷史上與森林的關系,著重探討了森林與現代人之間的聯系,并且論述了這種關系的重要性。在這里,人類的墮落的故事在不斷地重述,“一個鮮活的果實,一片垂落的葉子,/用私密的言語來講述身世”,然而,這個地方依舊和伊甸園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詩的魅力就在于奧登運用的技巧,沒有采用歸納性的語言,而是通過一種具有象征性的類比來揭示人類生活的深層真諦。詩歌揭示了史前時代先人還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先人生活在被兇殺,吞噬的危險之中。隨著詩中的描寫進入現代,森林不再那么危險,甚至對于戀人來說,森林充滿了無窮的魅力,詩歌的語言也增添了現代的意味,揭示田園背景下對人的尊嚴的思考。詩歌思考自然界和人之間的物質關系,森林的樹木是人類的書籍和棺槨的材料,它們意味著生存和死亡,樹木的用途和語言學者聯系起來,讀書是為了習得自然的語言,因為森林里有無法破譯的摩爾斯電碼,奧登在這里談到了讀者、布谷和鴿子的言語,自然的語言成了奧登探討的主題。
與《森林》相比,《高山》所闡述的主題觀點帶著偏見,引發人們的好奇感。詩歌語氣尖刻,對詩中所體現的安全和舒適的思想提出挑戰,也揭示了“要掌管人類”的難度,詩中寫道:“冰與石的天使/日夜守護她身傍,明確表示/他們厭惡任何生長”。奧登的詩中的高山多是代表某種挑戰,而在這首詩中,對于挑戰奧登采取一種隱退逃離的態度,從而表明,對于高山只能遠觀,遠遠地欣賞它的魅力與壯觀,不能靠近。而《湖泊》中的“湖泊”的大小適應家庭使用,他在詩中寫道,任何大的湖泊,盡管湖水可飲用,卻是一個‘不友善的海。“湖上的氣氛”可以營造一個好的氛圍,奧登認為湖泊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進行和談的地點。一個大小適度的湖泊甚至對于一個就要被溺死的人所堅信的宿命論具有很大的魔力,這種思想在《湖泊》的最后幾節中也得到了明顯的體現,一個人在保護自己的理想圣地上是勇敢的,甚至富有挑釁性。地球上的美好不僅體現在可見的事物的外在方面,也內化為它們所表現的天真和愛中,湖的贊美是源于湖的樸實和寧靜,第一次的教派會議就是在卑斯尼亞的阿斯卡尼亞湖舉行;湖是進行和平談話的最佳的地方,湖是一個“流動的中心”,它能夠幫助軍隊交戰的雙方走向和解,重新恢復友誼。城市中提供飲用水的水庫讓人產生內疚感,這與在湖上盛行的愛的氛圍形成鮮明的對比。 愛德華·門德爾森的《后期奧登》認為,“奧登希望找到一個安全的審美伊甸園,因為他知道自己身處一個充滿暴力的不安全的世界。”[5] 他把湖泊看作自己的避難所,他寫道,一個愛湖者對仁慈的自然的偏愛,這種偏愛和自我保護是相伴相生的。奧登的詩揭示了現代世界中無所不在的、令人不安的暴力意象,因為這種暴力就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詩歌中的 “島嶼”通常來講是人們的避難之處,而奧登的詩中島不是一個避難所,奧登采用簡短的四行詩體形式,島嶼上出現了圣徒、海盜、罪犯和土著居民、暴君、詩人和日光浴者,這個本是逃避的地方多次出現了不平等現象,存在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在民主的赤裸下/兩性在撒謊:除非/按年齡或重量你無法區分/撫養者與被扶養者。”同時,島嶼吸引著利己主義,“多么迷人的階層/我是其中唯一的成員!”。而《平原》中“平原”地貌沒有固有的形式和方向,平原是夢魘之地,對詩人意味著犧牲,詩人雖然渴望擁有兩個出口的洞穴,他并不是掌握權力的人,詩表現了邪惡的普遍存在。
與“平原”的夢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溪流”展現了一個充滿愛的田園風景,這里的水是純凈的,象征著一種天真無邪的狀態,水嘲笑人類利用它們的動機,在這個利用里,它超越人的控制。但是作為對人類理想的一種神圣的祝福,它成為夢想的推動力量,象征著優雅。愛德華·門德爾森的《后期奧登》認為,“ 溪流不同于其它地點,這里沒有暴力,這里幻想伊甸園的存在。”[6] 詩中所提及的“在那個有著所有約克郡秀美的溪谷”恰恰是奧登在寫這首詩前幾周去過得那個溪谷,他認為那是一個神圣的地方,在那里,“凱斯頓·貝克/發出孩子般的叫聲,跳進沼澤地”,而我也“撲在草地上,小憩一會。”在這里,奧登把婚戒和舞者的圓形舞臺類比。奧登在“溪流”中水的希望是一種真正的個人的愛的象征,《田園詩》中的水所帶來的安慰特別指的是一種母性的愛。《湖泊》中提到每個人在出生前都是“羊膜湖的天才”(這里的羊膜湖指的是子宮),而在《森林》中,孕育人類的那個沒有墮落的樂園會被永遠記住,“故去的人,聽盡幾近終了的悲傷,/聽到,或遠或近,他的最古老的快樂,/就是那個樣子,水的聲響。”在《海與鏡》中,這命運之水變得平靜,變得寬大慈悲。奧登對溪流進行了贊美,溪流是“純凈的生命,在音樂和運動中完美”。詩人認為純凈和天真的溪水“講述某個世界,完全不同的,/與這個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 這個世界不同于我們現實的世界,它充滿了仁慈和普愛,詩末通過一種夢境的形式展現出來,夢境中的歡快和幸福體現了一種思想狀態,一種沒有焦慮和內疚的思想狀態。
奧登相信自然的“他性”特征,認為人不僅是自然界的高級動物,而且具有靈魂的存在。奧登的自然詩基本是關于人的詩歌,《田園詩》中的典型地貌反映的是不同類型的人,詩中的高山、平原、溪流等吸引著不同的人,反映著人性的不同側面。詩歌中的自然景色揭示了人的關注,也恰恰揭示了奧登自然詩中對自然景觀描摹的獨特之處。高山、平原和溪流沒有什么本質的差異,都是自然界中中性的、不附帶精神意義的客觀物質,然而,在奧登的自然詩中,這些客觀物從人的角度闡述描摹,實際上,奧登借助于自然界,間接地談論人的狀況。
奧登不同于偉大的象征主義詩人葉芝,奧登詩中的意象運用是為了達到諷刺的效果。與艾略特也不一樣,艾略特的意象是經驗的客觀對應物,而奧登的意象是建立在寓言框架中,賦予意義以思想內涵。奧登的《田園詩》大量運用原型意象,展示了奧登詩學能力,尤其是在地貌象征技巧方面的豐富和延伸。這些詩篇中的細致描摹清晰地體現了奧登詩的深刻思想內涵。奧登不斷地強調自然的原初世界和后來的藝術世界是不同的,他對自然當作一種神圣的王國來贊美。塞瓦斯塔瓦·納森認為,奧登作為詩人一直在尋求外在事物和思想之間的一致統一,他通過自然的事物來展現精神世界。[7] 他的自然詩不是純粹的感性描述,詩充滿可見事物而非感性的東西。對他來說,自然界是人類生活真理的主要來源,他的詩用象征意義的自然地貌來表現藝術家的生活和性格,進而展現深刻的思想。奧登把冷靜地思考和敏捷的智性理解進行結合,并體現在個人、公共和宗教等因素的有機結合上。
[1] Rodway, Allan. Preface to Aude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84. p.138
[2] Bahlke, George, The Later Auden: From “New Year letter” to “About the hous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5
[3] Fuller, John. A Readers Guide to W. H. Au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0. pp.218-220
[4] Rodway, Allan. Preface to Aude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84. p.139
[5] Mendelson, Edward. Later Au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386
[6] Mendelson, Edward. Later Au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387
[7] Srivastava, Narsingh. W.H. Auden, a Poet of Ideas. New Delhi: S. Chand, 1978. p.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