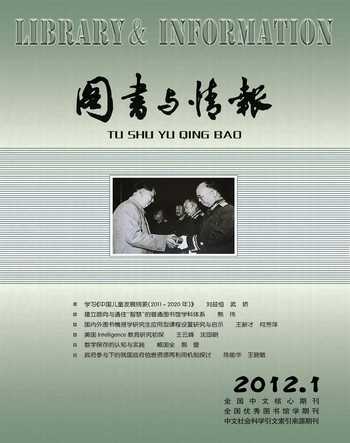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


摘 要:提升智慧水平是人類用戶求索知識的核心價值目標,應該以“智慧”為當代和未來圖書館學的“學科面向”。在明確定義“智慧”概念和把握協同用戶培育“智慧”路徑的基礎上,原則上能夠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應深刻轉變思維方式,探索建立“客觀知識本體”研究范式,重點突破“客觀知識關聯說”和“全信息微計算技術”等關鍵難題,積極組織跨學科合作攻關團隊,加快該理論體系建立步伐,把圖書館學真正推向成熟階段。
關鍵詞:圖書館學科體系 公共智慧服務 客觀知識本體 客觀知識關聯
中圖分類號: G250.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2)01-0004-06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General Library Science Facing and Leading to Wisdom
Abstract Raising the level of wisdom is the core of value target that users quest after knowledge. "Wisdom" would be the goal of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library science.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general library science facing and leading to wisdom would be established theoretically, and based on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wisdom" concept and the grasp of collaborative user breed. We should greatly change our way of thinking, explore and buil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Ontology of Objective Knowledge", and also breakthrough key problem such as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knowledge association" and "All Information Modeled Micro-Computing Technology ", and actively organiz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teams, and speed up its pace for really establishing mature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discipline system of general library; public wisdom services; ontology of objective knowledge; objective inowledge associatio
1 引言
圖書館學目前還是一門成長中的年輕的新興學科。“成長中”意味著其學科面向“尚不穩定”,“年輕”意味著其學科性質“尚不確定”,“新興”意味著其學科空間“尚不明朗”。然而,在新的千年里,它應該也必須走向成熟了。學科面向集中反映著一個學科擬實現的核心研究目標,而如何設定該目標取決于我們對該學科的“前見解”或者說是“前理解”。“前見解”陳述了研究者試圖回答或解決什么問題,為什么研究這些問題,鮮明地表達著研究者的基本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1]。一般來說,一定學科面向決定著一定學科性質,而一定學科性質決定著一定學科空間。因此,當代圖書館學科建設在明確學科邏輯起點——“核心論域”[2]的基礎上,必須進一步合理設定自己的邏輯終點——“學科面向”。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學術界對圖書館學科“面向職業”的最新設定 [3][4],是“如吾所識”思維方式下的“實用”設定。然而,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在用戶、社會和人類等立場上對圖書館服務價值問題的認識,例如,在人類立場上,圖書館是人類永久記憶客觀知識精華的社會機制[5]。更為關鍵的是,圖書館運動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性運動現象,有著關于主體、中介、客體和背景等方面的一系列運動規律[6],并不是“面向職業”的學科建設所能概括的。遵循所有這些圖書館運動規律發展圖書館事業和開展具體圖書館工作肯定能夠確立起統一的最終價值目標。就像面向職業的“臨床醫學”學科建設只能是醫學普通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面向職業的理論體系”只能是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下圖書館學積極回應和解決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用戶有效需求的“核心能力尚不充足”,集中表現在:目前的圖書館事業和工作只是常說文獻服務,大說信息服務,慎言知識服務,稀言智能服務,不言智慧服務。在新的千年里,學界應該正確認識“客觀知識”與“人類智慧”的辯證轉化關系,合理設定圖書館學的“學科面向”。在提出當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核心論域”[7]基礎上,經進一步的參考與論證,筆者鄭重提出:由于提升智慧水平是人類用戶求索知識的核心價值目標,應該以“智慧”作為當代和未來圖書館學彰顯自己核心能力的“學科面向”,努力探索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盡快把圖書館學推向真正成熟階段。
2 為何建立面向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
“智慧”問題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看似“務虛”的問題。《新華字典》給出了“智慧”的一個功能描述性定義:“對事物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智慧”是一種優秀能力,是人們實際生活的基礎。從后者角度看,雖然討論“智慧”問題是一個“難題”,卻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確實有益人們生活的問題。
“人生在世”都會面臨如何“安身立命”的現實問題和“安心立意”的理想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如何處理“目的確定”與“手段選擇”的關系。一般來說,每個人都會通過對人生意義的覺悟來確定特定性質的目的,即“慧”定所信奉的“德性”,同時,每個人都會通過開動腦筋并“合乎規律”地選擇一定的手段來實現特定性質的目的,即“智”運如何達成目的的“方法”。因此,選擇什么樣的“方法”來實現所信奉的“德性”是一個“智慧”問題,而“方法”與“德性”有機構成著“智慧”活動的基本內容。
“人生在世”是一個現實的有限人性問題,也是一個理想的無限天道問題。這決定了“智慧”幫助人們“安身立命”和“安心立意”的極端重要性——既近切啟示又宏遠關懷。凡是正常的人,無不自覺追求“智慧”,也渴盼得到來自各方面的智慧服務。至于學科,亦是如此。除了哲學坦率地宣稱自己“愛智慧”并被人們稱之為“智慧之學”外,迄今為止的所有學科也都是“愛智慧”的并以面向智慧并具有智慧品質為榮。因此,建立面向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既合乎“人之常情”又合乎“學之常情”。
無庸質疑,人類用戶利用圖書館的活動是典型的求索知識的專門活動。就目的層次而言,無論是“休閑娛樂”的目的還是“學習提高”的目的,無論是“完成任務”的目的還是“科學研究”的目的,都不能說是人類用戶所希望的最終目的,人類用戶求索知識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希望獲得至上智慧。就效果層次而言,從易得知識形體、易知知識內容、易用知識功能到易悟知識思想,都不能說是人類用戶所希望的最高效果,人類用戶求索知識的最高效果應該是:真正形成至上智慧。概言之,提升智慧水平是人類用戶求索知識的核心價值目標,建立面向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是圖書館學科發展的應有之義。
圖書館學自產生以來,先后提出并形成了“面向工作”、“面向機構”和“面向職業”的學科理論體系,代表著其發展的真實軌跡。在高度肯定它們歷史成就同時,我們必須深刻反思其根本不足:首先,把 “學科立場”尚定位在“圖書館行業主體立場”層面上,具有“狹窄性”與 “封閉性”;其次,把“學科性質”定位在“專門應用學科”的層面上,具有“初級性”和“簡單性”;再次,把 “學科品質”尚定位在“實用精神”的層面上,主要關注眼前“怎么做好”的問題,然而,沒有“怎么看——有什么”、“怎么想——為什么”和“怎么算——做什么”等合理前提條件的支持,“怎么做”很容易日益陷入“思路枯竭”的陷阱,同時,缺乏 “遠見” 的支持,可能導致圖書館現實活動中會更加“正確”地做好已經“不合時宜”的事情;最后,把 “學科發展”定位在“外延擴張”層面上,使圖書館學整體呈現“泛化”發展的態勢,然而,對于提升學科“內涵”所必須解決的“知識發現”、 “智能呈現”、“智慧涌現”等關鍵問題卻關注不足,更未在高級公共智慧服務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因此,目前的圖書館學科體系還不是憑借社會公認的”核心能力”立足的成熟的“探索——描述——解釋”系統。
人類社會進步之“風”吹“圖書館”之“幡”動,如果沒有人類用戶的“仁者心動”,二者對于人類用戶都是非相關的。面向“工作”、“機構”、“職業”的圖書館學,主要是圖書館從業者關注的圖書館學,惟有“面向智慧”的圖書館學才能通往人類用戶心靈深處,可以支持人類用戶以智慧方式來“安身立命”和“安心立意”,自然會被全社會高度認同。歸根到底說,圖書館學是人類的圖書館學,并非某個時代與某些行業或研究者可以局限的特殊圖書館學說,其 “學科面向”必然會不斷發生新的具體“轉向”,并將勢不可當地繼續朝前發展。智慧形態是知識運動最高級的形態,培育智慧是人類一切知識求索活動的最后歸宿。以“客觀知識求索活動”為中心問題的圖書館學,更應該有著“面向智慧”的精神追求。因此,“面向智慧”是圖書館學最高也是最后的“學科面向”,建立面向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乃是圖書館學科發展的必由之路。
3 能否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
學界對于“建立面向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必要性不會有太多的爭議,真正的質疑在于其可行性,即“能否建立”。 一般來說,目標的合理性應包含手段的可行性 [8],而手段的可行性可以反過來證明目標的合理性。現在,已無必要重申所謂“精衛填海”或“愚公移山”等人文精神,“宗教般”強調“信念”的力量,“蒼白地”堅信總回有一天能夠實現這個目標,應該選擇的是方式對“智慧”進行明確定義并系統闡明其可行性的道理,即只要能夠系統解釋其在什么條件下、選擇什么路徑、采取什么方法來具體地協同用戶把“客觀知識”轉化為人類“智慧”,就可以證明其可行性。
在參考學界前輩關于知識[9]、智能[10][11]和智慧[12][13][14][15][16]問題探索成果的基礎上,筆者嘗試對“智慧”概念進行如下定義。所謂“智慧”,是人類合規律性、目的性與效果性相統一的融會貫通能力,即合規律性的“智能”與目的性的“慧覺”高度統一的有效能力狀態,是理性自由活動以及理性與非理性的協調發展的積極成果[17]。其中,“智能”的本質是:針對特定問題和目的而有效獲得信息和處理信息,形成求解復雜問題的結構和策略,從而成功地達到目的能力 [18]。由于人們常稱“結構為方要,策略為權法”,所以“智能”通常表現為“方法”的選擇;“慧覺”的本質是:在大量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基礎上,發現問題價值目標的模式和邊界。由于“問題價值目標的發現模式”可稱之為“德之規范”,“問題價值目標的發現邊界”可稱之為“性之界定”,所以“慧覺”通常表現為對問題“德性”的確定。統一“智能”與“慧覺”的橋梁是基于“事實判斷”的“價值判斷”,即“方法”的特定功能對于“德性”發展狀態的積極效果,因此,“運智達慧”是“智慧”思維的基本方式。作為人類思維對象的“智慧”,客觀存在著如下的基本層次結構(見表1),從而能夠呈現出探索發現問題、系統解釋問題和妥善解決問題的強大能力。
在表1中,人類“智慧”中的“智能要素”、“慧覺要素”及其“能力水平”被確定為六個水平層次:第一層次在于明了生活之基礎;第二層次在于無違客觀之規律;第三層次在于合乎社會之規范;第四層次在于理解境遇之契合;第五層次在于堅定行動之意志; 第六層次在于獲得真實之自由。之所以把“識實”作為“智慧”的最低層次,在于強調把握實際情況,堅持從實際出發來認識和改造世界,是人類世界活動最基本的要求,之所以把“易行”作為“智慧”的最高層次,在于強調創造性實踐活動既是知識的出發點又是知識的歸宿點,惟有創造性地改造世界,才能獲得“果然”之自由。“果然”強調真實的自由是人類立足實然,認識必然、確定應然、選擇當然和能夠使然的綜合結果,這是它與片面強調現實效果的“實用”精神的根本差異。總之,惟有憑借整體的“智慧”,我們才能真正“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所面對的問題。
按照以上對“智慧”的定義,圖書館通過建構人類客觀知識精華的全信息時空,并充分發揮其整體效應作用,沿著“化理論為方法”和“化理論為德性”[19]這兩大根本途徑,協同用戶從客觀知識出發獲得各層級水平的智慧能力是完全可能的。首先,圖書館通過系統地傳播知識和信息,幫助用戶較為全面地了解現實世界,為其現實生活提供最一般的理解和解決問題的基礎;其次,圖書館通過幫助用戶“易得”、“易知”、“易用”和“易悟”知識,與“有史以來的整個人類知識精華體系”對話和交流,對于有力支持用戶探索和發現真理,具有其他主體力量所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再次,圖書館通過對用戶進行有導向的道德規范教育,不僅讓用戶知曉當今道德之然,也讓用戶知曉當今道德之歷史淵源及未來態勢,強化用戶的“向善之心”。更為重要的是,圖書館將通過在順序的事件序列中和并序的事件集合中,不斷開闊用戶的知識眼界,協同用戶日益強烈地反省自己或來自無知或來自傲慢的“偏見”,逐步培育“正見”世界關系的能力,進而洞察“民胞物與”的倫理大境;復次,圖書館將通過對人類客觀知識精華之間復雜關系的揭示,啟發用戶強烈感受人類客觀知識精華所反映的人類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多樣之美、廣博之美、幽深之美、融合之美和靈動之美,強化用戶的“審美之情”;又次,圖書館將通過對人類客觀知識精華中所蘊涵人類思想、人類精神和人類氣節的挖掘和彰顯,啟發用戶知曉什么才是這個世界真正永恒不朽的“對象性”存在,應多做有利于祖國和人民的事情,強化用戶的“信仰之志”;最后,圖書館將通過揭示人類實踐歷程與人類生活自由水平提高的相關性,啟發用戶勇于創造性地實踐,為達到“果然”之自由狀態而努力奮斗,達成用戶更高水平的“易行之通”。總之,圖書館支持人類自由地永久記憶客觀知識精華的努力,不僅為人類社會生活構建了基于對客觀知識內容“共識”和形式“共示”的公共認知與價值意義空間,更為人類“智慧”之樹自由成長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鮮活的客觀知識資源。
客觀地說,迄今為止的圖書館在啟益用戶智慧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果說還有什么根本性的不足,就是它尚未完整建構人類客觀知識精華的全信息時空,尚未充分發揮“如其所能”的整體效應作用。驀然回首,我們會驚覺,如果沒有人類對自然界微觀世界的探索,就沒有今天的自然科學技術進步,也就沒有人類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現在的圖書館只是打開了通向人類客觀知識精華宏觀形態及其社會運動的大門,還在以客觀知識單元的宏觀運動為中心,探討圖書館工作、圖書館組織和圖書館職業等“宏觀層面敘事問題”,尚未成功打開通向人類客觀知識精華微觀形態及其復雜運動的大門,沒有以知識元、知識分子、知識原子等微觀知識粒子的運動為中心,系統而深入探索和發現人類客觀知識精華微觀世界的運動規律問題。主要考察和解決客觀知識精華單元社會宏觀形態運動問題是人類用戶目前尚難以通過圖書館“易得”、“易知”、“易用”和“易悟”人類客觀知識精華的根本原因。而沒有上述“四易”,圖書館要全面深入開展“公共智慧服務”肯定“不易”。
經過較長時間探索,為了真正打開圖書館通向人類客觀知識精華微觀形態及其復雜運動的大門,有效轉化知識產權保護與知識資源共享的矛盾,完整建構人類客觀知識精華的全信息時空,大力支持圖書館全面活化“客觀知識”,并通過“轉知成識”、“轉識成智”和“轉智成慧”等三大環節,幫助人類用戶獲得智慧能力,也即能夠“轉知成慧”,筆者初步提出了一個“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行動路線圖”(見表2)。
在表2中,七個基礎理論與對應的七個核心技術是圖書館開展高級公共智慧服務的相輔相成的層級性實現條件。換言之,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思想路線是:依次解決好“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算”、“怎么辦”、“怎么樣”等思維方式轉變問題[20];其理論路線是:依次解決好 “超限世界觀”、“廣義知識論”、“客觀知識生命論”、“客觀知識本體論”、“客觀知識關聯說”、“大成智慧建構論”、“可能知識生活論”等理論發現問題;其技術路線是:依次解決好“融界方法論”、“柔性邏輯論”、“廣義計算語言論”、“科學語言本體論”、“全信息微計算技術” 、“超級高等智能工程”、“超循環知識生態論”等技術發明問題。統籌這三條實現路線的核心思路是:以“轉知成識、轉識成智、轉智成慧”為價值主題,在人類用戶的積極參與下,致力促進客觀知識在“事實—符號—數據—信息—知識—智能—智慧”這一人類記憶水平生態鏈中開展“如其所能”的日益高級的自由運動,最終幫助人類用戶形成一定智慧成果。至此,能否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問題可以具體化為我們能否創造支持圖書館啟益用戶智慧的各個層級的理論與技術條件問題。
能否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富于智慧的建立者。因為,富于智慧的建立者對于圖書館學研究現狀的理解,不在于其“封閉自洽”的“實在”性,即發現圖書館學已經有什么獨特內容,而在于其“感應天人”的“空”性,即發現圖書館學還缺乏什么獨特內容,特別是相對于人類用戶的多元需求,圖書館學還有什么未曾充分關注。富于智慧的建立者對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在于其“畫地為牢”的“專門”性,即采取某些專門的研究方法,而在其“契同萬物”的“一般”性,即采取所需要的任何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富于智慧的建立者對于圖書館學研究境界的理解,不在于片面強調“自覺利己”性,而在于更加強調 “覺人利他”性,而最高的“覺人利他”性就是,整合協同“人智、物智與群智”來啟益用戶智慧,并在此境界激勵下,全面開展相應的攻艱克難工作。
3 怎樣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
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學科體系是今后較長時間圖書館學科建設的基本任務。大約經過十年的努力,可望初步建立起其該學科體系。目前,主要提出四點建設意見。
第一,深刻轉變思維方式。總體要求是從產生“多元并立”學科體系的“如吾所識”的經驗色彩轉向產生“多元一體” 學科體系的“如其所能”的理論色彩。實現從“如吾所識”向“如其所能”的思維方式轉變的標志是確立“超限世界觀”及與之相適應的“融界方法論”。所謂“超限世界觀”,是指信奉“平行世界-關聯世界-可能世界-虛在世界”四位一體存在的無限世界觀,把“單一世界-實體世界-現實世界-實在世界”四位一體的有限世界僅作為“平行世界-關聯世界-可能世界-虛在世界”四位一體的無限世界的一種暫時的呈現形態,從而肯定世界事物的發展本身有著“如其所能”的無限潛力。所謂“融界方法論”,是指信奉“科學方法無定界、重在融會能貫通”的方法論,按照所能形成的客觀效應把科學研究方法分為把握實然、探索必然、明確應然、選擇當然、能夠使然和實現果然等六類基本方法,認為果然效應是前五種方法的高度協同應用的綜合結果,表示達成了預設事實狀態和價值目標,是人類一切努力奮斗的真實目的。
第二,探索建立新研究范式。應盡快從傳統圖書館學的“客體—中介”綜合范式轉向新時期的“本體—客體—中介—主體”綜合范式 [21]。該綜合范式的內容實質是“客觀知識本體”范式。該范式之“新”在于:探尋并建立起圖書館學的核心論域,即 “人類永久記憶客觀知識精華的社會機制”,以核心能力進化為價值導向,以有著特定結構與功能的客觀知識精華本體的社會運動為中心,來考察圖書館社會形態演變規律和明確其應然的社會定位;堅持高等智能觀,強調通過基于科學語言本體和全信息微計算的、日益高級的客觀知識關聯,來構建涵蓋客觀知識精華本體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的全信息時空,用于呈現無限可能的“人類世界客觀知識精華整體圖景”;堅信圖書館具有推動人類自由記憶客觀知識精華的社會使命,可以通過使人類用戶享有可能知識生活方式促進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目前,以“客觀知識本體論”為核心內容和以“科學語言本體論”為表現形式的“客觀知識本體”范式正在探索形成之中。為了加快其形成步伐,從理論發展角度看,一方面,迫切需要“廣義知識論”和“客觀知識生命論”等底層基礎理論研究的推動,另一方面,還迫切需要“客觀知識關聯說”、“大成智慧建構論”和“可能知識生活論”等上層基礎理論研究的拉動;從技術支撐角度看;一方面,迫切需要“柔性邏輯論”和“廣義計算語言論”等底層核心技術研究的推動,另一方面,還迫切需要“全信息微計算技術”和“超級高等智能工程”和“超循環知識生態工程”等上層核心技術研究的拉動。
第三,重點突破關鍵難題。從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礎和專項預備研究的情況看,具有承前啟后和牽引全局的關鍵難題是前述“行動路線圖”的第三層次的“究竟怎么算”問題,所涉及的基礎理論是“客觀知識關聯說”, 重在揭示圖書館運動的基本規律,闡明客觀知識精華微觀粒子自由關聯與宏觀形態創造性變換的關系,論述構建全信息時空的基本路徑與模式選擇等問題;其相關核心技術是“全信息微計算技術”,旨在打開通向人類客觀知識精華微觀形態及其復雜運動的大門,重在提出全面支持客觀知識微關聯操作和構建全信息時空所必須的一系列計算方法和解決方案,并開發出相應的操作平臺與應用軟件,它們在圖書館組織機構的安裝與使用,將標志著圖書館具有初步的公共智慧服務能力。隨著這兩個關鍵難題的突破,“大成智慧建構論”和“可能知識生活論”的立論與探索將有可靠的理論基礎,“超級高等智能工程”和“超循環知識生態工程” 的立項與建設將有可靠的技術基礎。進一步展望看,隨著 “可能知識生活論”指導的“超循環知識生態工程”的正式實施,將標志著圖書館作為“廣域的自由知識環境”而具有高級的公共智慧服務能力。
第四,積極組織跨學科合作攻關團隊。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關鍵在于有一批熱愛學術、能力較強、善于合作和敢于攻關的研究團隊。由于強化理論研究與技術開發的跨學科融合是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趨勢,我們必須積極組織一批以中青年力量為主體的區域性、全國性和國際性的跨學科合作攻關團隊,爭取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堅定不移地實施“項目推動研究”戰略,有規劃、分步驟地攻克有關重大研究難題,以期盡快形成全圖書館學界普遍關注和重視該學科體系建設的良好局面。
5 結語
在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下,圖書館必須與時俱進,盡快邁入創造時代,完成從“向用戶提供客觀知識精華資源”到“協同用戶培育和提升智慧能力”的深刻轉變;在明確當代及未來圖書館學研究的“核心論域”(學科建設的邏輯起點)和“學科面向”(學科建設的邏輯終點)之后,建立起面向并且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科體系的主要任務將轉向前述“行動路線圖”中有關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核心技術的開發,特別是對于關鍵難題的重點突破;應堅持 “能力立學”導向,以“關聯資源建設科學”、“微知識計算科學”、“公共智慧服務科學”、“信息素養教育科學”、“價值管理科學”和“計量圖書館學”等新興分支學科為突破口,加快建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體系。該建設歷程是圖書館學雖然艱難卻十分優雅的“核心能力飛躍”,將標志著圖書館學從此走向成熟。
參考文獻:
[1]段小虎.圖書館研究中的事實命題與價值命題[J].圖書館雜志,2006,(6):4-7.
[2][3][20]熊偉.當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客觀知識本體論轉向[J].圖書館雜志,2011,(12):2-11.
[4]劉茲恒,張久珍.構建面向圖書館職業的理論體系:第五次全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討會論文集[M].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前言.
[5]熊偉.根植“知識記憶”:圖書館作為“人類永久記憶客觀知識精華的社會機制”自立在世[J].圖書館雜志,2011,(2):6-12.
[6]熊偉.圖書館廣義本體論導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的重建[J].圖書與情報,2004,(5):1-6.
[7]謝寶媛.圖書館的定義[J]. 圖書館學研究,2003,(7):6,23.
[8]崔鳳雷,程煥文.崇尚智慧至誠服務[J]. 高校圖書館工作,2004,24( 6):14-15.
[9]傅榮賢.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知識說”的反思——從知識之學走向智慧之學的取向[J].情報資料工作, 2009,(1):6-9.
[10]胡軍.知識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1]鐘義信.信息科學原理(第三版)[M].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2.
[12](美)George F.Luger.史忠植等譯.人工智能:復雜問題求解的結構和策略[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13]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14]馮契.馮契文集(第二卷):邏輯思維的辯證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15]馮契.馮契文集(第三卷):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16]馮契.馮契文集(第八卷):智慧的探索[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17][19]錢學森,戴汝為.論信息空間的大成智慧[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18]楊國榮.知識與智慧:馮契哲學研究論文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1]熊偉.論圖書館學范式的形成與轉換[J].圖書情報工作,2004,(5):41-44,55.
作者簡介:熊偉(1973-),男,陜西教育學院圖書文獻與信息傳播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