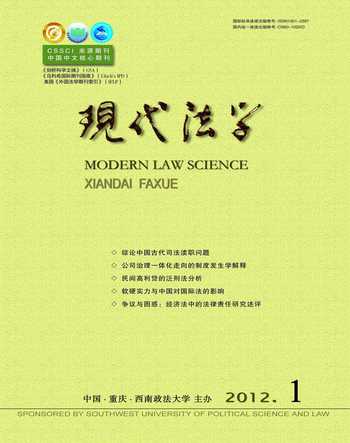論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
摘 要: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是表演者權(quán)但有其特殊性。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顯示出群體性、空間性、一定的傳承性。理論界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類型的界定存在諸多爭議,其中“群體說”體現(xiàn)了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民間根基、權(quán)利主體法定性、創(chuàng)作主體群體性。考量國際立法原則、行為要素、物理要素,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包括國家、民族、種群、種族、傳承人、表演者特定群體。外國立法及國際公約有相應(yīng)規(guī)定,我國無明文立法。
關(guān)鍵詞: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
中圖分類號:DF523 文獻標(biāo)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07
民間表演藝術(shù)是群體智慧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在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中,集體表演占表演類總數(shù)的93.1%。由于民間表演藝術(shù)內(nèi)涵的復(fù)雜性、創(chuàng)作的長期性,國際上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概念分歧巨大,各國立法對其保護也展開激烈博弈。英美等發(fā)達國家堅持傳統(tǒng)版權(quán)理論,認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具有集體性、主體個性不明確性、表達形式的變遷性,否認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獨立保護;民族文化資源豐富的發(fā)展中國家,堅持文化財產(chǎn)的民族性,堅持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的群體性,紛紛立法保護并推動國際立法。縱觀國際理論界或法律實務(wù)界,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確認標(biāo)準(zhǔn)以及類型的確立存在較大爭議。其原因之一是法律關(guān)系的主體并不明確,期待有效保護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的愿景難以實現(xiàn),特別遺憾的是,我國無明確的相應(yīng)法律。在此,筆者將結(jié)合國內(nèi)外立法實踐,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問題提出自己的管見,以期拋磚引玉,推動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一、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的概念
“集體”與“個人”相對,一般是指多個個體為了實現(xiàn)特定目的而通過互動形成的立體結(jié)構(gòu)。“集體”概念出現(xiàn)在各國語言中,如英文中“collective”指“of a group or a society(of persons,nations,ect.)as a whole”(有許多人或民族組成一個整體)[1]。中文 “集體”一詞的基本含義是“許多人在其中工作、學(xué)習(xí)或生活的有組織的整體。”[2]
縱觀“集體”發(fā)展歷史,集體行為都是社會的、歷史的行為,它不同于一般群體行為;“集體”作為人們在社會生活領(lǐng)域(包括藝術(shù)領(lǐng)域)中的基本組織形式,是群體發(fā)展的最高層次。在我國歷史上,沒有“集體”這一概念,但集體制度一直存在,現(xiàn)在的“集體至上”觀念還是人們行動的指南。作為一種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制度內(nèi)涵,“集體”是指為了表演者聯(lián)合體和個人的共同價值、共同活動目的,各表演者結(jié)合成有組織的整體。
基于“集體”基本內(nèi)涵,可以認為表演者集體是指表演者為了聯(lián)合體和個人的共同價值、共同活動目的,結(jié)合成有組織的表演者整體。表演者集體中各表演者有著共同的表演目標(biāo)、共同的表演利益和共同的表演,不僅認識到自己表演對個人的利益,還應(yīng)該認識到對整個組織的意義。表演者集體的最主要特點是開展對表演藝術(shù)發(fā)展起積極作用的共同表演活動,因此,只有集體目標(biāo)和社會文化目標(biāo)一致,集體表演才能成功。同時,各個表演者自愿取得集體資格,集體已經(jīng)成為表演者進行共同表演活動的中介;表演者自愿接受集體價值理念,如:價值定向、集體自決、協(xié)同活動結(jié)果的承擔(dān)等。而且表演者表演活動的整體性是表演者集體的最大特征,整體性表現(xiàn)為緊密的團結(jié)性、高度的整合性以及集體主義的傾向性,各表演者組成有機組織系統(tǒng),表演者之間存在相互合作與制約關(guān)系;表演者集體保護個體表演者利益,個體表演者在行使集體權(quán)時應(yīng)遵循集體的規(guī)則。此外,表演者集體是由表演者個體形成的,在表演者集體中,表演者之間有穩(wěn)定合作的關(guān)系,共同促進表演者集體的發(fā)展;表演者集體保障表演者個性發(fā)展,而且個性發(fā)展和集體發(fā)展相互促進,表演者個性隨集體的發(fā)展而┩晟啤
根據(jù)表演者集體的含義及特征,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可以定義為:表演者集體因集體表演民間藝術(shù)而產(chǎn)生的非違法的利益,即法律上的表演者集體法益。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是以有效的集體表演民間藝術(shù)表達為前提,該表演必須是法律調(diào)整對象;權(quán)利主體是以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為立足點,而非單一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盡管不排斥單一表演者),因此權(quán)利主體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創(chuàng)立者群體;權(quán)利客體即法益具有共同的指向性,即集體表演民間表演藝術(shù)目的所決定的共同利益,如違背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意志或社會公共的利益不是本權(quán)利客體。正如耶林所指出的“主觀權(quán)利是法律秩序授予個人的一種法律權(quán)能,就其目的而言,它是滿足人們利益的一種手段”[3]。在性質(zhì)上,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是表演者權(quán)的一種特例,是表演者權(quán)利體系的內(nèi)容之一,是一種新型綜合性質(zhì)的權(quán)利[4]。
要理解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概念,就要區(qū)分表演者合作權(quán)、表演者集體所有制、表演者共有權(quán)、表演者委托權(quán)等相關(guān)概念。表演者合作權(quán),是指多個表演者之間或者表演者組織為了共同的表演目的而進行相互配合、協(xié)作,進而取得因為表演而產(chǎn)生的共同利益的權(quán)利,是表演者集體權(quán)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表演者集體所有制指生產(chǎn)資料歸一定范圍的表演者共同所有,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一種形式,屬于經(jīng)濟基礎(chǔ)范疇,集體所有制實現(xiàn)的法權(quán)制度就是集體所有權(quán),外延廣于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表演者共有權(quán)是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表演者對同一項表演成果共同享有的權(quán)利,可以分為表演者共同共有和表演者按份共有,表演者共有權(quán)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的內(nèi)涵之一。表演者委托權(quán)是指表演者將自己的表演事務(wù)囑托他人代為處理的權(quán)利,該權(quán)利存在的前提是表演者與他人具有信賴關(guān)系,是派生權(quán)。表演者被雇傭權(quán)與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區(qū)別的關(guān)鍵是權(quán)利主體意志是否得到尊重以及地位的平等性。
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具有一定的特征。權(quán)利對象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即是一種通過特定社會群體或民族長期傳承而進行的非個人的、連續(xù)創(chuàng)作的產(chǎn)物,包括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戲劇、民間宗教儀式等形式。權(quán)利主體是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這個集體可以是一個或幾個民族,也可以是一個或多個村落,還可以指諸多表演者個體的聯(lián)合體;也許不能夠確定具體的個體主體。因為權(quán)利保護時間是建立在對受保護客體可利用價值實現(xiàn)的時間預(yù)期基礎(chǔ)之上的法律設(shè)計,而民間表演藝術(shù)自創(chuàng)作到每一歷史單元傳承者的再創(chuàng)作導(dǎo)致資源價值實現(xiàn)預(yù)期不確定性,所以,法律上難以界定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的保護期起始點和終結(jié)點,因此“設(shè)定任何受保護的時間都是不現(xiàn)實、不可能的”[5]。為此,《突尼斯樣板版權(quán)法》規(guī)定,對民間作品的保護不受時間限制。當(dāng)然,每個具體的表演者因生理及其創(chuàng)造性貢獻,相對于整個民間表演藝術(shù)來說是明確、具體的,他們的表演者權(quán)不應(yīng)被剝奪。此外,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創(chuàng)設(shè)與發(fā)展的群體性,要求使用者區(qū)別利用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在傳統(tǒng)和習(xí)慣范圍內(nèi)屬于合理使用,以營利為目的并于特定區(qū)域之外使用應(yīng)取得有償許可。加之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特殊性,需要多形態(tài)法律對權(quán)利主體交叉保護,從而使法律應(yīng)然效力受到約束,如對魔術(shù)表演,單一選擇版權(quán)法、消費者權(quán)益保護法、勞動法都很難使表演者的權(quán)利得到周全保護。
二、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的概念
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即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法律關(guān)系的實際參加者,包括表演者集體或多個表演者組織的聯(lián)合體。因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是經(jīng)過不斷的演繹而形成歷史文化現(xiàn)象的繼承,所以,它是特定地區(qū)、民族共同創(chuàng)作、世代相傳的集體智慧成果。即使原創(chuàng)者可能是某一個體,但在長期傳承中被特定群體文化環(huán)節(jié)吸納,創(chuàng)作個性逐漸被融合,最終體現(xiàn)為群體共同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具有自身特征。
首先,它具有群體性。群體性是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的最主要、最基本特性。群體性是一個或幾個特定民族、種群,或一個或幾個特定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現(xiàn)象。“群體這一概念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地區(qū)、承襲同一文化傳統(tǒng)的一群人,即通常所說的當(dāng)?shù)刈迦骸⒈镜鼗虍?dāng)?shù)厝恕⒚褡濉⒉柯洹⒃鼐用瘛⒆迦旱取保?]。群體性不僅指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中所表達的感情、反映的愿景、展示的內(nèi)容,對特定群體具有普遍性,還指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從原始創(chuàng)作到流傳、到再創(chuàng)新的每一歷史單元都是與群體藝術(shù)創(chuàng)作分不開。
學(xué)界大多學(xué)者根據(jù)傳統(tǒng)版權(quán)法有形著作權(quán)確認制度,認為“如果版權(quán)法將不同時期參與演繹創(chuàng)作的人均視為合作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最新版本作品上的權(quán)利人將無限制地增多,版權(quán)保護制度終將失去操作性”,從而否認民間表演藝術(shù)主體的群體性[7]。同時,也有學(xué)者根據(jù)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長期性、復(fù)雜性,而把權(quán)力主體歸為不特定主體,從而本質(zhì)上把民間表演藝術(shù)歸到公有領(lǐng)域。但是,群體性不等同于不特定性,正如哈貝馬斯認為“民族的屬性”是“文化的人造物”,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8],而那些不具有本特定群體的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者,不能成為該民間表演藝術(shù)權(quán)主體。即使是“作者身份不明”的,也可以經(jīng)過適當(dāng)程序特定化,從而使主體具有特定性,如《保護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伯爾尼公約》確立了作者身份的藝術(shù)表達權(quán)利主體認定制度[9]。事實上,“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是公民的民族,而不是血緣共同體”;“公民民族的認同并不在于種族—文化的共同體性,而在于公民積極地運用其民主的參與權(quán)利和交往權(quán)利的實踐”[3] 658。所以,從本質(zhì)上看,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主體是特定的群體。至于認定“群體”,一般考量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生長環(huán)境,而民間跨區(qū)域流傳的同一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則可適用“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將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區(qū)域群體視為該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權(quán)利主體。
其次,它具有空間性。空間,是由客觀物體和主觀意識共同構(gòu)成的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出共同意義和價值群體的區(qū)域。一定場所內(nèi)的人的行動、思想、感受以及人賦予該場所的意義與價值,總是不停地“轉(zhuǎn)化”、“生成”為該場所的一部分,這種變化是一定地域中諸多宏觀和微觀因素互動的結(jié)果[10]。根據(jù)人文地理學(xué)觀點,人類的地理空間行為具有共性特征,人類適應(yīng)、利用一定的空間環(huán)境,達到促進人類生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化景觀之間的關(guān)系互動和互育[11]。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表達通常只在特定的群體內(nèi)流傳,而該群體日常勞動和生活方式、經(jīng)濟狀況同質(zhì)性強,從而帶有鮮明的空間性,如非洲的“肚皮舞”、我國的蒙古族長調(diào)深受當(dāng)?shù)乜臻g的影響。當(dāng)然,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傳播可能會超越原生態(tài)始空間,從而使不同地域之間的民間表演藝術(shù)相互影響,此時空間范圍更廣闊。正如美國人文地理學(xué)者西門(David Seamon)指出:“在一個自然環(huán)境中,身體芭蕾和時空常規(guī)相結(jié)合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地方芭蕾——一種植根于空間的許多時空常規(guī)和身體芭蕾之間的互動。……地方芭蕾培育了一種強大的、深刻的地方感和計劃或設(shè)計的含義。”[12]。在人的生活中,凡俗空間在傳統(tǒng)社會中往往以儀式性的民間藝術(shù)表演與觀賞為基本內(nèi)容,但它難以擺脫神圣空間的投影,表演者如同儀式主持者用“身體芭蕾”描述、表現(xiàn)某種信仰和審美情感[13]。既然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是基于特定空間分類而獨立存在的,與相關(guān)群體的文化相互關(guān)聯(lián),其權(quán)利主體也只能來自特定空間的表演者。
最后,它具有一定的傳承性。民間表演藝術(shù)同文化的其他表達區(qū)別之處,在于傳承的優(yōu)勢超過學(xué)習(xí)的成分,并融化于習(xí)慣和傳統(tǒng)中,從而帶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或地域特征。因此,一種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的確定,是無數(shù)個來源群體當(dāng)中的表演者個體參與創(chuàng)作和流傳的結(jié)果,盡管參與者主觀上有的是有意創(chuàng)作,有的是無意參與流傳,而且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和進步并非刻意所追求”[14];有的為表達形式的確立做出了決定性貢獻,而有的可能做了一定的創(chuàng)作、傳承。每一歷史單元的民間藝術(shù)表演的繼承者都是在前人基礎(chǔ)上的再創(chuàng)作,都是智力勞動者,如洛克所言:“一個人只要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狀態(tài),他就已經(jīng)摻進他的勞動,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chǎn)”,“是正當(dāng)?shù)貙儆谒摹保?5]。所以,傳承者有權(quán)控制自己的表演,因為權(quán)利是“任何人的有意識的行為,按照一條普遍的自由法則,確實和其他人的有意識的行為相協(xié)調(diào)”[16],這正是特定群體的長期傳承才得以積淀、民間表演藝術(shù)本身也不因時代變遷而驟然斷裂的關(guān)鍵原因。此外,由于每一位非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原始創(chuàng)立者都是該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傳承者,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范圍也隨著歷史的變遷而呈現(xiàn)“前赴后繼”的軌跡。
三、界定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的要素
民間表演藝術(shù)集體表演作為法律保護對象,如其權(quán)力主體身份不明,必然導(dǎo)致法律關(guān)系內(nèi)容無歸宿。關(guān)于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利主體,目前理論界存在諸多爭議,其主要原因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指向的對象——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形式的特點:群體性、發(fā)展性、公開性。事實上,群體常常有自己的習(xí)慣法規(guī)范和控制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接觸使用和創(chuàng)造利用。為此,確定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利主體,應(yīng)該結(jié)合國際法原則、行為要素、物理要素來考量。
(一)國際公約對集體原則的規(guī)定。集體原則在國際公約中得到普遍尊重與執(zhí)行,對于表演集體原則也有國際協(xié)定的明文規(guī)定。保護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國際公約,從不同角度規(guī)定了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盡管不是特別規(guī)制的范疇,但作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重要內(nèi)容的民間表演藝術(shù),自然適用其規(guī)定。
國際公約對集體原則規(guī)定的主要內(nèi)容,可以歸納為4個方面。第一,防止出口與轉(zhuǎn)讓的集體保護。為人類保存一個合適的生活環(huán)境,考慮到文化遺產(chǎn)的消失會構(gòu)成絕對的損失,并造成該遺產(chǎn)的不可逆轉(zhuǎn)的枯竭,《國際文化合作原則宣言》規(guī)定各國有責(zé)任保護其領(lǐng)土上的文化財產(chǎn)免受偷盜、秘密發(fā)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險。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1964年就此通過了一項建議并收到進一步建議,1970年第十六屆會議通過《關(guān)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chǎn)和非法轉(zhuǎn)讓其所有權(quán)的方法的公約》,公約規(guī)定:“國民的個人或集體天才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財產(chǎn)”為締約國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17]。第二,建立長效機制的集體保護。由于威脅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新危險的規(guī)模大和程度嚴重,國際社會期望通過公約形式,以便為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遺產(chǎn)建立一個永久有效的制度。《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在“法律措施”中規(guī)定,文化的組成部分“應(yīng)根據(jù)其本身的重要性,由與各國的權(quán)限和法律程序相一致的立法或法規(guī)單獨地或集體地予以保護”[18]。第三,防止非法交流損害的集體保護。考慮到文化財產(chǎn)構(gòu)成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為促進各文化交流及民族文化的價值,防止對文化財產(chǎn)的非法貿(mào)易和損害,《關(guān)于文化財產(chǎn)國際交流的建議》規(guī)定:應(yīng)根據(jù)文化組成部分本身的重要性,“由與各國的權(quán)限和法律程序相一致的立法或法規(guī)單獨地或集體地予以保護”[19]。第四,民俗表演的集體保護。由于與口頭傳統(tǒng)有關(guān)的文化具有的極度脆弱性和可能遺失的危險,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提議成員國立法保護民俗,因此《保護傳統(tǒng)文化和民俗的建議》在“民俗的保護”部分明確規(guī)定“至于智力創(chuàng)造的民俗機構(gòu)是否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 都值得以經(jīng)過授意的方式進行保護, 為智慧產(chǎn)物提供保護。”[20]
(二)權(quán)利主體的行為要素——創(chuàng)造性勞動。創(chuàng)作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群體作為一個整體,確立其主體地位存在法理基礎(chǔ)。創(chuàng)造性話動是權(quán)利產(chǎn)生的“源泉”,而法律是權(quán)利產(chǎn)生的“根據(jù)”[21]。總體上,民間表演藝術(shù)屬于集體創(chuàng)作,這種集體性創(chuàng)作體現(xiàn)為兩種方式:由某個人完成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雛形后在群體時空環(huán)境中集體再創(chuàng)作,逐漸形成固定的藝術(shù)表達;由某群體在長期集體勞動與生活中共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作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之基礎(chǔ)的“傳統(tǒng)”,不是任何特定個人刻意安排而形成的結(jié)果,而是群體經(jīng)過長期實踐活動中特定群體文化呈現(xiàn)的結(jié)果。作為知識產(chǎn)品,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是行為者進行智力勞動創(chuàng)造的成果,創(chuàng)造者擁有創(chuàng)造結(jié)果的權(quán)利,這是當(dāng)代法律的基本原則。依照這一原則,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創(chuàng)造者就應(yīng)是其權(quán)利主體。
民間表演藝術(shù)是群體創(chuàng)造和個體傳承二位一體的文化原生態(tài),因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創(chuàng)造者是一個群體,并經(jīng)過長期流傳和傳承,所有參與創(chuàng)造的表演者都是“表演者集體”中一員。由于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日常生活中都會融入個人創(chuàng)作,對表演藝術(shù)傳統(tǒng)進行再表演,如果沒有傳承人的再表演,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傳統(tǒng)內(nèi)涵就不可能世代相傳;后繼者的傳承行為如不以傳統(tǒng)內(nèi)涵為基礎(chǔ),則會使民間表演藝術(shù)失去靈魂。例如由楊麗萍主演的《云南映象》,傳承人的創(chuàng)作活動多樣,包括改編、整理、制作成影視等,由此產(chǎn)生的表現(xiàn)形式眾多,如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等等。表演者集體作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創(chuàng)造者、傳承者、使用者,應(yīng)獲得公平的利益回報,對其享有權(quán)利是法律本質(zhì)要求,也是法律公平、正義價值的內(nèi)在體現(xiàn)。因此,這些表演者群體以創(chuàng)造者的身份具備了權(quán)利主體的資格,法律因?qū)τ嘘P(guān)群體主體身份予以確認。
此外,《生物多樣性公約》還將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歸入“傳統(tǒng)資源權(quán)”,本質(zhì)上,民間表演藝術(shù)實質(zhì)是承載著傳統(tǒng)文化的程式化信息,這種程式化信息由群體創(chuàng)造積淀并由群體成員傳承再現(xiàn),傳承人又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展現(xiàn)。而信息作為財產(chǎn)權(quán)的重要內(nèi)容,“法律就不能不相應(yīng)地對它加以保護,事實上這門法是傳統(tǒng)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22]。可見,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群體對他們集體創(chuàng)造和延續(xù)的傳統(tǒng)信息享有信息產(chǎn)權(quán),自然具有主體地位。
(三)權(quán)利主體的物理要素——表演者集體成員身份標(biāo)準(zhǔn)。由于我國法律對集體成員資格的取得、喪失沒有明確規(guī)定[23],認定表演者集體成員身份,需要采取綜合標(biāo)準(zhǔn)而非單一尺度。
從實踐來看,確立表演者集體成員身份標(biāo)準(zhǔn)一般有:特定地域的戶籍;對集體依賴程度;集體的表演權(quán)。所謂特定地域是指以自我歸屬和歸屬區(qū)別于其他人群所聚集的自然空間。這些人群有組織地、持續(xù)地居住在公權(quán)力確認的土地上,并且他們世代對這些土地及其產(chǎn)出實行“有效占有”,有共同的語言、習(xí)慣及其他顯著的傳統(tǒng)文化特征。除原始性表演者外,后歷史單元傳承者因為出生、婚嫁、遷徙等原因,其地域戶籍會發(fā)生變化,因此,不能夠完全以地域戶籍作為表演者集體成員身份取得標(biāo)準(zhǔn)。至于對集體依賴程度,在表演者集體中,一般表演者,特別是剛剛從事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表演者,對表演者集體的資源有更多的依賴性,多是與集體共興亡,表演者個體對集體依賴程度高;反之,已經(jīng)成名或者有較大影響力的表演者,不僅對表演者集體的資源無多大的依賴性,相反,表演者集體對這樣的“大腕”具有相當(dāng)?shù)募纳裕按笸蟆睂w發(fā)展具有極強的提升作用。因此,在現(xiàn)實中,“大腕”往往脫離了其“誕生”的原始集體,但不能夠因此否定“大腕”的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地位。集體的表演權(quán)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利主體的最根本體現(xiàn),作為集體權(quán)主體對所在集體表演擁有表演權(quán),是集體成員資格的最顯性標(biāo)志,因為成為表演集體成員的前提是對該傳統(tǒng)表演藝術(shù)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貢獻,即表演。但是,在特定情況下如對某場劇演出的投資者,對表演者有選擇權(quán),甚至自己親自掛名演出,非表演者集體成員也能夠成為名義上的表演者。
此外,作為傳承者不僅符要合身份標(biāo)準(zhǔn),還應(yīng)同時具有主觀與客觀要素。客觀上,他們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原創(chuàng)者的后裔,并具有“歷史上的連續(xù)性”;如果已被同化或異化,仍保有和延續(xù)著自己的傳統(tǒng)表演藝術(shù)所蘊藏的文化傳統(tǒng)。主觀上,他們自我認同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與其原創(chuàng)者的同一民族性或群體性。
四、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類型
目前,我國關(guān)于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種類劃分,相關(guān)理論比較多,主要有國家說、少數(shù)民族說、專門機構(gòu)說、群體說、雙重主體說、綜合集體說;還有復(fù)雜主體說、重疊主體說、特定群體主體說、實際權(quán)利主體說等。但從具體類型來看,大致可以歸為三大類。第一,單一主體說,該說認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是唯一的,又分為國家說、少數(shù)民族說、專門機構(gòu)說。國家主體論主要理由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權(quán)益的主體具有不特定性與群體性,創(chuàng)作者身份難以確定,國家作為主體便于司法操作,傳統(tǒng)版權(quán)理論中同匿名作者或無名作者的著作權(quán)制度設(shè)計。學(xué)者如張革新、王鶴云等持此觀點[24]。少數(shù)民族說基于文化財產(chǎn)的共創(chuàng)性與實際創(chuàng)作者,如學(xué)者顏斐。而專門機構(gòu)說的考量因素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民間性、可操作性以及權(quán)利行使方式,
如嚴永和等學(xué)者[25]。第二,重疊主體說,該說認為,權(quán)利主體包括群體或國家,特定群體(或社區(qū))或民族,有關(guān)的群體、居民團體或民族。其中又有群體說、雙重主體說。群體說是基于創(chuàng)作性與民間表演藝術(shù)長期的流傳過程的民族風(fēng)格和地方特色,如吳漢東等學(xué)者[26]。持雙重主體說的學(xué)者,如邱平榮等,基于如下考慮: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價值、單一權(quán)利主體保護不全、公有領(lǐng)域劃分標(biāo)準(zhǔn)、文化安全[27]。第三,復(fù)雜主體說認為,權(quán)利主體包括國家、民族自治政府、民族、村、多村集體聯(lián)合、社區(qū)、傳承人、收集整理人和個人等,如梁隆乾等[28]。
前述觀點從不同角度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范疇進行論述,具有積極價值,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些學(xué)說把權(quán)利主體與權(quán)利實施者混同、權(quán)利主體范圍過于狹窄或過于寬泛。筆者認為,群體說比較符合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的實際,主要有以下理由。首先,民間表演藝術(shù)保護的根基在民間。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是在特定區(qū)域或民族中產(chǎn)生、流行、傳承的,并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表演者完善,具有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和地方特色。如果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保護得不到基層的、原生土壤上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或主人公的支持,很難實現(xiàn)保護的目標(biāo)。同時,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演進過程中,“知識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第三次重大變革與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為由單向度主體向多向度主體發(fā)展”[29],這說明群體也將納入權(quán)利主體的范圍。第二,權(quán)力主體法定性。特定的個體表演者具有不特定性。在法制社會中,法律所保護的是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權(quán)利主體,而不考慮具體主體的性質(zhì)。在私法領(lǐng)域,國際上立法將不確定人員的群體作為權(quán)利主體是通行作法,我國民事法律也有多處集體主體的規(guī)定[6]233。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本質(zhì)上是私權(quán),權(quán)利主體就應(yīng)該是“非官方”性質(zhì),民間表演藝術(shù)本身與行政性質(zhì)組織并無關(guān)系,如果將主體認定為行政性質(zhì)組織包括國家、機關(guān)或國家指定的機構(gòu),導(dǎo)致行政干預(yù)民間藝術(shù)表演,可能破壞民間表演藝術(shù),違反其私法本質(zhì)。當(dāng)然,這并非否認國家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管理權(quán)。第三,原始個性的模糊性與群體特征的確定性。民間表演藝術(shù)是特定群體成員個體或集體創(chuàng)作、繼承、發(fā)展的產(chǎn)物,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最初的創(chuàng)作者可能是某個群體中的個人,但在長期的傳承過程中,后來繼承者賦予民間表演藝術(shù)以時代內(nèi)涵,前任創(chuàng)作者的個性特征被模糊化,表現(xiàn)為集體文化特性。如“青海省大通回族土家族自治縣橋頭鎮(zhèn)下廟一村陳啟花等117名村民訴柴玉奎、柴明孝、甘肅音像出版社、青海省喬佳音像有限公司侵犯民間社火表演者權(quán)”一案中,法院認定了該村117名社員的共同訴訟主體資格[30]。
根據(jù)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確定要素以及群體說,具體主體可以有不同類型。第一類是國家。國家一般不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但是在國際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中,可以成為權(quán)利主體,代表全民族行使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權(quán)。第二類是民族、種群、種族。這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普遍主體。第三是傳承人。這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普遍主體,但是單個傳承人不是權(quán)利主體,只能是集體的成員而享受權(quán)利,因此,傳承人享有的權(quán)利實際上是對其集體權(quán)利的延續(xù)。對傳承人保護,日本、韓國等有專門法律條文規(guī)定。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公布第一 、二、三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中有關(guān)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傳承人共805人,涵蓋傳統(tǒng)音樂、傳統(tǒng)舞蹈、傳統(tǒng)戲劇、曲藝、傳統(tǒng)體育、游藝與雜技、民俗等[31]。第四是表演者特定群體。這是由各個民間藝術(shù)表演者包括非本民族、種群、種族而又是本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達的表演者聯(lián)合體,如祁劇表演者團體。但表演者特定群體只能夠就其特定貢獻部分享有完全權(quán)利,其它共性藝術(shù)表達的權(quán)利視情形分別由第一、二、三類主體行使。
結(jié)束語
民間表演藝術(shù)是特定群體重要文化載體,是不可再生文化資源,更是民族的文化財產(chǎn)。這項巨大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是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創(chuàng)造財富者得益是一個亙古長存的真理,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實際情況是傳統(tǒng)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不保護這一創(chuàng)造財富者。細探現(xiàn)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國際秩序,存在三個緣由:文化資源缺乏且科技發(fā)達國家把持文化財產(chǎn)分配規(guī)則——法律制度的制定權(quán);文化資源豐富且民族自信缺失的國家追隨他國法律規(guī)則——喪失自身文化優(yōu)勢的利用權(quán);文化財產(chǎn)的無形,導(dǎo)致有形財富的吸引力,出現(xiàn)“賤賣”國家文化以求“文化自信”。長期以來,文化工業(yè)化結(jié)果導(dǎo)致了民族文化安全問題,在國際競爭中本國民族文化被褻瀆甚至貶損,引起人們對工業(yè)文明的恐懼,于是有些國家開始著力保護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積極探索對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主體范疇,承認并保護傳承者。當(dāng)然,國際上對此態(tài)度不一。作為五千年文明古國、民族表演藝術(shù)資源大國,又作為民間表演藝術(shù)國際競爭力弱國,在國際化進程中,我們支付了昂貴的學(xué)費。因此,我國更應(yīng)加快建立民間表演藝術(shù)表演者集體權(quán)制度,全面確立權(quán)利主體類型及其保護機制,積極創(chuàng)建文化立國的國際知識產(chǎn)權(quán)新秩序。
お
參考文獻:
[1]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1988,p219
[2]李行健.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2004:612.
[3][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關(guān)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童世駿,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108.
[4]鄭智武.論表演者權(quán)體系[J].中北大學(xué)學(xué)報,2010,(4):58.
[5]唐廣良.三大主題的關(guān)聯(lián)性[N].北京: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報,2001-11-01(3).
[6]管育鷹.知識產(chǎn)權(quán)事業(yè)中的民間文藝保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5.
[7]崔國斌.否棄集體作者觀——民間文藝版權(quán)難題的終結(jié).法制與社會發(fā)展[J]2005,(5):75.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6.
[9]《保護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伯爾尼公約》第15條
[10]Allan Pred,“Place as Historical Contingent Process: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 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Vol.74,1984,pp.279-297.
[11]赫維人,潘玉君.新人文地理學(xu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2:31-35.
[12]David Seamon,A Geography of the Life world:Movement,Restand Encount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9:54-57.
[13]周顯寶.人文地理學(xué)與皖南民間表演藝術(shù)的保護[J]蔽囊昭芯,2006,(4):76-90.
[14]趙蓉、劉曉霞.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法律保護[J].法學(xué),2003,(10):77
[15][英]洛克.政府論[M].葉企芳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4:19.
[16][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xué)原理——權(quán)利的科學(xué).沈叔平,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7:39-40.
[17]參見《關(guān)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chǎn)和非法轉(zhuǎn)讓其所有權(quán)的方法的公約》第4條
[18]參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公約》第40條.
[19]參見《關(guān)于文化財產(chǎn)國際交流的建議》第1條第40款
[20]參見《保護傳統(tǒng)文化和民俗的建議》第6條.
[21]劉春田.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評論〔第一卷) [Z].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2:191-192.
[22]鄭成思. 信息、信息產(chǎn)權(quán)及其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關(guān)系[N]. 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報, 2003-11-04(理論).
[23]任丹麗.關(guān)于集體成員資格和集體財產(chǎn)權(quán)的思考[J].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8,(1):64.
[24]張革新.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權(quán)屬問題探析[J].知識產(chǎn)權(quán),2003,(2):48-49.;王鶴云.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的版權(quán)保護制度[N].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報,2001-11-01(3)
[25]嚴永和.論傳統(tǒng)知識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
[26]吳漢東.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藍皮書[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322.
[27]邱平榮,李勇軍.論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著作權(quán)保護[J].江淮論壇,2003(4).
[28]梁隆乾.誰是民族民間音樂的主體[J].民族音樂,2007(1)
[29]曹新明.知識產(chǎn)權(quán)主體制度的演進趨向[J].法商研究,2005,(5).
[30]參見: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寧民三初字第3號判決書
[31] 參見我國文化部文件:文社圖發(fā)〔2007〕21號;文社圖發(fā)〔2008〕1號;2009〕6號.
The Essence of Collective Rights of Folk Performing Arts Actors
ZHENG Zhi瞱u
(Zhejiang Art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Abstract:
Folk performing arts actors collective rights fall within the ambit of performers rights, but are of specialties bearing the color of groupism, spatiality and somewhat heritability. Much has been argued by theorists about the essence of folk performing arts actors collective rights and among the theories developed is the “group doctrine” that emphasizes folkishness of folk performing arts, legitimacy of the rights owners, and groupism of the works creators. By r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inciples, behavior elements and physical factors, one can see that the main elements of folk performing artists collective rights should enclose state, nation, population, race, successors, and specific groups of performers, which can be found in foreign laws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whereas no express provisions can be discovered in Chinese laws.
Key Words: folk performing arts; performers collective rights; su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