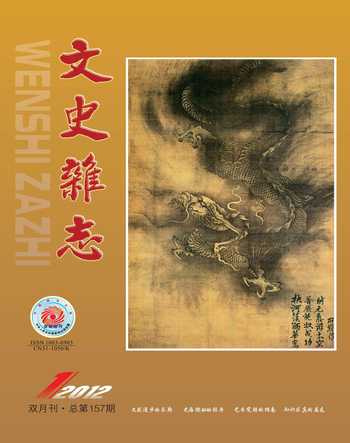明清時期的晉商會館規約初探
王宏選 單文杰
明清時期,晉商作為商幫中的奇葩譜寫出一曲商業傳奇,晉商會館的興盛就是其歷史見證。晉商在全國各地建立眾多會館,比較有名的有蘇州全晉會館、聊城山陜會館、開封山陜會館、洛陽潞澤會館、南陽山陜會館、張掖山西會館等。晉商會館一般規模宏大,建筑考究,商業性質明顯,具有顯著的地域性和行業性特點。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旅外晉商深刻認識到“無論日識新知,莫不休戚與共,痛癢相關”,必須建立會館以團結同鄉士商。經過同行協定或公議,晉商會館制定出明確的管理規約,名曰“規牌”、“行規”、“條規”、“章程”或者“俗例”等。會館規約內容廣泛,涉及入會資格與費用、議事制度、會館公產管理制度、會員的義務、違規的罰則、貨物質量和計量標準等諸多方面。
一會館組織與公產制度
晉商會館在建立之初,管理大權一般由同鄉中地位高和有聲望的人執掌。隨著會館的發展和成熟,公舉會首制逐步推行。公舉并非選舉,但形式上需要得到大多數會員的認可。一般而言,被公舉為會首的往往是本地區有名望者或是殷實大商號。因為他們對公共事務熱隋高,捐資多,社會交往廣,具有較高的威信和社會活動能力。比如,著名晉商六必居醬菜園自乾隆年間開始,一直擔任臨襄會館的會首。會首又稱董事、柱首、司月、值年等,負責總理會館的簿籍銀兩和處理會館重大事項。
漢口山陜會館的規約對會首的地位作出明確規定:“所有收支賬簿、房屋、家具、菜園、地基、應用人役,總歸值年經營差委。”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中國經濟全書》中,對晉商公所及其董事的職能作了詳細的記述。當時上海的山西票號成立上海匯業公所,對外代表山西票號的團體利益,對內負責協調票號之間的利益沖突。關涉公所利益的爭議事件,全權由董事來決斷。“然為總董者,既由同業者共同選定,自得同業者全般之信用,故于總董提議之事,或裁決之事,幾無不服從者也。”
會首一般都有明確的職責,主要包括:1.對會館公共財產與經費進行管理和支配,調解、仲裁本幫同行之間的商業糾紛。2.每逢重大節日,召集同鄉,共同祭祀本鄉本土所尊奉的神祗,以聯絡鄉情。3.身處異鄉,難免發生“疾病疴癢”,會首號召會員為落難的同鄉舉辦募捐義舉,向貧病交迫的同鄉提供錢財和藥物救濟,也為客死異域、無力歸葬故土的同鄉提供義園、義地。4.聯合團結本幫眾商力量,代表眾商與當地官府交涉商業事務,與當地牙商作斗爭,以擺脫牙人的控制。較大的會館除會首外,下設若干專職人員如坐辦、司事、書記、賬房等,協助會首處理館內日常事務。他們受聘于總管或董事,領取一定的薪水。而董事會或理事會下設的襄董、襄理、董事、理事等職位,都是由有一定地位、熱心鄉里事業的人員或商號兼任,并無專職。此外,會館要雇一名或幾名長班看守會館,負責日常管理工作。
晉商會館的管理規約,一般對會館公產有著明確規定。公產的來源,主要包括會費、捐項、厘金、香資、房租、利息、批頭等渠道。公產的適用和管理必須嚴格遵守會館規約,其支出主要用于會館的修繕、請戲班演神戲、日常接待及為落難同鄉買義冢等事項。公產取之于本幫同人,因而必須妥善保管和適用,會館人員不得怠于職責或濫用職權而使公產損毀。
據《漢口山陜會館志》載,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山西和陜西籍的十幫商人共議山陜會館管理條規,對會館公產的管理和使用作出詳細規定:1.所有收支賬簿、房屋、家具、菜園、地基、應用人役,總歸值年經營差委。2.會館宜保持清潔衛生,平素日期不準閑人入內游覽。3.不準外幫借館演戲,如有徇情私借情事,從重議罰。4.館內燈彩家具一概不準出借,如違者議罰。5.晚間10點鎖門,如遇宴會燈戲12點為止,除水龍救患外不得任意啟閉出入,如違者立驅出館。6.會館重地燈火最宜小心,嗣后我各幫字號如遇在館做會演戲,客散戲終主人務將廟院戲臺一應燈燭親查熄滅始準回號,以昭慎重,如違議罰。7.館內不論粗細貨物,概不準在內晾曬,以昭肅敬。8.本館司事、住持人等內不準留客過宿,在外不準支取銀錢貨物,自議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賒貨物,一經知覺,逐出會館,決不寬貸。9.水龍有備無患,倘有不測,一時出館夫役人等酒資,一切照章施行。10.供奉香火、長年神燈,乃住持應辦之事,嗣后逐日長香,務要敬謹供奉,每逢會期奉香獻酒,自必住持侍奉,年節三天,僧人間有貪閑假手他人,殊屬不恭,自議之后,住持二人輪流執香在殿侍候以昭誠敬。11.凡選用館丁務要小心謹慎,能干辦事者充之,不得輕舉濫進。館之內外門巷每日打掃潔凈,館之社產市屋務聽值年者調撥,催取租息不致稍懈。館內不許容留閑人飲酒戲耍,致生事端。館外街巷不許收荒擺攤賭博。館役不得徇情容隱不報。如敢不守館規,徇私偷懶,即行斥革。12.大會值年,從前十幫輪流,位年二號會辦。今增匯業,每年四號。以祀產漸增,館務紊繁。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銀兩,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交下首,務期明悉周詳,毋延。13.招僧住持原為供奉香火,每日長香神燈,務要敬謹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掃。會期朔望倍加誠敬,灑掃潔凈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謁,平日不得隨便出外游玩。
二會員義務與行會罰則
明清時期的會館組織一般比較松散,對入會者約束力較弱,但是晉商會館對入會者所應履行的義務大多有明文規定。加入會館的商人要交納一定的會費,遵循會館規約中的交易規則,參加會館的各種社交活動、宗教儀式等。同時,晉商會館規約特別強調入會的本幫商號,要重視商業信譽,買賣公平,童叟無欺,取信于民,否則予以處罰。
從會館規約可以看出,入會者在行業內生活與經營的諸多方面受到嚴格限制,會員需要履行諸多的義務。晉商會館及其規約在維護市場公平交易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為在異域經商的本幫人創造出一個穩定的市場環境,也從根本上維護了本行會員的整體利益。
除了規定會員義務,各地晉商會館規約還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了對違反規約行為進行懲處的罰則。其主要包括如下處罰形式:第一,財產罰。包括罰銀錢和沒收貨物兩種懲處方式,目的在于通過直接減損違規者經濟利益以示懲戒。財產罰是針對違反規約行為的最主要制裁方式。第二,名譽罰。特指晉商中流行頗廣的一種比較有特色的懲罰方式——罰戲,即罰違規者花錢請戲班子給大家演一臺戲。看似荒唐的懲罰方式,恰恰反映出晉商的睿智。第三,開除行籍。這種剝奪行會會員資格的處罰方式,一般適用于嚴重擾亂市場交易規則、嚴重影響晉商群體形象和聲譽的行為。“公同革出,永不復行”,一旦被逐出會館行會,受罰‘者必然受到其他晉商商號的排斥,無人再與其進行商業往來,也就剝奪了違規者繼續經營的能力。第四,稟官究治。如果會員嚴重違反會館規約和行規,甚至觸犯國家刑律,會館的制裁力度和貫徹能力往往受到巨大挑戰,這時就需要借助國家暴力對違規者加以制裁,即“稟官究治”,由會內本幫會員合力將違規者扭
送官府。
上述處罰形式中,最具特色的當屬“罰戲”。雖然其他地區的行會組織中也存在罰戲現象,但晉商中的罰戲不是個別和偶然現象,其做法也由來已久。涉及罰戲的條文規范,散見于各地晉商會館的碑刻銘文及會館規約中。
立于雍正二年(1724年)、重刻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社旗山陜會館《同行商賈公議戥評定規概》碑云:社旗店為四方客商雜貨興販之墟,因近來人煙稠多,其間即有改換戥秤,大小不一,獨網其利者。是以,合行商賈會同集頭等,齊集關帝廟,公議秤足十六兩,戥依天平為則,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換,犯此者,罰戲三臺。如不遵者,舉秤稟官究治。惟恐日后紊亂規則,同眾稟明縣主蔡老爺金批鈞諭,永除大弊。
在湖北販布的晉商會館議定有嚴格的《布行條規》,對布商交易的懲罰辦法做了詳盡規定:一議該處買布,設有公廠,均至地出桌,不準移埠,取巧傲眾,以便互相稽查;又不準任意漲價,以及濫收窄短布等弊。今既城鄉同行,均愿竭力立定此章,即宜固守其章。如果故違,經公議罰不貸。一議春秋二季開市,預著廟僧,咨會各行某聚會,公擇吉期,議定時價開莊。如有存奸計者,私先刷條,開莊買壞市價,令商等裹足,以便壟斷。此種刁徒,理主公罰神戲二部,酒席一桌,以戒將來。
“制裁”和“戲曲”無論在形式還是性質上都差別甚大,制裁的有效實施往往需要肅穆莊重的環境,而戲曲營造的恰恰是歡慶娛樂的氛圍,乍一看很難把二者聯系起來。其實,罰戲表面上是一種名譽罰,實際上也融合了財產罰的功能。違規者以罰戲的方式公開對大家賠禮道歉是名譽罰,而破費錢財請來戲班子也是財產罰。同時,這種處罰方式也與山西人癡迷戲曲不無關聯。晉商熱衷于興辦戲班,而且不滿足于聽戲,他們組織自樂班,俗稱“鬧票兒”。在緩解思鄉之情的同時,晉商也讓山西梆子戲走出山西,進入全國的各個角落。對晉商而言,商路即戲路,把罰戲作為晉商行會內的一種處罰方式也就顯得不足為奇了。
三會館的行會調處
晉商旅外從事商業活動,由商事競爭引發的生意糾紛不可避免,此時就需要一個大家認可的組織來化解糾紛。晉商會館所確立的行會組織,承擔著調解和仲裁晉商同業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糾紛的功能。明清時期,在傳統民間調解的基礎上,晉商依托會館組織逐漸形成特有的商事糾紛解決機制——行會的調解和仲裁制度。由于行會調處的依據是會館預先設立的管理規約,調處的地點往往是在會館的祠堂內,因而會館在維持行會內部穩定和有序商業秩序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晉商之間發生糾紛,大多數情形是在會館的行會內部協商調解和仲裁是非,并且共同議罰。爭議雙方當事人都必須服從,否則會受到同業的排斥。晉商行會的具體的調解和仲裁過程由晉商中一些會館董事或有名望的紳商來主持。調解者或仲裁者秉持公平正義和誠實守信的宗旨,盡力撮合爭端雙方互相諒解和做出讓步,以促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如果調解或仲裁后雙方仍無法達成諒解,才可以訴諸官方。而且爭議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直接起訴,必須首先求助于會館的行會組織,否則將受到晉商同人的責難。這種禁止性的義務是絕對的,行會處理的前置原則保證了晉商會館處理內部爭議的優先權。
晉商群體之所以傾向于會館的行會調處,主要取決于這種糾紛解決機制與官方訴訟機制在成本收益上的懸殊,這也是行會調處的優勢所在。
首先,行會調處在救濟成本上是低廉的。糾紛當事人只需把爭議事項提交行會,然后在會首主持下各抒己見,經由其他會員做出初步的是非判斷,最后會首權衡利弊作出最終裁決。從裁決的時效性看,這種業內救濟途徑是方便決捷的。而官方訴訟救濟則顯得相形見絀。當事方首先面對的是價格不菲的訴訟費用。由于商場瞬息萬變、商機轉眼即逝,而官方訴訟程序相對緩慢,即使短暫的數日也可能使糾紛雙方在商戰中處于不利地位。
其次,從裁決的正確性分析,行會調處往往優于官方訴訟機制。晉商之間的糾紛一般商業性質明顯,行會對糾紛的定性比官方更為準確。因為一方面會館行會內部有許多德高望重的行家里手,他們對行業紛爭具有較大的發言權;另一方面,由于主流社會對商人階層的排斥,在正統體制內往往缺乏解決商事糾紛的專業人員。
最后,會館的行會調處比官方救濟具有更好的社會實效。糾紛雙方一旦選擇官方訴訟渠道,無論誰最終贏得官司,都必然面對潛在的困境——經受行會及其他會員進行的“二次隱形裁判”。因為晉商會館規約中明文規定,在一般情形下禁止會員不經會館行會組織的處理而直接告官。這一規定對會館會員而言,具有極強的權威性和震懾力。如果官司的勝訴方無法在會館的行會裁判中贏得會館組織及其他成員的一致承認,誰也無法保障他的實際利益。旅外晉商一旦受到整個晉商社會的排斥,失去會館這道屏障的保護,其生存都可能有問題。
晉商利用傳統的地域觀念,把商埠中的同鄉之人聯合起來,通過會館這一組織形式制定出完善的管理規約,既避免了晉商之間的內耗,又為有效地同異地商人進行競爭提供了保障。晉商會館這一組織形式如同家族一樣,成為構造傳統社會的重要元素,被納入中國傳統的禮法秩序當中。在這個意義上,基于會館規約形成的社會秩序,是在官僚統治鞭長莫及的商業領域出現的一種民間自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