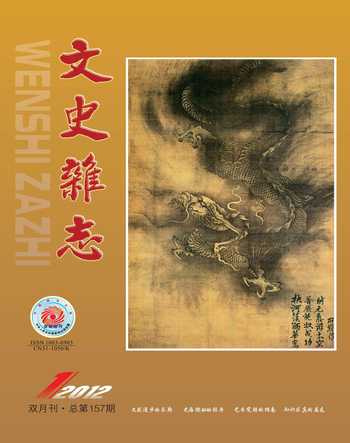借龍言志 妙對佳聯
夕照褸
《堯山堂外紀》云:明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問之,則代父充役者也。帝(當時朱元璋尚未稱帝,文中追記故云)曰:“‘七歲童兒當馬驛,能作對乎?”即應曰:“萬年天子坐龍庭。”帝喜,蠲其役。這個對子之所以得到厚賞,是因為投合朱大將軍喜歡好口彩的心理。另有旁證即張誼《紀聞》記載:太祖(朱元璋)與徐達閑行至江口,欲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值歲除,呼舟無應者。有夫婦老人載一舟,欣然納之,日:“天晚矣,命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為食。明晨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口號:“圣天子六龍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高皇(朱元璋)聞此吉語(好口彩!預兆一個開國皇帝,一個大將軍),與中山(徐達后封中山王)躡足相慶。登極后訪得之,(老人)無子,官其侄,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也。
《堅瓠集》云:相傳明太祖(朱元璋)幸馬苑,永樂帝(其子朱棣)、建文帝(其孫朱允炊)同侍,太祖出句云:“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云:“雨灑羊毛一片氈。”太祖不悅,永樂對云:“日照龍鱗萬點金。”其氣象已不侔矣。這次屬對單就文字論,結構還是相應的。“風、雨、日”同門,“馬、羊、龍”同群。“千條線、一片氈、萬點金”,比喻同類。就聲律看,出句“平平仄仄平平仄”,對句“仄仄平平仄仄平”,都合格。似乎兩個對句不分軒輊。問題就出在立意選材上。出句以“千條線”比喻奔馬細絲飄拂的尾毛,切實,明白。對旬則立見劣優。永樂帝用“萬點金”比喻游龍迎日耀輝,碎金閃爍的鱗甲,富麗堂皇,度量非凡。對比之下,建文帝“一片氈”,舉言瑣屑,形象骯臟,十足小家把式,氣象遠遜其叔朱棣矣!朱元璋苦心培養的皇太孫允炆,出口不能成章,難怪他要“不悅”啊!
與之同類的故事還見于《巧對續錄》:汪衡甫方伯宦浙來談,謂近來文士,早慧者多。昨送一星使到某家,其子方10歲,聞客言“勞于王事”,應聲曰:“簡在帝心”。因檢案上《詩經》“巷無服馬”命對,又應聲曰:“隰有游龍”。其兄對“野有死麕”,遠不如矣!座上嘖嘖稱羨,惜佚其姓名。
《金陵瑣事》云:(顧)東橋公鎮楚(巡撫湖廣)時,張太岳(居正)僅十余歲,應童子試。東橋曰:“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雛鶴學飛萬里,風云從此始。”張即日:“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東橋大喜,解腰間金帶贈之,曰:“他日貴,當過我也。”
《邱瓊山逸事》云:邱文莊公,少從師于里宦之家塾。時天雨,坐席當瓦穴漏滴,邱私換宦兒席于漏所,而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兒訴于師,師日:“能屬對者,即為理直。”因曰:“點雨滴肩頭”。公應聲曰:“片云生足下”。師稱善。宦兒愧不能對,哭告其父。父怒,召公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虎?”公即對曰:“安知魚不化為龍!”宦知其非常人,好語遣之。
相傳羅江李氏“叔侄一門四進士、弟兄兩院三翰林”,“四進士”指李化楠、李調元(化楠之子)、李鼎元、李驥元(李化樟之子)。“兩院”,指調元和驥元皆任過主考或副主考。“三翰林”指調元、鼎元、驥元分別授翰林院編修或檢討。李化楠出句“蜘蛛有網難羅雀”,以試其子才學。李調元應聲對曰:“蚯蚓無鱗欲成龍”。以上三對均用“成龍”典故,學童以之自喻,表達日后“勇躍龍門”,“龍騰九天”之雄心壯志,敏思捷對更見氣魄。
《巧對續錄》:德清蔡明經壽昌少有神童之稱。趙太守學轍府試,愛其才,以女妻之。嘗偕游碧浪湖,趙口占“魚蹙水紋圓到岸”句,命之對,即應聲曰:“龍噓云氣直沖天”。此等均屬同類少年言志故事。
歷來傳說“父愿子成龍”的對句故事,應對童子是誰?或曰解縉,或曰紀曉嵐,或曰林則徐,或曰蔡鍔,或曰某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既然是故事重提,對年輕讀者負責,總得說個來龍去脈。應該根據事實,實事求是地作一番研究。
請看《對聯話》卷十四引《聯選》的文字:予又記一聯,某童子應試,因人擠,其父馱之前聽唱名受卷。試官見其幼,問知馱者為其父,因出聯命對曰:“子將父作馬”。某童遽抗對曰:“父愿子成龍”。試官大喜,稱為奇才。文中“某童”一詞是關鍵詞語。該書作者吳恭亨是湖南慈利縣人,是南社成員、《慈利縣志》總纂,所編《對聯話》共十四卷,收錄清代及民國初年諸多名人之作,對包括蔡鍔在內的辛亥革命以來至護法運動的革命人物,都極力贊揚。該書收錄蔡鍔的作品和軼事,為啥不說蔡鍔當年屬對的故事呢?這只能說明身為蔡鍔同時代人的吳老先生也不認為那屬對是蔡鍔的故事;否則他為啥不明寫“蔡鍔”,而要書“某童”呢?
《七修類稿》說:何景明入場考試,年最小,其兄背以進之。御史出一對曰:“弟騎兄作馬。”景明遂應聲為對:“子證父攘羊。”對句出于《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景明小小少年,熟讀“四書”,臨場屬對,運用自如,既有文采,更見品德。很可能后人認為“子證父攘羊”欠妥,改為“父愿子成龍”的。不明究竟者再附會到某些名人身上,才產生許多不實之詞。還有甚者,改出句為“以父作馬”(對句為“愿子成龍”),殊不知出句四字均為仄聲,前后音節失替,上下聯文失對。如此考官還須回塾中攻讀《聲律啟蒙》,墊補墊補。
有文章說袁世凱13歲時曾制一聯:“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以潛龍自許,以逐鹿自勵。姚雪垠小說《李自成》中寫道:牛金星非常高興,馬上在桌上攤好紙,蘸飽筆,略一思索,寫成一副對聯:“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尚炯看見金星不僅字寫得好,而且在對聯中把闖王比做潛龍,暫時蟄居大澤,希望闖王“逐鹿中原”,內容非常恰切,不禁連聲叫好。同時他看出來,請金星幫助闖王打天下的事有八分可以成了。不久,李自成從野外回來,看見金星寫的對聯,十分高興。等他品味了一下對聯的內容,卻有點不好意思,謙遜地說:“先生,這下一句‘中原鹿正肥很恰切目前隋形,上一句‘大澤龍方蟄卻不敢當。當今起義的人很多,弟無德無能,怎敢以潛龍自居!”牛金星大聲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將軍愛民如子,思賢若渴,遠非他人可比,萬不要妄自菲薄。”如果說姚雪垠借用現成聯語寫進小說,那也是作家藝術加工的手法。可惜電影《大刀王五》中譚嗣同家布景使用此聯,居然寫成“大澤龍雲蟄,中原鹿正肥”,誤認“方”為“云”,再加繁化所致。
莫漢喬先生《五百年內三次重用的妙聯》說:元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率領的“紅巾軍”起義誓師,樹起兩面大旗,上寫旗聯:“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明朝正德年間,河北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起義軍中,也樹起兩面大旗,斗大的金字寫著:“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清朝咸豐年間,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提倡“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打下南京,改為“天京”,宣布建立“太平天國”。其“天王府”大殿懸掛金字楹聯:“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虎賁”乃勇士之稱,語出《書·牧誓》:“武王戒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孔穎達疏“若虎賁(奔)走逐獸,言其猛也”。“飛龍”,比喻帝王,“九五”指帝位。孔穎達疏:“言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飛龍在天……猶若圣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成”。典意準確有力,措詞雄渾豪壯,既高度概括了太平軍當時排山倒海、銳不可擋之勢,也堅定地表達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