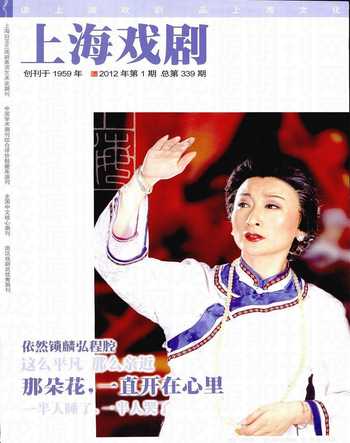關(guān)于譚派和譚鑫培體系
翁思再
“派”的本意是大河的支流。皮黃合流之后,京劇逐漸形成了。合流之初是老生的天下,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人稱三足鼎立。他們的身后出了譚鑫培,他是程長庚的弟子,又拜余三勝為師,還借鑒張二奎,熔此“老三鼎甲”于一爐而自創(chuàng)一格,這樣就派生出去,人稱“譚派”。若干年后他的孫子譚富莢也有大成就,藝術(shù)風格鮮明,觀眾仍稱之為“譚派”。一個家族,貢獻兩個流派,藝壇絕無僅有。可是這樣就發(fā)生一點問題:新譚老譚混為一“譚”,模糊了二者在層次、學理以及風貌上的區(qū)別。
譚鑫培被梨園界后人稱為“一代宗師”,他的成就具有一種承前啟后的劃時代意義。他不僅綜合了生行“老三鼎甲”的成果,而且藝術(shù)所涉及的面很廣。他最早是三慶班的武行頭,長靠、短打、武丑兼擅。除此之外他還創(chuàng)造過《盜魂鈴》之類的玩笑戲。在宮廷演戲的嚴格要求下,他老戲精演,改編出許多經(jīng)典作品流傳至今。他把昆曲傳下來的曲韻即中州韻,同各路皮黃里的湖廣音、徽音、京音有機地結(jié)合,為京劇制定“梨園家法”即舞臺音韻體系,使得京劇具備成為廣譜型劇種乃至成為國劇的基礎(chǔ)性條件。可以說京劇藝術(shù)發(fā)展到譚鑫培,就形成了一座集大成的里程碑。
譚鑫培的這種集大成地位,還可由他對于楊小樓、梅蘭芳和余叔巖“三大賢”的奠基作用來證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京劇黃金時代,這時在藝術(shù)上橫向列著三座高峰就是楊、梅、余。老生行當:譚鑫培的弟子余叔巖藝術(shù)上不求變異,而在唱腔韻味方面有所發(fā)展,在音韻體系方面有所完善。余叔巖的藝術(shù)雖已有余派之稱而實際上仍然是譚派。經(jīng)過師徒兩代的努力,譚鑫培和余叔巖形成了今天老生藝術(shù)的主流。武生行當:楊小樓是譚鑫培的義子,他的武生戲受到譚鑫培的親授;如今舞臺上風靡的楊派長靠戲《挑滑車》,實際可以被認作是廣義上的老譚遺響。旦角行當:梅蘭芳在青年時期由譚鑫培帶著演出,受到提攜而藝事大進。梅蘭芳后來名聲超過譚鑫培,然而就影響而言,梅蘭芳從四大名旦算起至今是七十多年,而譚鑫培從光緒年間“無腔不譚”算到今天已有100多年歷史,可謂譚在前、梅在后。另外,從藝術(shù)覆蓋面來看,迄今為止整個生行沒離開譚鑫培的范疇,而梅蘭芳在旦行卻未能做到全覆蓋,又是譚在前、梅在后。這就難怪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評價說:“四海一人譚鑫培,聲名廿紀轟如雷!”
在譚鑫培身后,“譚派”風行。受其直接傳授或影響的有余叔巖、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和周信芳。通過余叔巖再傳,出了譚富英和楊寶森。又在言菊朋、余叔巖、馬連良的合力之下,造就了奚嘯伯。這些流脈后來也被稱“派”。言派、高派、馬派、麒派、楊派以及譚富英的新譚派,今后或許還會有李(少春)派等等,茫茫九派流中國,老生藝術(shù)成為多姿多彩的大廈。然而,它們雖然也被稱為“派”,卻同譚鑫培的“派”有著上下游之別。
對于紛呈的藝術(shù)流派不能等量齊觀這個問題,美學家葉秀山先生有過一個闡述——藝術(shù)的發(fā)展往往是這樣:每個時期都有整合起上個階段成果的綜合性的流派。由這個“源”,可以發(fā)展成許多支流,這些支流在不同的方面為某部門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了新的因素,為更高的綜合準備條件,到了一定的時期后又會匯臺成“源”。這個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又把某部門的藝術(shù)推向新的階段。藝術(shù)的發(fā)展,就是這樣循環(huán)不已,日漸完善的——譚鑫培藝術(shù)的來龍去脈,非常典型地證明了這一點。所謂“分久必臺,合久必分”,譚鑫培從“老三鼎甲”這個“源”發(fā)展而成“派”之后,自己又成為新的“源”,后世再發(fā)展而源頭仍在此,因此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認為“無腔不譚”。
譚富英當然也屬于“無腔不譚”。作為余叔巖的徒弟,“新譚”出自譚余主流。譚富英兼演安工、靠把和衰派戲,堪稱完整意義上的老生演員。不過比起祖父來,他的戲路要狹窄得多,比如譚鑫培所擅長的武生戲、武丑戲和玩笑戲他就未能涉獵。譚富英唱腔的特色,在于嘴里具備一種罕見的腮音,唱起來特別豁亮。他臺風爽朗,有著滿身正氣和一股憨勁兒,尤擅扮演忠臣義士一類的角色。總的來說,他整體風格明亮率真,卻不如老譚古樸和道勁。無疑“老譚”是基礎(chǔ)性流派,而“新譚”則是特色性流派。
同樣作為基礎(chǔ)性流派的,在旦行是梅蘭芳的梅派。鑒于學術(shù)界已就“梅蘭芳體系”形成共識,今天我們把譚鑫培藝術(shù)稱為“譚鑫培體系”便有充分理由。這樣一來就可以把“譚派”這個詞的義項單一化,專指“新譚”譚富英,不至于混為一“譚”了。這是一種嚴謹?shù)膶W理態(tài)度。“譚鑫培體系”不僅是一頂桂冠,而且是有豐富內(nèi)容的。在它的結(jié)構(gòu)里面應(yīng)該包括劇目、唱腔、文武戲、身段論、表演方式、歌唱技巧、伴奏方法、流派沿革等等;所涉及的學科有美學,文學、藝術(shù)史、發(fā)聲術(shù)、音韻學、京劇教育學等等。可以說,這里的每一個子系統(tǒng)都是一片有待開拓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對于譚鑫培體系的研究必將有力地完善和支撐整個京劇藝術(shù)表演體系的理論架構(gòu)。
京劇表演體系這個名詞濫觴于梅蘭芳所著《舞臺生活四十年》,他說“譚鑫培和楊小樓代表京劇的表演體系”。梅蘭芳如是說,是他偉大的謙虛之表現(xiàn)。我認為科學結(jié)論應(yīng)該是把“譚鑫培體系”同“梅蘭芳體系”并列,前者涵蓋生行,后者代表旦行,二者合起來才是京劇藝術(shù)表演體系的全璧。